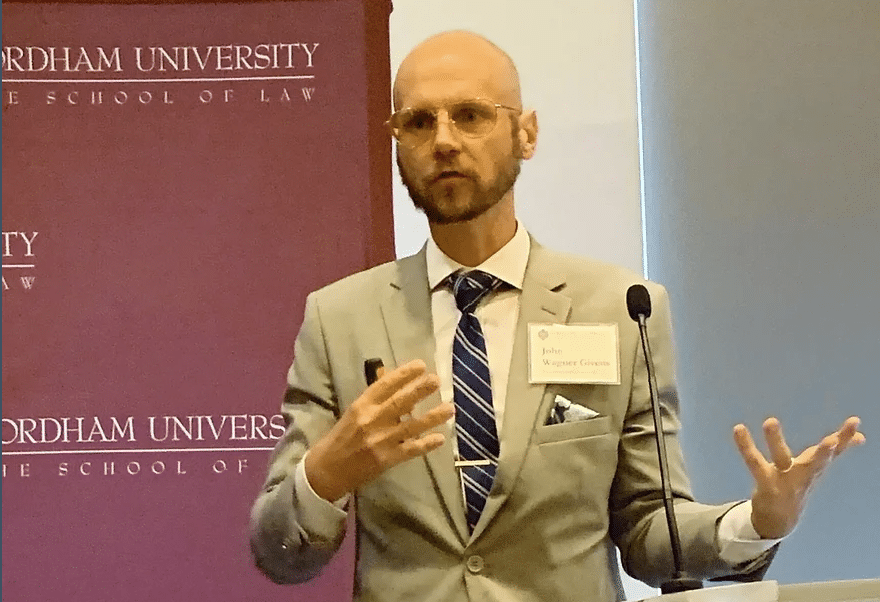同理心能成为美国政治极化的“解药”吗?
作者: 来源:PoIiticaI理论志
摘要: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美国党派社会极化明显加剧,学者们不得不寻找解决党派冲突的办法。群际关系心理学将同理心确定为减少群际冲突的关键机制之一,一些人认为缺乏同理心(empathy)导致了党派极化。然而,同理心并不总是能兑现这一承诺。我们认为,在实践中,同理心的体验偏向于一个人的内部群体,实际上会加剧政治极化。首先,我们使用一个大型的全国样本,证明了更高水平的性格共情关注(dispositional empathic concern)与更高水平的情感极化(affective polarization)有关。其次,使用实验设计,我们表明,高度共情关注的人在评估有争议的政治事件时表现出更大的党派偏见。综上所述,我们的结果表明,与流行观点相反,更高水平的性格同理心实际上促进了党派极化。
作者简介:
Elizabeth N. Simas:休斯顿大学
Scott Clifford:休斯顿大学
Justin H. Kirkland:弗吉尼亚大学
文献来源:
SIMAS, E., CLIFFORD, S., & KIRKLAND, J. (2020). How Empathic Concern Fuels Political Polariza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14(1), 258-269. doi:10.1017/S0003055419000534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党派社会极化明显加剧,学者们不得不寻找解决党派冲突的办法。群际关系心理学将同理心确定为减少群际冲突的关键机制之一,一些人认为缺乏同理心(empathy)导致了党派极化。然而,同理心并不总是能兑现这一承诺。我们认为,在实践中,同理心的体验偏向于一个人的内部群体,实际上会加剧政治极化。首先,我们使用一个大型的全国样本,证明了更高水平的性格共情关注(dispositional empathic concern)与更高水平的情感极化(affective polarization)有关。其次,使用实验设计,我们表明,高度共情关注的人在评估有争议的政治事件时表现出更大的党派偏见。综上所述,我们的结果表明,与流行观点相反,更高水平的性格同理心实际上促进了党派极化。
美国的社会极化正在急剧增长,这一趋势是通过2016年总统大选中表现出的超党派化(hyper-partisanship)的趋势。意识形态差异超越了政策偏好差异。个人对政党的社会和心理依恋引发了情感反应和偏见,这些反应和偏见渗透到各种各样的观点和行为。例如,个人对政治竞争对手越来越负面的情绪、拒绝面对任何其他党派的观点、并拒绝与其他党派成员的交流、阻止与自身观点矛盾的权利法案的推行。日益显著的党派分化现象造成了种种负面结果:立法僵局、对政府的低信任度、非政治领域的职业歧视。
虽然党派身份的分裂相对较新,但种族和族群等社会身份长期以来存有争议。群体间冲突的最有希望的解决方案之一就是同理心,或者是他人的观点或情感的分享。例如,心理学研究表明,对被污名化群体(例如无家可归者或艾滋病受害者)的同理心关注感可以减少污名化和偏见。其他研究表明,对(少数)种族和族裔的同理心可以为容忍非法移民和可疑恐怖分子的民权政策提供更高的支持。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认为“同理心赤字”是美国政治许多问题的根源。按照这个说法,如果美国人能够理解对手的感情和观点,也许能够找到更多的共同点并减少过度的党派争执。
但是,尽管同理心有可能减少群体间冲突,但这种潜力可能并不总是被实现。关于同理心减少冲突效用的乐观发现来自对移情经验直接操纵的实验数据,但是从强迫实验(forced exposure experiment)中产生的影响可能与自我选择(self-selection)的情况有所不同。这个方法论上的观点至关重要,因为人们在日常经历的同情心中有系统的偏见,并且倾向于对内群体成员表现出更大的同理心。当处在可自由选择的情境时,人们往往找到符合自身需求的同质性环境(这才是现实中人们愿意付出同理心的场合)。人们认为同理心往往具有较高的社会成本,这导致促进同理心的动机下调。此外,我们更有可能理解和分享群内成员的经验,从而造成“同理心差距”。这种移情差距导致了现实世界的后果,例如减少了帮助外部成员的可能性,以及他们生活方式的贬低。即使个人愿意换位思考,这实际上可能会通过强化负面刻板印象或引发愤怒来增加冲突。因此,尽管在某些情况下对个人或群体的同情经验可以减少偏见,但现实世界中的个人可能很少将自己置于鼓励换位思考的情况下。
因此,即使是最同情的人也可能没有对他们的党派对手感到同情。更糟糕的是,如果出现被视为伤害本团体成员的行为,同理心甚至可能转变为对对方的愤怒情绪。因此,最富有同情心的人可能比那些冷漠的人反而在政治上更加极化。在本文中,我们结合了政治学和心理学文献,测试共情如何影响政党间敌对行为的多个方面。首先,使用全国性的调查,结果表明那些展现出更高程度的共情性格的人具有更高的党内偏爱,并且与他党的接触程度较少。其次,通过实验设计,本文展示了个人高度关注共情的倾向,会在宽容表达和幸灾乐祸体验(schadenfreude experience)中表现出更大的党派偏见。总体而言,我们的结果表明,倾向的同理心倾向于助长而非减少党派极化。
一、同理心与极化
长期以来,政治科学家采取了一种以政策为中心的方法来研究大众公众的极化。但是,尽管党派精英在政策上一直存在分歧,但只有弱的和不一致的证据表明大众公众已经效仿了。相比之下,采用社会认同方法研究极化的学者发现了来自公众间的有力证据,因为对其他政党的情感变得越来越消极。从这种角度来看,大众极化更多是党派政治强化而带来的结果,而不是事物偏好的产物。反过来,显著的群体身份导致两个主要政党成员之间的明确分歧。
这种极化现象不仅仅是负面情感。以往的研究表明,这种现象的行为表现与奥尔波特关于偏见的框架中的前三个层次一致——言语敌对、避开外团体成员和实际歧视——在政治领域内外都存在。例如,Lelkes和Westwood发现,个人更有可能拒绝其他政党的成员作为自己团队的成员,并且更有可能支持反对这些政党演说的行为。甚至有证据表明存在幸灾乐祸的现象,当那些不幸的事件归因于对立方时,例如军队伤亡和经济衰退等不幸事件,一些个体反而感到愉悦。总而言之,美国选民中的党派政治似乎越来越成为“我们”与“他们”的问题。
因此,同理心成为弥合这种鸿沟的潜在工具。移情通常被认为是一个单一的过程,但心理学家普遍同意它由多个重叠的过程组成。根据同理心的概念,有四个相关的但不同的类型。我们将注意力集中在可能最接近该术语的概念——共情关注(empathic concern)的维度上。共情关注是指倾向于为身处困境的他人感受到以他人为中心的情感,例如同情或怜悯。共情关注可以被视为一种类似特质的倾向,而同情(或怜悯)则是相应的处于情感反应的状态级别。以他人为中心的同情或怜悯是共情关注的机制,借以此,人们会采取行动来援助他人或帮助他人减少伤害。同情对群体内冲突的降低也起着核心作用。实际上,它始终是小组偏见减少的最直接驱动力。因此,共情关注不仅与有关同情心和极化的普遍论点最密切相关,而且它也是接近取向行为和亲社会行为的最强预测因素。
但是,尽管那些在共情关注上具有特质性高水平的人更有可能在各种情况下体验到同情,但我们认为,共情关注实际上应该加剧而不是缓解上述许多极化表现。首先,同理心的表达是有偏见的。因为同理心既可能在心理上又可能在经济上带来成本,所以有许多因素会影响一个人是否会体验到同理心。这些因素中至关重要的是个体与目标之间的关系,因为个体更容易对内部群体成员产生同理心关注。例如,最近的一项神经科学研究通过与足球队的联系来操纵群体认同。参与者报告称,当受试者是内部群体成员时,他们对他人痛苦表现出更多的同理心关注,并且更愿意承受痛苦来减轻另一个人的痛苦。这两种反应都与左前岛叶的激活一致。同理心体验中的这种族群偏见可能部分原因是与内部群体成员更多的共同经验,这有助于同理心地产生。更普遍地说,对内部群体成员的同理心有助于增强合作及其所带来的收益。相比之下,在资源有限或群体冲突时,对外部群体成员的不加区分的同理心可能是代价高昂的。因此,我们预计人们更有可能对党派内部群体成员产生同情,这将促进党派偏袒。我们预计将观察到两种形式的假设:
H1:与其他政党相比,可以预测到共情关注应该产生更多地对党内成员更积极的情绪反应。
H2:反之,共情关注应该会增加对其他政党的负面情绪。
然而,尽管那些具有高度同理心的人可能会不喜欢外部政党成员,但他们也可能不会避免接触他们。因此,尽管同理心可能会促成极端化的许多表现形式,但它可能会减少至少一种:社交距离 (social distance)。这可能看起来有些违反直觉,但它与高度同理心个体不是被动或回避冲突的证据是一致的。相反,情感关注对应着一种“接近”动机(“approach” motivation),有助于促进亲社会行为。因此,具有高度同理心的人不应该被与意见相左的人接触或与外部政党的熟人产生分歧所排斥。相反,同理心应该增加个人接触或与多样化的他人互动的接受度,通常会激励人们“以更支持他人的方式行事,而不是取决于他们对他人的喜好程度”。因此,我们提出到三个假设:
H3:预期情感关注将创造一种接近动机,从而减少社交距离。
然而,愿意接触与自己不同的思想和个体也有其限制。情感关注度高的个体在与不同派别的人接触时,应该更愿意接受中立或良性互动。也就是说,在情感上更为包容的现象通常出现于非对抗性的情景,例如与外团体成员在同一社交场合中相处。但是,当群体和(或)与他们的潜在互动被呈现为更具威胁性或竞争性时,情感关注可能会促进更多负面的道德情绪,例如愤怒或想要惩罚的愿望。对内群体的偏见与对外群体的愤怒结合在一起,也可能导致另一种比同理心更为消极的情绪:幸灾乐祸。特别是在内部群体竞争加剧的情况下,如果外部群体的损失被视为内部群体的收益,那么这种情况可能会带来愉悦感。
这些更为消极的共情反应很容易转化为政党间的竞争。关于伤害的信念和愤怒的感觉似乎普遍存在于美国的党派政治中。根据最近的一项调查(Pew 2016),近半数的民主党人(41%)和共和党人(45%)报告称,看到对立党派是对国家福祉的威胁。相似比例的民主党人(47%)和共和党人(46%)也报告对立党派感到愤怒。此外,许多政治情境实际上都是零和游戏。举个例子,考虑这样一种情况:一位现任立法者的尴尬个人照片被泄露给媒体。高度共情的反对党成员可能会为这位立法者及其家人面临公开羞辱而感到同情。但是,由于共情也驱使他们支持自己的政党并将该立法者所在的政党视为有害的,这些感觉可能会被认为是公正的惩罚或对用党候选人代替该立法者的前景潜在增加的喜悦所缓和。因此,当对立党派被认为造成了伤害时,具有共情倾向的人应该会产生更强烈的愤怒情绪,并更强烈的希望减少外部党派所造成的伤害。这带给我们另外两个假设:
H4:共情关注会增加信息审查的意愿,如果信息来自敌对派别。
H5:尽管共情关注通常应该减少幸灾乐祸的情感,但这种影响在对立政党遭受痛苦时应该比同党派遭受痛苦时要弱。
当然,我们并不是第一个提出党派分歧可能导致对外派别产生愤怒和负面情感的人。事实上,对外派别候选人的愤怒经常被用作情感极化的指标。研究表明,意识形态分歧会影响愤怒情绪。然而,我们的贡献在于将共情融入理论故事中,并表明那些对他人表现出最大关切的人也是最具社会极化倾向的人。因此,极化不是公众缺乏共情的后果,而是我们体验共情的偏见方式的产物。
在接下来的部分,我们将展示分析以检验这些假设。我们首先对一项原始的全国性调查进行检查,以探索共情和党派偏爱以及社交距离之间的关系。然后我们利用调查实验更清楚地说明了将共情与社交极化联系起来的因果路径,并探索了对审查和幸灾乐祸的倾向。
二、研究1:情感与社会距离
我们首先使用YouGov在2016年5月进行的原始调查数据来测试我们的期望值。YouGov采访了1,181名受访者,其中1,000名受访者与人口在性别、年龄、种族、意识形态、政治兴趣、选民注册和党派上进行了匹配。采样框架是根据2010年美国社区调查、2010年人口普查和2007年皮尤宗教生活调查构建的。
我们的第一个假设(H1)是,那些更具共情关怀的人会相对支持自己的政党而非对立党派。为了检验这种党派偏好,我们利用了两个问题的回答结果,询问受访者对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态度,采用了一个七点量表,范围从“非常有利”到“非常不利”。然后我们将受访者对另一个政党的评分从他们对自己政党的评分中减去,以创建一个序数测量,范围从6(最高的本党评分,最低的对立党评分)到-6(最低的本党评分和最高的对立党评分)。为了测试我们对共情者更多负面看待对立党的预期(H2),我们只需检查对立党的七点偏好度评分。
为了捕捉社会距离(H3),我们使用了两个问题,询问受访者如果(a)他们的家庭成员与另一个政党的成员结婚,或者(b)他们的邻居在自己的院子里放置了另一个政党的总统候选人的标志,他们会有多么生气(两个问题都用五分制度进行测量)。尽管对后者的反对似乎属于审查的范畴(H4),但我们认为仅仅放置一份正面的竞选标志并不足以引发更多负面的移情反应。也就是说,我们只有在对立党派的言论明确具有敌对性时才预期会出现审查。我们对两个回答取平均值,得到一个范围从1(两种情况都不难过)到5(两种情况都非常难过)的度量。这个量表的平均值是2.0,有41%的受访者属于最低的类别。
我们使用人际反应指数(IRI)来衡量共情,这是一种广泛使用和经过验证的衡量人际共情的工具。IRI要求受访者使用五分制的评分来指示一系列28个陈述描述他们的程度。我们的重点在于七个旨在衡量共情关注的问题。IRI的完整文本和因子载荷可在本文的线上在线附录A中找到,共情关注指标主要包括诸如“当我看到有人受到利用时,我会感到有点保护他们”和“有时当别人遇到问题时,我并不感到非常难过”(反向编码)等陈述。我们重新缩放所有回答的范围,使其从0到1,并将这些共情问题的平均值用作我们的关键独立变量 (α = 0.75; x bar =0.68, s.d. = 0.18). 剩下的问题用于构建类似的七项指标,以代表共情的其他三个维度:personal distress (α = 0.77)、perspective-taking (α = 0.76)和fantasy (α = 0.76)。目前,我们将这些变量视为控制变量,并在文中稍后讨论它们的理论意义。
此外,我们控制了政党认同的强度、意识形态的极端程度和新闻兴趣,因为两极分化应该在最忠诚和积极参与的公民中最为突出。我们还包括一个二元指标来表示政党成员资格,以考虑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之间的潜在差异。最后,我们控制受访者的教育程度、年龄、性别、种族和收入水平。
表格1呈现了三个序列logistic模型的结果,每个模型都对应我们的一个因变量。我们首先分析两个检验党派情感的模型。结果如预期。在相对于党内好感度的模型中,共情关注的显著正系数表明,随着个体的情感共情能力增强,他们更有可能偏袒自己的政党。图1左侧的面板展示了这种影响的大小。从最低的情感共情值变化到最高的值,会导致在党内有最高的好感度并对党外持有最低的好感度(相对党内偏好= 6)的概率增加约0.14。因此,这些结果支持我们的观点,即情感共情有助于情感极化的发生。
表1
图1
如果这些发现主要是由于对同党的积极情感而不是对党派对手的负面情感所驱动,那么这些发现可能不太令人担忧。然而,在表1的第2列中呈现的外党青睐模型提供了清晰的证据,即共情关注促进而不是抑制外团体敌意。这个结果在图1的右侧面板中有所说明。在这里,共情关注的最小-最大变化会使表达最少的外党青睐的概率增加约0.27。综合这些结果表明,共情关注促进情感极化,并且是通过推动负面的外团体情感来实现的。
在社会距离方面,共情关注度再次成为一个显著的预测因素。但是,尽管共情增加了相对和绝对不喜欢异党的情感偏见,但通过增加与异党接触的舒适度,它降低了这种情感极化。如图2所示,那些共情关注度高的人对于拥有一个属于对立党派的家庭成员或邻居的可能性更不容易感到不安。共情关注度从最低到最高的转变将使得在最低类别中的概率增加-即表明您完全不受任何情况的困扰-约为0.32。因此,虽然共情关注度可能会引起更多的对党派对手的负面情绪,但共情关注度的面向接近方面似乎鼓励与异党成员接触,可能是为了改变被视为有害的行为。
图2
党派身份的调节作用
根据我们的论述,人们在体验同情心时对自己的内部成员比外部成员有偏见。考虑到我们在这里关注的是党派身份,共情关注度的影响应该在那些具有党派身份的人和那些最强烈地持有这种身份的人中最为明显。我们用一系列附加模型进行了测试,这些模型显示在在线附录B中。在第一组模型中,我们将共情关注度与一个哑变量进行交互,该变量指示受访者是党派人士还是独立人士(包括倾向者)。我们首先检查了相对党派情感的绝对值。如预期的那样,共情关注度在党派中显著预测了极化(b = 1.64, p = 0.017),但在独立人士中没有这种效应(b = 0.62, p = 0.355),尽管交互项不具有统计显著性(p = 0.244)。我们采取了类似的方法,将共情关注度与党派强度相互作用,分别估计了每个党派强度水平上同情心的效应。与预期的一样,该效应在强烈党派(b = 1.72, p = 0.047)和弱党派(b = 1.56, p = 0.118)中最为明显,但在摇摆派(b = 0.62, p = 0.559)和独立人士(b = 0.63, p = 0.373)中较弱,尽管交互项不具有统计显著性。与之相反的是,在研究社会距离时,我们发现效应在党派身份上基本保持不变,这表明,与理论一致,对外团体成员的舒适感反映了那些共情关注度高的人的更一般的接近动机。相反,当我们检查社交距离时,我们发现效应在党派身份上基本上是恒定的,这表明,与理论一致,对外团体成员的舒适感反映了那些具有高度同情心的人更一般的方法动机。
三、研究2:审查与幸灾乐祸
为了进一步解释我们的调查结果,并更好地区分极化与对两个政党的普遍厌恶之间的差异,我们接下来展示了一项原始实验的结果,该实验允许我们测试我们对审查(H4)和幸灾乐祸(H5)的预期。我们的实验嵌入在休斯敦大学的1232名本科生的调查中。虽然是方便抽样,但样本相对较为多样化,并在我们的关键自变量–共情关注(x bar=0.69, s.d. = 0.17)上提供了足够的变异性,该变量再次使用IRI进行测量。
实验对象被随机分配到两个版本的短文中的一个,描述了最近在一所大学校园发生的抗议事件。治疗的完整文本可在在线附录C中获得,但在各种情况下,有几个关键事实保持不变。在两个版本中,校园警察不得不关闭一群支持党派的学生的抗议活动,他们抗议某个因发表激烈言论而出名的人所发表的演讲。在两个版本中,一位试图聆听演讲的旁观者被抗议者打击。在两个版本中,抗议者成功地取消了演讲。在文本中,我们只是随机变换了党派意涵。在一个条件下,演讲者批评民主党,并受到学院民主党人的抗议;在另一个条件下,演讲者批评共和党,并受到学院共和党人的抗议。
接受治疗后,我们询问了一系列关于演讲者、抗议者和被抗议者袭击的旁观者的感受的问题。我们首先关注对演讲者的反应。虽然我们发现那些具有移情关注的人更容易接受相对温和的反对派接触,但我们预计演讲者对受访者所在党派的明确攻击会使那些具有移情关注的人更容易产生负面情绪。也就是说,我们预计党派偏见会增加关闭批评受访者所在党派的演讲者的愿望,并且移情关注会放大这种党派偏见在审查方面的影响。为了测试这一点,我们评估了审查制度,通过让受访者使用七点量表对四个陈述表达是否同意,包括演讲者是否应该被邀请,抗议者是否有正当理由,演讲是否应该被允许以及大学是否应该做更多的工作保护言论自由。我们使用这四个回答的平均值构建了一个连续的审查制度测量,其范围为1至7,平均值为3.45(标准差为1.06),中位数为3.50。
接下来,我们考虑对于针对特定政党的抗议者的反应。我们询问被试对于惩罚参与抗议的学生的三种不同形式的支持程度:禁止该团体举办未来的活动、对参与学生进行停学处分和开除参与学生。在对所有三个项目求均值后,我们的样本对于惩罚抗议者的愿望相对较低(在七分制中x bar=2.81)。然而,我们预计当抗议者来自不同政党时(即,学生们正在抗议来自被试自己政党的演讲者),被试更有可能想要惩罚抗议者,并且在高度共情的被试中,这些处理效应将最大化。
最后,我们考虑对被抗议者袭击的学生的反应。我们创建了一个同情程度的衡量方法,通过平均两个关于同情和同情那位学生的问题来得出 (x bar=3.10)。同样,我们通过平均两个问题来衡量受访者对于受伤学生的滑稽和幽默感,以得出一个五分制的幸灾乐祸程度(x bar=1.82)。由于旁观者在试图听演讲时被袭击,我们预计那些同情心更强的人在演讲者来自相反政党时会表现出更少的关注和更大的幽默感。也就是说,当旁观者无法听到被支持者的发言时,人们应该更加同情并感到更加愤怒。但是,当旁观者无法听到对立方的发言时,高度关注他人感受的人可能不太愿意关心,并且可能会为自己一方成功阻止对方听到发言感到高兴。
总之,当被呈现出外部政党与内部政党的发言人时,我们预计那些高度关注他人感受的人会表达出更强烈的审查演讲者的愿望,较低的惩罚抗议学生的意愿,并对试图听取演讲者发言时受到攻击的学生表现出较少的同情心,但更多的幸灾乐祸情绪。为了测试每个预期结果,我们使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对于连续的审查和惩罚变量)和序数逻辑回归(对于序数同情和幸灾乐祸变量)来将我们的四个结果建模为接受外部政党与内部政党演讲人处理,共情关注以及两者的相互作用的函数。这四个模型的结果显示在表2中。
表2
图3
首先讨论审查,我们发现在处理和共情之间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左侧图3说明了这种效应。尽管共情程度较低的人不区分两种类型的演讲者,但共情程度较高的人在对方政党的演讲者发言时更有可能要求停止演讲。更具体地说,对于一个比共情程度均值高一个标准偏差的个体,审查欲望从5分尺度上的3.22增加到3.77 (p<0.01)。这些结果符合我们的期望,即人们的共情倾向会加剧政党偏见。
在想要惩罚抗议者的愿望和对被抗议者袭击的旁观者的同情方面,我们没有发现显著的交互作用效应。共情关切在无论是对内党派还是外党派的发言者,都会一致地降低惩罚愿望并增加同情心。尽管共情不会加剧党派偏见,但交互项的系数表明,共情也不能提供任何缓冲党派偏见的作用。最后,在看待幸灾乐祸时,我们再次观察到处理和共情之间的交互作用系数具有统计学显著性。为了说明这一点,图3右侧的面板绘制了被预测的不同概率之间的差异,在外党派与内党派的演讲者条件下,他们被归类为最低的幸灾乐祸程度(1级,也是众数)。因为这是最低可能的值,那些共情程度高的人的影响是显著且负面的,表明他们不太可能处于这个低的类别,随后更可能处于一个较高的类别。例如,再次考虑那个共情程度得分高于平均值一个标准偏差的个体。我们的模型预测,当被抗议者在试图听取来自不同政党的发言者时,处于任何大于1的类别的累积概率为0.68,但当发言者来自同一政党时,仅为0.54。在线附录C中提供的其他分析表明,无论是看民主党人还是共和党人,这些实验结果都支持我们的论点,即共情并不能减少选民中的党派敌意,在某些方面甚至会加剧这种敌意。
“换位思考”能够拯救极化吗?
总的来说,我们的结果基本上与更悲观的关于共情影响的观点是一致的。然而,我们专注于共情关注度,而一些研究表明,换位思考可能会减轻某些形式的情感极化。与共情关注不同,换位思考不涉及对他人情境的情感反应。相反,换位思考“使个人能够预测他人的行为和反应”。因此,换位思考可能会提供更好的团体间理解,而没有负面的情感反应。实际上,换位思考而不是共情关注最有利于促进谈判和发现隐藏协议的能力,高度换位思考者不太可能有刻板印象,更容易容忍分歧,更容易被政治辩论和对话的机会所吸引。因此,换位思考可能有潜力减少这里探讨的任何形式的极化。
然而,对于换位思考的期望并不那么明确。有些人将这种倾向描述为“关系放大器”,可以增强关系中的合作或竞争性质。符合这种观点的是,一些研究发现,换位思考程度高的人更容易在竞争游戏中采取策略性(自私)行为,并更愿意在竞争环境中从事不道德行为。实际上,在一些情境下,换位思考可能失败甚至适得其反。因此,换位思考也可能无法减少政治上的分化。
与这些混合的期望一致,我们发现很少有证据表明换位思考可以减少探讨的极化类型。在研究1中,我们没有发现换位思考可以预测政党情感(见表1)。当排除对共情和其他共情方面的控制时,我们确实发现换位思考与社会距离存在显著的负相关(见在线附录B),但仍未能将换位思考与支持内部政党或支持外部政党的倾向联系起来。正如表3所示,在我们的研究2实验中,换位思考并没有显著降低政党偏见。
表3
然而,极化还有许多其他表现方式,超越了我们两个研究所探讨的范围。换位思考的认知性质可能有助于通过促进政策辩论或接触对立党派的新闻来源来减少党派分歧。但是,我们未能发现换位思考减少外团体敌对等极化的基本方面的证据。当然,否定换位思考作为缓解极化的部分解决方案还为时过早,但我们的初步发现并不令人鼓舞。
来源时间:2023/4/12 发布时间:2023/4/11
旧文章ID:296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