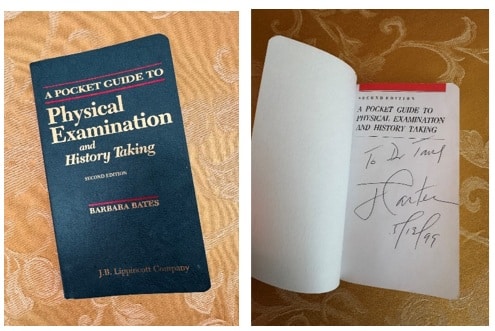党争加剧,美国呼唤“政治经济学”回归
作者:尼古拉斯·莱曼(Nicholas Lemann) 来源:法意观天下
法意导言
美国现实表明曾经由专家学者们主导构建的市场规则越来越容易受到党派斗争的影响。本文《美国的新政治经济学》(The New Political
Economy)于2023年1月8日刊登在《华盛顿月刊》(Washington Monthly),作者尼古拉斯·莱曼(Nicholas
Lemann)认为美国当前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不再只是专家学者们所研究的理论问题,而是在不断受到党派斗争的影响。自由主义者应当避免陷入市场自由的窠臼,关注经济政策中正在发生的巨大变化。此外,还应发展出一套新的经济政策指导原则,诸如避免经济权力过度集中,减少经济发展对群体的破坏以及平衡利益冲突等,以促进国家的稳定发展。
曾经由专家学者们主导的市场规则越来越容易受到党派斗争的影响,而这也正是国父们的初衷所在。自由主义者需要成为美国新政治经济学发展的先锋。
在《联邦党人文集》第十篇中,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如是写道:“造成党争的最普遍而持久的原因,是财产分配的不同和不平等。有产者和无产者在社会上总会形成不同的利益集团。债权人和债务人也有同样的区别。土地占有者集团、制造业集团、商人集团、金融业集团和许多较小的集团,在文明国家里必然会形成,从而使他们划分为不同的阶级,受到不同情感和见解的支配。管理这各种各样、又互不相容的利益集团,是现代立法的主要任务,并且把党派精神和党争带入政府的必要的和日常的活动中去。”
麦迪逊于1787年发表前述观点,当时美国宪法还未批准通过,所谓的政府也几乎不存在,但其构思在很多方面都有启发意义。他认为,新国家的政治纷争主要来源于经济利益冲突,而政府的主要任务就是解决这些争端。任何曾经在立法机构工作过的人都能体会到麦迪逊的想法在现实中的映射。早在共和国成立之初,南方的种植园奴隶主便与北方奉行贸易保护主义的制造商展开了斗争,美国第一和第二银行则是争夺中央金融权力的归属,税收、领土扩张以及修建道路和运河等有关“内部改进”方面也争论不休。在今天,经济利益集团仍在各领域相互争斗——贸易、工会的作用、大型科技公司的权力、向清洁能源的过渡以及无数的其他问题。
此类政治问题与我们在当代一般性公众议题中所讨论的内容存在脱节。我们习惯于认为非经济问题(堕胎、移民、治安)因其重要特性而有讨论的现实必要,这往往都是些基本的道德问题,而经济问题则是专家们对“经济”的技术管理而非利益集团之间的权力斗争。失业率、通货膨胀率、美元的强度和贸易逆差是多少?美联储在下一次会议上将提高多少利率?金融市场将对此如何反应?这些都是人们可能会在报纸头版和电视新闻中看到的经济问题。麦迪逊所认为的美国政治经济仍在现实中存在,但是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点关注。
这种情况是如何发生的?从建国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将经济问题视为美国政治的中心以及权力斗争的方式似乎是合适的,特别是考虑到最近的历史研究工作将奴隶制看作资本主义的一种形式。在进入经济工业化时代后,围绕经济问题展开的辩论尤其激烈,这催生了大规模的移民、城市化和前所未有的财富积累(在个人手中)和权力集中(在信托和公司手中)。在20世纪初的几十年里,作为对现实的回应,联邦监管机构、中央银行以及政府支持的大规模工会运动和现代福利国家出现了。
战争为经济大萧条划上了句号,二战后的繁荣削弱了美国政治对经济斗争的关注,福利国家的发展停滞不前。战后的几年里,包括自由主义者在内的许多人都认为,美国已经建立了一个可行的经济秩序,该秩序由受到严格监管的工业企业主导,具备类似其他工业民主国家政府为劳动者提供保护的福利国家功能。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崛起就是一个现实的写照。1946年,经济学成为一门学科,白宫也设置了经济顾问委员会这一正式常设机构。这体现了一种新的信念,即通过监督和管理财政和货币政策,政府可以保持经济增长,控制通货膨胀和失业,并遏制未来的萧条。这种想法具有政治优势,不会像劳动法或反托拉斯法那样再引起冲突。而且,它将重点放在宏观经济而不是经济利益集团之间无休止争夺优势上。人们可以把“政治”“利益集团”看作是政府管理经济的敌人,而不是本质。
随着20世纪的到来,至少在精英圈子里,一系列传统政治经济学工具被认为几乎是愚蠢的方式,还会取得适得其反的效果。这其中有贸易限制,价格控制,产业政策,试图打破大规模的经济集中,支持特定的城市、城镇和地区的发展以及促进工会的政策等。其中许多在政治上表现为经济实体之间的竞争(比如艾达·塔贝尔,和她的父亲一样,代表小规模石油生产商与标准石油公司进行斗争),但经济学理论和经济政策都对经济实体间的相互作用不感兴趣。经济的整体健康状况和消费者福利成为经济政策唯一的正确目标。不平等和社会混乱可以在事后通过再分配主义的税收政策来解决。这些并不只是保守派的想法,自由派政府也热情参与,放松了对航空公司、卡车运输、能源、电信、金融和其他行业的管制。1987年,《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头版社论(后来被删除),呼吁废除最低工资制度。美国两党都支持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后续一系列自由贸易条约。
这种经济体制不断加剧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这种情况一直没有得到改善。这是一种温水煮青蛙的变化模式,即渐进式发展而非以不可忽视的事件出现。直到2008年的金融危机和随后的经济大衰退才引发了政治层面对20世纪末经济确定性的强烈反应。此后,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运动出人意料崛起,主导了全世界的政治,有时会从根本上威胁到民主的持续健康发展。这其中有些是左派,但更多是右派,有时还带有强烈的文化因素,但始终都植根于经济上的不满。
当你的生活不太如意时,政治经济学就会显现出来。当你所在城镇的工厂搬到海外时,你可以感受到贸易政策对生活产生了不利影响。但如果你受过良好的教育,生活在繁荣的大都市,找到了一份好工作,那是因为自由市场发挥了作用。要想重新唤醒我们长期休眠的政治经济学意识,必要的第一步是认识到经济是后天而非自发形成的。世界上有许多资本主义国家,每个国家都有其独特的资本主义特征,其由法律和习俗塑造,并不断被修改。私人企业(比如农场、对冲基金、汽车制造商、社交媒体平台、制药公司)的成功或者失败不仅取决于他们自己的工作和创造力,还取决于政府为他们制定的博弈格局和游戏规则。菲利普·朗曼(Phillip Longman)在文章《每日高价》(Everyday High Prices)中呼吁人们关注政治经济学的一方面——零售商和供应商之间为利益而进行的不公开的恶性斗争。在这其中政府总是作为一个不总公正的裁判存在。私人股本在50年前还不存在,如今它在经济上的突出地位依赖于联邦监管中一系列鲜为人知的变化。如果有更强势的反垄断政策,就不会出现席卷一个又一个行业的“四大”或“五大”合并。谷歌和Facebook等科技公司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功,是因为它们对自己所呈现给大众的内容并不承担法律责任。所有这些政策都是发生在法庭和听证会上的,只有游说者,并没有媒体或公众的密切关注。
正如当前美国政治经济学的形成——特点是高度不平等、显著的地区和种族差异以及对普通人生活的极大破坏,它在发生时几乎没有人注意到,其重塑也是如此,因为它已经在进行中了。在美国,最被低估的大事之一是拜登政府戏剧性地背离了过去几届政府(包括民主党政府)的经济政策。本届政府在反垄断问题上是几十年来最激进的。它在金融领域采取了强有力的监管措施,在产业政策方面进行了重大尝试,例如试图加强国内半导体产业并启动绿色能源产业。巴里·林恩(Barry Lynn)在文章《制造业与自由》(Manufacturing and Liberty)中讲述了这件事,并催促政府采取更多措施。
人们不应认为共和党夺回众议院控制权意味着拜登政府制定重大经济政策的时代已经结束。也许完全恢复数万亿美元的《重建美好未来法案》是不可能的,但其中的一些内容,比如加强教育、培训和学徒制,以及针对“护理工作”的有效产业政策,很可能再次出现。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共和党把自己的未来押在了继续从民主党手中夺走工人阶级选民的能力上,而要做到这一点,需要的不仅仅是无休止的口头攻击。此外,由于如此多的经济政策是由法院和立法机构制定的,民主党对参议院的持续控制意味着政府可以继续任命能够履行其使命的人。
如果要测试一下你对拜登政府的《美国救援计划》《两党基础设施法》《通胀缩减法案》中降低和增加至5000万美元的支出项目的熟悉程度,你能过关吗?我想我是不会的。这些重大举措往往被报道得像是决定白宫胜负的冠军赛,而不是关注内容本身。对于自由主义者和进步主义者来说,关注经济政策中正在发生的巨大变化是至关重要的。尤其是在反垄断、金融监管、劳工政策和保守派所谓的“行政国家”的未来方面,对立阵营的人也会出现在做出决定的地方,而他们会独自前往吗?
在宏观和微观层面更密切关注这些经济问题的同时,自由主义者也需要发展出一种新的经济词汇表达。如果你曾经上过经济学入门课程,你可能会学到这样的知识:政府重塑经济的尝试注定要失败,任何放在企业身上的经济负担都会转移到消费者身上,赤字和债务是不负责任的行为,行业集中只要不直接伤害消费者就不是问题,贸易限制总是个坏的想法,创造性破坏是市场经济不可避免和体现其健康的一个方面。反对这些陈词滥调的尝试往往被认为是政客们试图为他们的选区争取政治利益的无聊和适得其反的活动,而不是制定出良好的公共政策。一套新的经济政策指导原则将有助于重构一系列广泛的争议,有助于与许多在当前经济进程中感到落后和被忽视的选民沟通,并指导我们自己对具体建议的评估。
我现在只提出其中的一些原则。首先,经济权力的过度集中无论是对人民的福祉还是对我们民主的健康都是非良性的。而经济权力转化为政治权力破坏了宪法旨在建立的平衡和对少数人权利的保护。我们不需要刻意伤害财产之主(这是富兰克林·罗斯福的说法)的利益,除非他们有过大的影响力并对普通人的关切视而不见。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之中因教育水平、种族、居住地和工作种类的差异而存在巨大且不断扩张的鸿沟,除非能够纠偏,否则这个国家就会变得不公平和不稳定。经济如同政治,再次引用詹姆斯·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的另一篇文章中的话:野心必须用野心来对抗。
其次,经济的设计和管理不仅是要促进经济的整体健康和增长,而且应该最大限度地减少持续的经济破坏可能对生命、健康和群体造成的伤害。当大型经济实体吞并较小的经济实体时,通常是通过承担其债务来给后者施加巨大的压力,迫使它们裁员或者以其他方式破坏社会。我们不应该再相信只要是自由市场交易就对国家有好处。资本主义总是在产生活力的同时带来错位。处理这些问题的一个方式便是事前预防——不失去工作,不削减利益,不容许社区衰败,这远比事后纠正要好得多。
第三,与所有政治一样,经济政治从根本上也包含利益冲突。麦迪逊在1787年就意识到了这点。政治经济学不是技术性的也并非与党派无关联,将其只留给专家们去研究并不是最好的选择。在实践中应用大量普遍性概念亦非最好的解决方法。笼统断言市场的优点常常会阻止我们本该进行、而且现在需要进行的讨论。美国政治经济的未来正在上演,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密切关注这些具体问题,而这才是一系列现实行为的目的所在。
文章来源:
Nicholas Lemann, The New Political Economy, Washington Monthly, 8/01/2023.
网络链接:
https://washingtonmonthly.com/2023/01/08/the-new-political-economy/
译者介绍
卢俊妃,北京大学法学院21级硕士研究生,现为法意读书编译组成员。
来源时间:2023/2/6 发布时间:2023/1/29
旧文章ID:292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