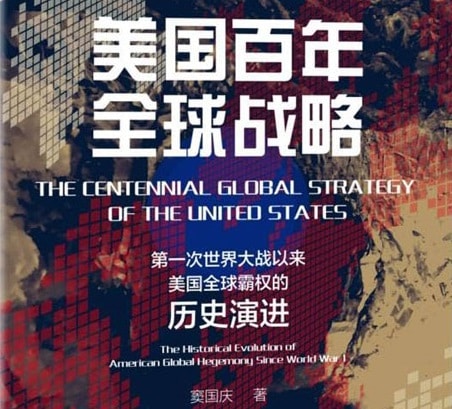反恐20年,美国陷入全面衰退危机
作者:本·罗兹(Ben Rhodes) 来源:法意读书
法意导言
转眼间,距离波音767客机撞击世贸中心已经20年了。20年前,小布什政府坚决发动的阿富汗战争,终结于前几日喀布尔机场上令人难忘的画面:仓促起飞的美军运输机和追着美机跑的阿富汗人民。20年来,阿富汗战争给世界带来了什么?正如原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本·罗兹(Ben
Rhodes)近期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第五期上发表的文章《倾覆之后,反恐给美国带来什么?》(How America Lets Its
Enemies Hijack Its Foreign
Policy)中追问的:“若没有这些武力干预,这些国家的人民是否会过上更好的生活?”全文回顾了美国20年来的反恐行动,得出了结论:战争并未达成目的,在使对象国陷入更深的专制与动乱的同时,对美国造成了巨大损失,威胁着美国与全球的民主价值观。为此,作者强调重新关注民主而非地缘敌人才是当务之急。显然,这是民主党人的传统观点。对“美式民主”价值观的再次强烈推崇与全球传播,已充分体现在拜登的外交政策中。值得注意的是,本文的一些逻辑与观点仍是需要深思的。作者重振民主的逻辑终点,是否是为了新的地缘遏制?
21世纪至今没有什么事件能像“9·11”那样,如此深刻地影响了美国以及其在世界的地位。这场恐怖袭击刺破了冷战结束后十年里美国人的自满情绪,并粉碎了历史将终结于美国领导的全球化的胜利的幻想。美国对此的反应程度重塑了美国政府、外交政策、政治与社会。如今,这一反应余波未尽。美国人只有审视这种过度的反应,才能明白他们的国家已然为何,路在何处。
我们很难夸大“9·11”的影响,反而很容易低估它。无论如何,“反恐战争”都是美国霸权时期的最大规模行动,这一时期始于冷战结束后,现在它已到了强弩之末。“9·11”后的20年来,反恐主义一直是美国国家安全政策中的首要任务。政府机构被重新设计以便在国内外打一场无休止的战争。一切基本职能——从移民管理到政府设施建设,再到公共政策,就像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旅行、银行、身份证等一样,已经为安全问题让步很多。美国已经在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巴基斯坦、菲律宾、索马里、也门和其它一系列国家使用了武力。恐怖主义已经成为美国几乎所有双边和多边关系中的一个突出问题。
反恐战争同样重塑了美国的国家身份。苏联垮台后,美国是一个失去了统一的使命感的国家,这种使命感曾被冷战培养起来。资本主义民主和共产主义专制之间、自由世界和封闭社会之间意识形态斗争的清晰性消失了。在“9·11”之后,乔治·布什(George Bush)总统提出了“统一美国身份”的宏愿,并将这一斗争引向下一代。他宣称,像反法西斯主义和反共产主义一样,反恐战争将是一种划时代的斗争。
布什将反恐视为一场具有决定性的、持续数代人的、全球性的战争,代表了在一场前所未有的国家灾难之后,一种有效的领导形式,但这不可逆转地带来了过度扩张和意想不到的后果。美国政府很快便滥用了其监视、拘留和审讯的权力。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争已经远远超出了消灭基地组织的初衷。美国的民主与军事化的政权更迭联系在一起,破坏了国内稳定和政权在国外的合法性。布什和他的政府所许诺的、以及保守派媒体不停预言的胜利从未实现,这逐渐削弱了美国人对政府的信心,并促使他们寻找内部的替罪羊。紧随“9·11”时代之后的沙文民族主义随之演变成一种恐惧和仇外的混合情绪,这最终导致了一位总统的上台:唐纳德·特朗普。他只在口头上承诺结束海外战争,而实际上重新利用反恐战争的话术去攻击不断变化的国内政敌。
如今,美国有一个更真诚地承诺要结束国家“永无止境的战争”的总统。乔·拜登总统做此事的决心通过他在阿富汗撤军的决定上表现出来,并且在拜登政府的全球议程中体现得更清楚。在他四月对美国国会的首次演讲和七月G-7峰会上发表的演说中,恐怖主义让位于消灭疫情、应对气候变化、重振民主以及与美国盟友一道,准备同日渐强盛的中国开展长期竞争的议题。“9·11”事件发生20年后,拜登在一步步推动美国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后“9·11”时代以后(the post-post-9/11 era)。
然而,有关反恐战争的庞大基础设施仍然存在,战争的诸多优先性已然影响着美国政府的组织、军事力量的部署、情报界的运转、以及对中东独裁政权的支持。正如奥巴马政府的情况一样,这些现实限制了美国果断地迈过后“9·11”时代、重振全球民主、以及巩固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能力。真正的转变需要采取更多强有力措施:重新安排美国在“9·11”之后的长远规划,并改变在国内外鼓励威权主义的安全化心态(securitized mindset)。若美国政府本身被设计用来发动战争,那他将永远无法结束战争;若民主在国家安全的权衡中始终被轻视,那政府就无法复兴民主。
同时,与美国在“9·11”后反思性地团结起来相比,今天美国代表什么以及作为美国人意味着什么更具争议性。关于美国身份的争论已经如此尖锐,以至于这个国家更容易受到各种暴力极端主义的影响,而“9·11”事件后的姿态正是为了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曾经,国会大厦被致命袭击会是一个清醒的行动号召;而今,它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以右翼否认主义(right-wing denialism)和转移话题(deflection)为特征的部落政治(tribal politics)来解释的。那个在9月11号后领导了数万亿美元的国家安全建设的共和党,却不愿意调查1月6号那天发生的事。
在这个背景下,聚焦与中国的竞争将是一个重新定义美国宗旨、重塑美国国内身份的做法。这一竞争现在成了美国政界的主要关切,它令两党达成了广泛的共识。美国确实有一些很好的理由去关注中国。不像基地组织,中国既对社会与治理有不同的看法,也有能力改变世界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讽刺的是,“9·11”事件后中国在全球影响力快速提升,因为美国常因对恐怖主义和中东事务的关注而筋疲力尽。从地缘政治影响力来说,中国已经成为反恐战争的最大受益者。然而,我们也有充分的理由对美中对抗可能发生的情况保持警惕。通过一个新的“我们对抗他们”来定义美国在世界的宗旨和身份,可能会使我们重犯在反恐战争上的一些最严重错误。
“远洋客轮”
奥巴马总统过去常常将美国政府比作一艘“远洋客轮”:一个巨大而笨重的结构,一艘一旦朝着确定的方向行进便难以转向的货轮。在“9·11”事件后,布什政府为这艘客轮指向新方向,并为之注入巨大动力。国家安全机构将重心再次放在打击恐怖主义上来:新机构的大量设置,组织结构的重新规划,新权力的授予,预算的重新编制,以及国家重心的重设。2001年美国在阿富汗军事上击败塔利班后,华盛顿沉湎在狂妄的胜利主义氛围中。美国的全球影响力似乎从未如此强盛。在2002年的中期选举中,共和党横扫国会掌握控制权,对恐怖主义采取强硬手段的政治主张在投票箱中得到了响亮的验证。自那时起,美国一直在清理这艘远洋客轮留下的残骸。
今天,那些经历了最激烈反恐战争的国家已深陷在不同程度的冲突之中。阿富汗正重新陷入内战,塔利班正重掌“9·11”前的优势。伊拉克经历了一场由基地组织(AQI)发起的漫长暴乱,后者随后演变成伊斯兰国(ISIS)。伊斯兰国仍因族群斗争和伊朗的影响而四分五裂。利比亚、索马里和也门都缺少统一政府,那里仍进行着残酷的代理人战争。“9·11”事件后美国的军事行动确实有一定的基础,也确实存在一些需要军事回应的威胁。但这些国家的条件说明了军事干预的局限性,也向我们提出一个问题:总的来说,就是若没有这些武力干预,这些国家的人民是否会过上更好的生活。
“9·11”事件后的一系列战争支出是惊人的。超过7000名美国服役人员死在阿富汗和伊拉克;超过50000人在行动中受伤;参加9·11事件后的退伍军人中;还有超过30000人选择自杀。成百上千阿富汗和伊拉克人流离失所。而据布朗大学(Brown University)“战争成本项目”(Costs of War Project)估计,因美国的军事介入,3700万人无家可归。与此同时,战争中和战后的各项投入已耗资接近7万亿美元。
对恐怖主义的反击也消耗了美国政府本就有限的巨大精力:总统和高官的时间和注意力,机构内部的人员配置和优先次序,这些都无一例外。想想吧,在过去二十年中,美国本可以利用这些资源和精力,在那些尤其是被中国共产党日益增强的经济影响力和改善基础设施的承诺所诱惑的地方,努力同中共展开有关气候变化、流行病、日益扩大的不平等、技术破坏与美国影响力减弱的竞争。
当然,鼓动反恐战争的组织是基地组织。“9·11”事件后,美国和其他国家面临更具灾难性的恐怖袭击威胁,他们不得不回应。值得称赞的是,美国军方和情报界消灭了基地组织,并除掉其领导人拉登。ISIS也同样通过美国有限的军事行动而被击退。我个人同那些执行反恐政策的美国人打交道的经历令我对他们肃然起敬。他们在优先事务不断变化的政府中勇敢地为他们的国家服务,帮助防止袭击和拯救生命。在一些方面上,国家反恐机构确实有存在的必要。
然而,这一事实并没有消除极大的过度反应,以及扭曲的风险评估,而这定义了华盛顿对“9·11”的反应。国家花费数万亿去阻止的袭击,仅会造成少量伤亡。要避免这种伤亡规模,我们本可以用一个更强力的反应来阻止COVID-19,通过已被国会阻挠的最低限度的枪支安全措施,或者通过预防由气候变化带来的极端天气来达到。所有这些都被忽视或阻挠,部分是因为华盛顿在恐怖主义上的固执。“9·11”战争的成本,包括机会成本的规模暗示我们,这个国家一定需要一场结构性的修正了,而不仅仅是一种改变。
始易终难
从总统开始,几乎所有拜登政府的高级官员都在奥巴马政府为使美国从“9·11”事件后的战争中解脱出来而努力发挥作用,这项复杂而充满政治色彩的任务最终将驻阿富汗和伊拉克的美军人数从2009年的近18万人减少到2017年的约15000人。在奥巴马的第二个任期,华盛顿的全球议程就像拜登在七国集团讲话中的描述:组织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加强全球卫生体系,并在试图遏制扩张的俄罗斯的同时向亚洲倾斜。
然而在事后看来,常被指责过度克制的奥巴马政府,实际上明显在相反的方向上犯了错误,因为它维持了“9·11”后的各项反恐措施。2009年在阿富汗的增兵行动延长了战争的时间,尽管回报越来越少,但致命无人机被扩大应用,这虽然取得了战术上的成功,却在许多国家将杀人制度化了。对包括沙特政权在内这样的独裁主义盟友的默许,败坏了美国的民主言论与风气,前者在也门发动灾难性战争。特朗普上台后,他的政府在中东部署了数以万计的美国军队以对抗伊朗,放松了平民伤亡管控,不再担忧人权问题,完全拥抱专制的盟友和伙伴,并将气候变化和全球健康置于次要地位。
显而易见的教训是,仅仅改变海轮方向是不够的。拜登和国会应该重新设计它。以气候变化为例,在奥巴马任下,为实现限制全球变暖的《巴黎协定》而进行的努力利用了分散在各机构的稀缺的气候专业知识人才,以及国会分配给反恐的一小部分资源。奥巴马政府不遗余力地将气候方面的专业知识与美国外交政策的机制联系起来:在国际政治中取得任何实质性成果所需的双边和多边关系管理。特朗普政府一上台,刚开始的气候优先便停止了。同样的事发生在白宫的流行病防治办公室上,它是奥巴马在2014年埃博拉疫情暴发后设立的。特朗普关闭了那个办公室,将其工作范围纳入一个专注毁灭性武器的办公室中——流行病防治工作实际上被反恐战争的基建吞没了。
现在,拜登团队有着二十年的前车之鉴,那就是对恐怖主义的关注已经带偏了国家的优先战略,而公众日益关注大流行病、气候变暖以及来自中国和俄罗斯的挑战。为了真正优先解决这些问题,拜登和他在国会的民主党盟友,应尽力结束部分“9·11”事件后的措施了。2001年国会的《授权作战法案》(Authorization for Use of Military Force)被用来为“9·11”事件以来的各种军事干预行动提供法律依据,该授权书应被废除,并为更为准确规范的东西所取代,在拜登任期结束前有一个确定的结束时间(built-in sunset)。常规行动的无人机打击应停止,其应只在美国政府准备公开披露和证明其行动的情况下使用。美国军队在全球的兵力情况应反映出对中东地区的优先考虑在减少;五角大楼应减少美国军队在波斯湾地区的过度表现,这种情况在特朗普时代有所加剧。
为了能够长期对气候变化和全球健康等问题保持关注,拜登政府应增加对清洁能源、大流行病防范和全球健康安全的联邦投资,并同时对支出进行重大改革。例如,国务院和美国国际开发署等机构应加强气候方面的专业知识建设,情报部门和军队应投入更多资源,了解并应对威胁美国人民真正存在的危险。
拜登团队会在这些措施上遇到阻力,就像奥巴马政府发现自己常常在与美国的政治大潮抗衡一样。关闭美国在古巴和关塔那摩监狱的努力受到两党议员的阻挠。2012年美国驻利比亚班加西设施遇袭,共和党对此极尽冷嘲热讽,这是一种对极右翼阴谋论的日益热衷,与共和党试图否定民主党支持的任何外交政策举措的结合。伊核协议旨在阻止伊朗核武器和另一场战争,而上述努力比授权在伊拉克进行一场无限制战争还带来更多争议。
但是现在,拜登处在一个后特朗普(post-Trump)、后大流行(post-pandemic)的时刻。共和党对特朗普主义的欢迎无疑威胁了美国人民的生命,并破坏了该党促进美国价值观的外交主张。拜登和他的团队具有独特的优势,可以向公众说明他们更值得信赖、更有能力、更能确保国家安全和加强国家民主。
为此,美国必须抛弃威胁民主价值观的思想。参考一下穆罕默德·苏丹(Mohamed Soltan)的经历,他参加了2011年在塔里尔广场(Tahrir Square)的抗议活动,是一位埃及裔美国人。他庆祝了埃及领袖胡塞尼·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的倒台,以及随之而来的民主开放。但在2013年军事政变驱逐了民选总统穆罕默德·穆尔西(Mohamed Morsi)后,苏丹加入了开罗拉巴广场(Rabaa Square)的抗议者。当局的安全部队开火,杀死了至少八百人。苏丹被击中,而后被捕入狱,饱受折磨,被审讯者鼓励自杀。他进行了持续近500天的绝食,并拒绝了ISIS的招募。在奥巴马向埃及独裁者阿卜杜勒·法塔赫·塞西(Abdel Fattah el-Sisi)发出个人呼吁后,他才被释放。
这种反乌托邦式情景揭示了“9·11”事件后美国外交政策的失败。该政策向一个残暴的政权、一个允许ISIS在其人满为患的监狱中招兵买马的政权,提供数十亿美元的军事和经济援助,这为该政权的残暴与美国援助合法化了,并使之更加激进。反恐战争总是在与自己开战。美国一边为埃及的镇压提供补贴,一边口口声声要宣扬民主价值。就像华盛顿继续向一个压制异己并在也门发动残酷战争的沙特政府出售武器一样。美国在反恐战争中的关键盟友,不仅是埃及和沙特阿拉伯,还有以色列和土耳其等国,都在“9·11”后都变得更加独裁严厉。他们在世界各地助长了美国想要扭转的独裁主义浪潮。这绝非巧合。
重振全球民主与永久的全球反恐战争是不相容的。天平必须要重新权衡。美国的军事援助应当以尊重人权为条件。华盛顿应当摒弃长期以来拖累美国外交政策的虚伪性。
反恐战争激化国内矛盾
反恐战争不仅加速了世界各地的专制潮流,在美国国内亦是如此。后“9·11”时代的沙文主义融合了国家安全与身份政治,歪曲了有关美国人的概念,模糊了批评者和敌人的界限。
在“9·11”事件后,一种“他我对抗”(us-versus-them)的右翼政治和媒体机构激怒了那些没有努力投入到反恐战争的美国人,并夸大伊斯兰世界作为“他者”入侵的威胁。但随着“9·11”袭击事件消失在人们的记忆中,而且很明显,美国在阿富汗或伊拉克不会有大的胜利,“他者”的本质已经有了变化。对恐怖主义的恐惧和关于“令人毛骨悚然的伊斯兰教法”的阴谋论,演变成对南部边境移民的恐惧,在国歌中下跪抗议警察暴力的运动员的愤怒,以及关于从班加西到欺诈选民的一切阴谋论。更多时候,这一系列举措针对的是少数族裔。
讽刺的是,伴随着白人民族主义者在夏洛茨维尔(Charlottesville)撞死一名反示威者,以及在匹兹堡的生命之树犹太教堂杀死11人,这种对“9·11”事件后国家政治仇外情绪的重新引导,最终是助长而远非打击恐怖主义。这也构成了一度无法想象的专制场景。当同胞们被无情视为国家的敌人,一场美国的暴力起义甚至也可能成为现实。
超级大国拥抱好战的民族主义,这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影响。“9·11”事件后美国政策的过度举措被其他地方的独裁者重新利用,后者在反恐的幌子下针对政治对手,取缔民间团体,控制媒体,并扩大国家的权力。当然,这不是美国的作为。然而,正如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沉浸在为其滥权行为开脱的“你也一样”主义(whataboutism),(译者注:whataboutism指的是冷战期间苏联对于西方世界政治宣传的一种回应手段,当西方世界指控苏联的某些问题时,苏联往往反问这个问题在西方同样存在。即一种道德相对主义立场。这个词在2008年由爱德华·卢卡斯(Edward Lucas)在《经济学人》的发表的文章后盛行)美国人对此感到退缩时,他们不应该轻率地忽视自己国家的过度扩张和好战的民族主义,这破坏了华盛顿反击普京、捍卫民主价值和加强基于规则的秩序的努力。
在“9·11”之后的几年里,一些人被关押在美国关塔那摩监狱。无人被认定犯有恐怖主义罪或被认为对美国构成严重威胁。当奥巴马初上任试图关闭该监狱时,有一个计划是在美国释放一些被拘留的维吾尔人,以表明美国政府愿意尽自己的责任,因为美国要求其他国家遣返一些被拘留在关塔那摩但被允许释放的公民。奥巴马的提议遭到了夸张的反对,其遭遇到的阻力使监狱无法被关闭。南卡罗来纳州的共和党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Lindsey Graham)和康涅狄格州的独立参议员乔·利伯曼(Joe Lieberman)带头提出指控,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声称这些人 “有激进的宗教观点,使他们无法与我们的人口同化”。
美国领导全球的传统,以及美国人对成为世界树立榜样的“山巅之城”的渴望,都令美国人理所当然地感到自豪。但是,为什么他们会认为,只有当他们的榜样——美国,呈现出积极的价值观和品质时,其他国家才会效仿呢?美国人既已毫无理由地入侵另一个国家,出于方便而支持专制,并在自己的国家羞辱少数族裔,那么当其他国家效仿这些错误行为,或利用它们为自己过度专制而辩护时,美国人不应该感到惊讶。
美国必须面对这一不安的事实,不是因为华盛顿应该从这个世界中退却,而是因为它不能把这个领域让给俄罗斯和中国。美国必须不能辜负它作为自由世界的领导者所讲述的更美好的故事。归根结底,这是美国人必须从 “9·11”事件后学到的最重要教训。要恢复美国的领导地位,就必须重建美国民主的范例,作为美国外交和国家安全政策的基础。
更多的我们,更少的他们
所有这些教训必须用到与中国不断加剧的竞争上。证明美国能比中国控制资本主义更优越是必要的,拜登正在为基础设施巨额支出辩护。国会正对科学和技术投入大量资源,以跟上中国创新的步伐。拜登和白宫正在提出有利于美国某些产业的政策,并完善出口管制制度,以解除连接美国和中国的关键供应链。美国的国防开支越来越受到未来突发事件的影响。国务院把加强美国在亚洲的联盟作为优先事项,在贸易、技术和人权方面,美国正与合作伙伴合作,并通过七国集团和北约等多边组织,建立尽可能牢固的对华统一战线。这些努力将产生自己的政治动机和压力,它们也将为美国政府内部资源和精力的扩大创造动力。人们已经可以感觉到这艘大船正在调整航线。
然而,尽管这些举措中的每一项都有其合理性,但仅是简单聚焦一个新“他们”是错误的——这种冲动可能会促成另一波民族主义影响下的专制主义,这在过去已经毒害了美国政治20年。更好的做法是更多地关注“我们”——一个有足够韧性的民主国家,能够经受住与对手政治模式的长期竞争,在世界民主国家中形成共识,并为世界树立一个更好的榜样。
除了在基础设施等大项目上有所作为外,美国的民主必须得到加强和振兴。保护投票权以及强化国内民主体系必须成为美国民主范例的基石。解决美国的不平等和种族不公正问题将证明,民主可以为每个人提供服务。根除流经美国金融系统的腐败,将有助于净化美国政治,遏制流向其他国家专制者的资源。阻止美国社交媒体平台上虚假信息和仇恨言论的泛滥,将遏制激进化,并削弱世界各地的独裁主义。30年来,美国政府在与中共打交道时将经济利益置于人权之上,许多美国公司、文化机构和个人也是如此。这种情况必须改变,这不是因为中美地缘政治上的敌对关系,而是美国对国内和全球民主价值观的支持。
世界是艰难甚至凶险的。美国必须坚持自己的立场以捍卫其利益。但是,在后“9·11”时代以后,这一定义不该是与下一个敌人的对抗,而应该是将民主作为人类组织的成功手段加以振兴。为了用一个更好的代际项目来取代反恐战争,美国人必须被他们所支持的东西,而不是他们所反对的东西所驱动。
翻译文章:
Ben Rhodes, Them and Us, How America Lets Its Enemies Hijack Its Foreign Policy, Foreign Affairs, Volume 100·Number 5/Issue 2021
网络链接: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states/2021-08-24/foreign-policy-them-and-us
译者介绍
陈泰安,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2020级硕士研究生,现为法意读书编译组成员。
来源时间:2021/9/14 发布时间:2021/9/14
旧文章ID:259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