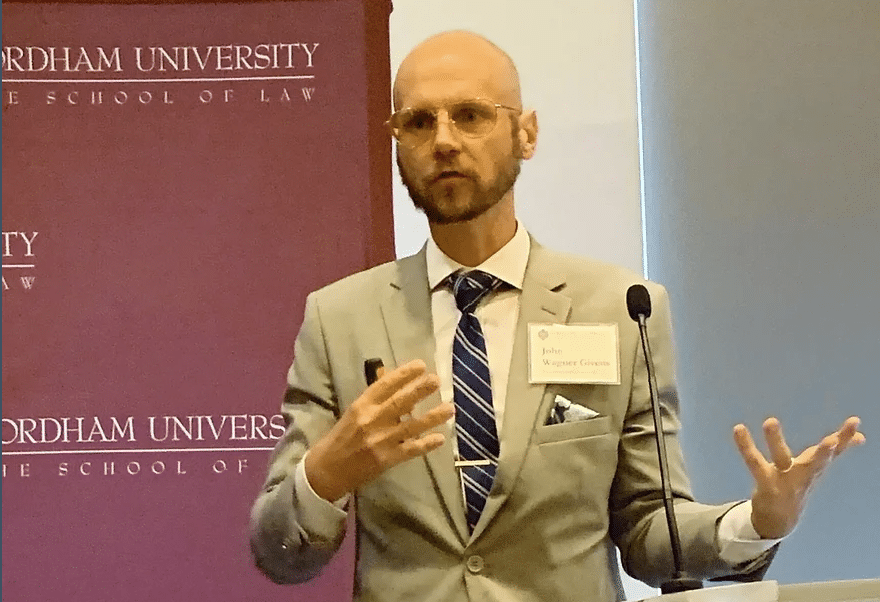确诊五十万,美国社会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作者:罗伯特·帕特南 来源:探索与争鸣杂志
编者按: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在美国愈演愈烈,截至4月11日,美国累计确诊已超50万例。此前,美股已经历多次熔断,国内市场陷入进一步动荡。美国社会为何会受到如此严重的冲击,应当成为有担当的社会科学研究者的案头议题。本文中,帕特南教授指出,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始,美国的社会资本结构运行并不顺畅,美国人的社会连接成为国内面临的重要问题,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孤岛”上的个体。不仅如此,由于美国贫富差距的加大,由此形成的阶级隔离也日益严重,“美国梦”目标的实现似乎愈加困难。同时,帕特南教授也说明了社会资本的衰落如何会影响到人们的健康水平。本文原载《探索与争鸣》2019年第3期,值此之际,本公号重新编发,以供诸君思考。
如果你们读过我任何一本书,《让民主运转起来》《独自打保龄》或者《我们的孩子》,那么对于我接下来要讲的,你们并不陌生。
事实上,当我初次听到社会资本这一术语时,我的学术生涯已经人到中年了。在过去三四十年间,关于社会资本的研究,始终是全世界社会科学最红火的领域之一。当我开始就社会资本进行写作之时,当《让民主运转起来》出版之时,人们几乎对社会资本这个词闻所未闻。那时候,每过两三年,也许会有一篇关于社会资本的论文发表出来。而现在,每两三个小时,就会有一篇社会资本的论文发出来。所以说,这个领域真是今非昔比。为什么会这样?原因在于,社会资本这个同我的研究交织在一起的概念,被证明是极其重要的。
一
当我说社会资本时,我是指社会关系网以及与此网络相伴而生的互惠和信任的交往规范。那我所说的互惠又是指什么呢?互惠的意思也很简单。我现在帮你一把,却并不期待你现在就回帮我,因为生活仍在继续,你将来某时会帮我忙的,或者说你帮了他,而他又帮了我。所谓普遍互惠,就是说你愿意对他人施以援手,而不必担心他们紧接着要以何种行为来回报你,因为你们所有人都在同一个关系网中。
关于社会资本,核心的教义就是社会关系网很有价值。首先说,对于身在关系网中的人来说,网络有其价值。这方面的例子很多。如果你处在某个关系网中,你就会因你人在网中而获益。举个例子,在这个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大多数人,他们是怎么找到工作的,并不是因为他们知道多少事,而是因为他们认识多少人。我所讲的,可不是腐败。我只是说,大多数人找到工作,并不是通过互联网或者报纸。大多时候,你得知某个工作机会,是通过你的朋友或者朋友的朋友,或者由此让工作找到了你。比方说,某人正准备雇用一名新的电脑程序员,而他跟一位朋友提到此事。接下来,朋友又将这事讲给了另一个人,而那个人恰好又认识你。于是他们说:“我的天,我刚好认识一个人,他应该适合这份工作。”社会关系网的效应非常强大,芝加哥大学商学院的一位学者就曾做过一项研究,根据美国人一辈子的收入来计算他或她的朋友圈的金钱价值。你有多少好朋友,你就会有多少工作。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朋友的金钱价值要高于学位的金钱价值。这么说吧,你们为什么要到北京大学来,不是因为你在课堂上能学到什么,也不是你在这里读什么书,而是积累社会资本。当然,对于个人来说,社会资本还有许多其他好处。我们过会儿再回到这个问题。
社会关系网还会惠及局外人,也就是那些不在关系网络中的人。美国、英国以及许多其他国家的研究都证明了这一点。大多数国家都是如此——要预判一个邻里社区的治安状况,最贴切的指标并不是执勤警察的人数。那是什么?是多少人可以直呼他们邻居的名字。社会资本可以阻止犯罪!罗斯玛丽和我住在一个紧挨着哈佛的社区,那里满满都是社会资本。在我们的邻里社区,人们永远在野餐,在烧烤,在聚会,总之有着各种各样的社会连接。这就说明我们的社区存在充裕的社会资本。我并没有参与邻里的社会资本,我经常不在家,但因为关系网络具有外部效应,我也能从中获益。这么一看,社会资本太强大了!还能举出许多例子,每一例都可以证明,从社会连接中获益的并不仅限于关系网络中的人。那些富含社会资本的地区,就拥有密集的社会关系网,也因此可以形成好政府。人们生活在这样的地方,即便他们自己并不加入某些组织或参与俱乐部的活动,也能享有好政府。社会关系网存在整体的、间接的或者外部的效应。研究已经表明,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事实。
让我们说说各种形式的资本。物质资本就是某种工具,像一把螺丝刀。如果你省吃俭用,买了一把螺丝刀,有了这个工具,你就可以更快地修理更多的自行车。大多时候,物质资本被用于做好事。当然,你也可以拿起螺丝刀去为非作歹。任何工具,你都可以用来做坏事。物质资本还是那件工具,只是用在了不好的目的上。社会资本也是如此。我并没有说社会资本总是好的。我所说的只是,社会资本总是很强大,而且经常被用于做好事。研究结果表明,就经验层面而言,对于我们所关心的许多事,社会资本是一个重要的预测指标,有了社会资本,生活经常会更美好。
我已经向你们讲述了社会资本。社会资本越多,则地方政府越好。同样成立的是,某区域内社会资本增幅越大,则孩子们的学业就越好。作为一项指标,社会资本可以有效地预判出教育成绩。如果你对学校的教育质量感到担忧,你可以提高教师的薪酬,也可以增加社会资本。我告诉你们,增加社会资本是更好的选项。社会资本还有助于经济绩效。社会资本可以降低犯罪率,减少偷漏税。它还能促成更有效率、同时更少腐败的好政府。在这里,我还要多说几句。社会资本还是身体健康的预测指标。知道这一点,真的很重要。加入一个团体,那么你在接下来一年死亡的几率会减半;要是加入两个团体,几率会减少3/4。这不是只对美国人应验。我想在其他国家也同样成立。孤单生活,同吸烟一样,都是造成过早死亡的巨大威胁因素。所以说,如果你既抽烟,又没有加入任何社团,那到底什么是健康杀手,还真说不定呢。且听老人言,如果你没法戒烟,那怎么着也要加入两三个社团,弥补身体这本钱!
我能听到,你们中有人在说:“得了吧,鲍勃,同他人交往可以有助于健康,这怎么可能呢?”答案之一就是我们所说的“社会支持(social support)”。说得明白些,如果你有很多朋友,当你生病时,就会有人给你送来鸡汤。或者说,当你老了,你摔倒在浴缸里,要是你有朋友的话,就会有人来照看你,救你这条老命。所以说,原因说简单也简单,同朋友保持联系,就提供了社会支持。但答案还不止于此,还有一部分原因是生理性的。放眼今日学界,关于社会资本和公众健康的研究,最有意思的关注就在于社交互动同生理学也就是人体机能的关联。
研究结果表明,同其他人待在一起,尤其是同我们认识的人在一起,会改变我们人体的机能。它构建起专业人士所说的“压力缓冲区”(stress buffers)。同他人更多交往,就会让你的身体更能适应来自环境、细菌等的威胁。有些研究非常有趣,它们证明,你的朋友越多,那你得感冒的几率就会越少。为什么会这样?你的朋友越多,那你就越有可能接触到细菌。但更重要的是,如果你有更多的朋友,你身体的生化机能就会发生变化,你体内就会产生更多的保护抗体。
现在我得澄清一下,我是一名政治学的博士,可不是医学博士。所以说,我刚才所讲,并不是告诉你们“快点加入两个团体吧,然后就万事大吉了”。我说的是,科学研究已经找到了非常有趣的有力证据,也发现了新的证据,表明我们从生理构成上就是社会性的存在。我们作为一种生物,从构成上就是要同他人在一起。这么说吧,如果我们不太同他人相处,那我们的身体会变得不健康。老年人尤其如此。老年人更容易孤独,这是严重的危险。现在你们知道,为什么我总是要紧跟着我的妻子罗斯玛丽了吧。
社会资本有不同的类型,正如人力资本有不同类型一样。人力资本只是指培训和教育。所以说,从本地汽修学校拿到一个文凭,或者从北京大学获得一个学位,会增加你的人力资本。
上面打的这个比方并不是说,你在北京大学获得人力资本的提升,就会帮助你修好汽车的瘪胎。不同类型的人力资本,是用于不同目的的。社会资本亦是如此。关于不同类型的社会关系网,不同类型的社会资本,最重要的区别之一就在于社会连接的不同,有些社会关系网是将我同像我一样的人联系起来,而另一些连接则是将我与不同于我的那些人联系起来。第一种资本叫粘合性社会资本(bonding social capital),它将我同其他白人、男性、老年、美籍、犹太裔的教授们联系起来。第二种是连接性社会资本(bridging social capital),我要是有这种资本,就意味着在我的社会关系网中,可以发现不同世代、不同种族、不同社会阶级、不同性别的人。
做出这样的分类,我不是说连接性社会资本好,而粘合性资本就不好。要是你生病了,为你送来鸡汤的人,来自你的粘合性社会资本。我们所有人都需要大量的粘合性社会资本。我们需要同我们一样的人。但问题是,在一个多元化的现代民主国家,连接性的社会资本确实更重要。要有社会纽带,将我们与不同种族、不同社会阶级、不同性别或者不同国籍的人们联系起来。生活在现代世界,所有这些连接性的纽带都至关重要。
到此可以说,我们需要粘合性的社会资本,我们也更需要连接性的社会资本。但难题是,培养粘合性的社会资本易,而培养连接性的社会资本则难。我祖母就明白其中道理。英语有个谚语妇孺皆知,即物以类聚/人以群分(Birds of a feather flock together)。意思很明显,羽毛颜色相同的鸟儿会待在一起。我祖母当然不知道什么是社会资本,但是她明白,培养连接性的社会资本要比粘合性资本难得多。
所以说,对于今天的美国来说,真正的大问题,几乎是所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并不是我们到底有多少粘合性的社会资本,而是我们所有的连接性社会资本还剩下多少。
二
在意大利,我待了25年。在那25年中,我认识到一点:社会资本很重要。是什么指引我找到下一个研究题目的?首先不是学术兴趣,同我作为一名政治学者的研究旨趣无关,而同我身为一位美国公民的利益息息相关。1994年前后,我发现美国民主陷入很麻烦的境地。大约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民主就其运转而言就从来没好过。美国人变得越来越不信任我们的联邦政府。
当时,我脑海中蹦出个念头,我此前作为一名学者在意大利研究的题目——社会资本,会不会同我作为一名公民回到美国后所关注的现象存在关联。刚开始时,这个想法只能说是很模糊。我对自己说,好吧,如果在意大利,社会资本构成民主的重要条件,那么怎么解释我们美国政府运转不良,原因也可能在于从1965年到20世纪末,我们的社会资本也在衰减。
但问题是,我没有任何证据来证明这一假设。接下来发生的事就如我的生活往常一般,很幸运,罗斯玛丽把我从困境中“拯救”出来。你们要知道,当时,美国最常见的社会组织形式就是我们所说的“家长-教师协会”。就是那种在学校里把家长同教师联系起来的团体,这是一种非常常见的组织。当我们的孩子还在上学时,我同罗斯玛丽都参加了家长-教师协会。而我一直想当然地认为,这类组织总是在发展壮大。
直至某天早餐时间,罗斯玛丽递给我一份报纸:“瞧瞧这个,我们这里的家长-教师协会的成员人数一直在下降呢。”于是我们开始讨论这个问题,我也很好奇,这种现象是不是只发生在我们镇上。我们发现,整个美国,家长-教师协会的会员数都在下降。那么其他组织又如何呢?比如说男童子军和女童子军。结果让我们大吃一惊,从1964年开始,童子军的人数也一路下降。那些朋友团体又是什么样呢?在美国,所有的男人组织都以动物来命名,比如雄狮会,驼鹿会,麋鹿会,雄鹰会,还有浣熊会。结果表明,所有“动物俱乐部”也都出现会员流失的情况。
有一天,我同一位老熟人共进午餐,他是全美最大的连锁保龄球馆的老板。你们知道保龄球怎么打吗?在美国,它是非常受欢迎的游戏。打保龄的美国人,要比在选举中投票的还要多。因此保龄球是个大生意。我给他讲了我的研究发现,美国社团都在流失会员。他告诉我:“鲍勃,你发现了我们这行面临的主要经济难题。没错,打保龄球的人数在上升,但麻烦是,成群结队的球友却越来越少。”在我小时候,大多数人是成群结伴去打保龄球的。也就是说,人们聚在一起,五人组成一队,同另外一支五人队一起比赛。
我这位朋友的经济难题就是,如果你组队打保龄,打联赛,那你消费的啤酒就是单人打保龄时的四倍之多,经营者从哪里赚钱?钱在啤酒里,而不是球和球鞋上。所以说,他现在的处境说来也奇怪,光顾保龄球馆的顾客越来越多,但营业额却不升反降。后来,我把这个故事转述给另一位朋友,他这么说:“哦,那你的意思是我们更常去打保龄,但却是在独自打保龄。”我当时就想,多么好的一个题目啊!所以这就是《独自打保龄》书名的由来。说真的,这不就是这本书最精彩的地方吗!
当我开始研究美国社会资本的状况时,我收集了大量的证据。在这里,我要给你们坦诚当时的感觉,一开始,我当然不知道这研究将会通向何方。开始时,我只不过是想要搞清楚美国正在发生些什么。但证据却每每让我感到震惊:那些我曾经以为人人都有的社会关联,全都开始萎缩甚至于枯竭。
要想测估社会关系网的历时变化,最简单的方法,不是唯一的方法,就是去测估社会组织。但务必要记住,社会资本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有很多并不是组织。比方说,有一群同事,每周五都出去喝酒或去图书馆,读书或者一道做点其他事,这就是社会资本。但这不是组织,只是人们聚在一起而已。在上海时,我看到一大群老年人在公园里跳舞。那就是社会资本。记住,它不是组织,但它构成了一种社会关系网。
我们之所以关注组织,是因为许多组织都保留了它们的成员记录。所以说,你可以向前追溯一段很长的时间,找到某个组织历史上曾有多少名成员。我有一张图表,其数据包括了美国32个不同组织的人员规模变动,时段覆盖了整个20世纪。从该图表中,我们可以读出,在某一组织所覆盖的人群之中,到底有多少实际上加入了该组织——比方说,全部孩子中加入男童子军或女童子军的到底有多少,所有中年男子中加入某一家“动物俱乐部”的又有多少,所有女性中加入妇女组织的又有多少,全部黑人中加入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又有多少人。
自20世纪初年起,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组织。只有一个例外时期。在大萧条期间,平均而言,美国各类组织在五年内流失了过半数的成员。大萧条对社会联系的杀伤力极大。但随着整个国家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走出萧条,特别是在二战期间以及战后,美国很可能迎来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组织繁荣。
每年,每一个组织都在吸收更多的成员。当然,美国人口的基数也在变大,但重要的还在于,加入组织的人数比例越来越高——更多的孩子加入童子军,更多的父母加入家长-教师联谊组织,更多工人加入工会⋯⋯越来越多。直至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和70年代,突然、悄然且诡秘地,所有的美国组织都开始经历人员规模的缩水,成员数先是减少,然后暴跌,最后是断崖式的下降。
每一个组织都知道,它的成员在不断流失。当成员开始离散时,每个组织首先说的是:“我们要改变一下做事的方式了。我们要找到更有本事的人,让他负责招募会员;问题出在我们的组织上;也许我们要拿出更好的活动方案。”但如果你环顾整个美国,却发现每一个组织似乎在一夜之间都染上某种怪病,这可能性有多大呢?不大可能吧,因为这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
我已经描述了组织成员人数的走势。但总有理由告诉我们,以组织来测评社会资本,并不是一个完美的指标,有可能我在采样时就没有选对组织呢。而且我在前面也说过了,并非所有的社会资本都是组织化的。也有可能,人们参与俱乐部活动更少了,但外出野餐聚会却更多了。我们不仅要看社会组织,还要考察组织以外的许多形式的社会资本。
于是,我们观察了美国人参与公共聚会的发展趋势。我们发现了一整套此前被尘封的民意调查,连续25年,每年都有问卷和数据。该民调表明,在20世纪70年代,回答说此前12个月中曾参加过公共聚会的,约占全体美国人的23%。到了我们开始研究的1995年,同比数据下降到12%。现在更是降到了8%。事实上,就在最近几个月,这一数字略有小幅上扬。
再看看普通美国人每年参加俱乐部聚会的次数。这一数据覆盖了所有类型的俱乐部聚会,而不只是我挑选出的俱乐部。20世纪70年代,美国人平均而言每个月都要参加一次俱乐部聚会。但到了20世纪末,这一数字下降到每半年一次。而时至今日,大多数美国人压根不会去参加什么俱乐部活动。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家庭娱乐中。美国从前曾有一种生活中的习惯,我们叫“晚餐派对”。但现如今,这种习惯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美国家庭内的晚餐,也大致如此。在美国,家庭晚餐曾经是再普通不过的事,但现在却难得一见。所以说,哪怕是在家庭内部,我们同其他家庭成员的联系也在减少。
再看看美国人是变得更慷慨,还是更吝啬吧。这个指标关注的是我们每年从个人资金里捐出多少来。20世纪前半叶,美国人,无论富有还是贫穷,每年多少都会捐出一些钱来做公益。整体上,人们捐出的钱越来越多,一直到1964年,又是个拐点,从此后美国人开始越来越自私。与此相关,我们美国人不再信任彼此了。我在这儿不会展示所有的细节,但大体而言,美国人的社会信任度,也即你是否相信他人,出现了急剧下降。在被问及这个问题时,此前大多数美国人会给出肯定的答案,但现在大部分美国人却只会说不。
现在我们需要总结一下。首先,社会资本有着许多类型和形式。其次,社会资本很重要。再次,回想下《让民主运转起来》,社会资本看起来极其稳定,500年的时间内都不变。然而,在我算长但也不那么长的人生历程中,我却看到了美国社会资本的崩溃。《独自打保龄》出版后,我获得了许多关注。为什么人们的眼球都紧盯着《独自打保龄》?为什么突然之间,全世界都在谈论《独自打保龄》?不是因为我多么聪明,而是完全出于偶然,我撞上了所有美国人都知道正发生在他们生活中的事情。
他们知道,若是同父母一代相比,他们的社会联系不再紧密了。但他们曾经在心里想过,认定这是他们个人的过错。也许他们的爸爸妈妈是真正的社交好手,但他们却很懒惰。聚会就在那里,只是他们不愿意去。但现在,来了这么一位哈佛的教授,告诉他们:“这不是你的错,全国上下,都是如此。所以别担心。”但讲真的,我在担忧,不是担心你,而是担心我们所有人。我们失去了连接。
三
最后,我要跟你们简单聊聊我最近写的一本书:《我们的孩子》。这本书提出了一个问题:在我已经谈到的社会变革同美国孩子的生活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联?
在今日之美国,不仅有民主的衰落,不断加剧的政治极化,日益衰减的社会资本,还出现了经济不平等的加剧。接下来,我将给你们展示一幅大图景,概括出美国社会在过去三四十年发生的转变。
现在你们想象下,将所有美国人在这里排成一队,根据他们所占有的财富,队伍的那头站着最有钱的,比尔·盖茨就在那头;然后,在队伍中间就是普通的美国人;再接着就是穷人;最后是无家可归的穷光蛋。那么在过去40年中,美国人的收入分配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位居排头的美国人变得更加富有;而落在队尾的则穷到了无家可归;位居中间的美国人,变得越来越少。
从历史上看,美国人对经济不平等一向怀有摇摆不定的态度。不同于某些西欧国家,或者也同中国不一样,要是某些美国人占有巨额的财富,我们并不会感到太困扰。因为我们是这么假设的:人人起步于同一个起跑线,你成功了,取决于你的能力,还有你比别人更努力。美国人最在意的是,我们的人生应该从同一个起点出发,而不是我们应该到达同样的终点。
当美国成为一个独立国家时,我们向全世界宣告的第一件事便是,我们相信人人生而平等。这就是美国梦了。你在美国能过上什么样的生活,应当取决于你自己,取决于你的劳动和能力,而不看你父母是谁,做了些什么。而我现在要告诉你们,美国梦正变得越来越不真实。
在美国,收入分配的不平等越来越严重。阶级隔离也在加剧,什么叫阶级隔离?我是指富人只跟富人居住在一起,而穷人也只和穷人一起住。至于那些贫富混居或者中等收入的社区,早已越来越小,居民也越来越少了。所以说,问题还不只是我们能有多少收入,而是我们能同哪些人关联起来。社会阶级的隔离日益加剧,这就意味着富家子弟上富人的学校,身边同学是同样的孩子;而寒门子弟上穷人的学校,同学都是穷孩子。这边,穷孩子要去读穷学校;而另一边,富家子弟就去读好学校,这就意味着他们仅仅接触到其他的富家子弟。社会阶级的隔离还会决定我们同谁结婚。富人家的孩子只会同富家子弟结婚,因为他们平时就在一起。反过来说,穷孩子就只能同其他穷孩子结婚。这可是一个大问题啊!美国社会从前并不是这样子的,过去贫富之间常有跨阶级的婚姻。
我希望你们可以看清楚现在的状况。出生决定命运,命运可以继承。你出生在市镇的什么地方,就会生活在那里,也在那里上学,也就意味着你的孩子也是如此。要是出生在穷人区,你就只能同穷孩子生活在一处,只能去读穷学校。假设你能结婚,那也只能找到门当户对的穷家孩子。同样真实的是,在市镇富人区的那一边,社会资本仍然存在。家庭还维持着传统的结构:妈妈、爸爸和孩子们。在富人区,95%的孩子同他们的父母生活在同一屋檐下,因父母离婚而成长在单亲家庭的只有5%;但在同一市镇的穷人区,大约70%的孩子要在单亲家庭中长大。这无关乎种族,不是肤色黑或白的问题。在美国生而为穷人,就是如此。想想看:美国大多数穷孩子都生活在单亲家庭,而且人数越来越多。
一般而言,他们会有一位单身的妈妈。谴责妈妈无济于事。如果要指责谁,我也会怪在爸爸头上。但问题是,如果家里只有一位成年人,那么养育孩子就要困难许多。单亲家庭在穷人生活中成为常态,就导致了一个严重的后果:穷孩子所能获取的资源,不仅是经济资源,还包括社会资源,同富家子弟所能掌控的,不可相提并论。所以说,在今天的美国社会,你们可以看到各种各样我所说的“剪刀差图表”。在图中,顶部一条线代表富人区的生活,而底边另一条线则展示出穷孩子的人生。结果表明,富家子总是好上加好,而寒门子弟却每况愈下。
事到如今,我们美国人可以做的事很多。要是我认为无法解决这个问题,我大概就不会写《我们的孩子》了。我们美国人要开始有忧患意识了,如何做才能缩小富家子弟和穷孩子的差距,不仅是经济的鸿沟,还包括社会资本的天壤之别。原因在于,这一边的孩子们,我的孙辈儿女,拥有许多人生导师。老师关心着他们,父母疼爱他们,教会里的牧师指导他们,邻居也喜欢他们。但在距此不远的市镇另一边,穷孩子却是孤单无援的。
这些孩子没法信任父母,因为他们的家庭早已破裂。他们没法信任邻居,因为他们居住在危机四伏的社区内。他们没法信任自己的学校,因为他们上的是不伦不类的学校。他们没有教练可以信任,因为他们连课外的体育运动都没机会参加。他们灰心丧气。他们不相信任何人。在写作《我们的孩子》时,我们曾访谈过一位年轻女孩,她在“脸书”上说:“爱,只会受伤;信,令你死亡。”想一想吧,在青少年阶段无法相信任何人,这样的成长意味着什么。这不仅伤害了这些孩子,也是我们这个国家的失败。我们为何走到今天这地步?回到20世纪50年代,当我在这个国家长大时,我生活在美国中部农村地区的一个小镇。那是一个适于长大成人的地方,在经济上算不得富足,但生活中满满都是社会资本。
当我的父母提到“我们的孩子”这个词时,他们总是会说:“我们的孩子需要一个游泳池。”他们说这话的意思,并不是要为姐姐和我修建一个游泳池。在他们的口中,“我们的孩子”这个词,指的是镇上所有的孩子。也许镇上所有人都要多交一点税,这样我们就可以在高中修建一个游泳池,为了镇上所有的孩子,每一个孩子。然而在过去三四十年间,“我们的孩子”的语义在美国已经大大缩水了。
现在,当人们说起“我们的孩子”,他们所指的只是他们自己生的孩子。当人们谈及生活在镇上那一边的孩子们时,他们会说:“好吧,这太糟糕了,但这不是我的问题。他们不是我的孩子。问题出在别人身上。”这样的想法,恰恰就是问题之所在。我们已经开始了一种大变迁,告别了这个“我们”的社会,而进入一个“我”的社会。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看起来更为艰巨,也更棘手。
但到此,我还是要提出一个更普遍的观点:每当进入经济和技术快速变革的历史阶段,社会中就会弥漫着严重的焦虑,不平等日益加重。如任其恶化下去,就会感染到下一代人,事态就愈加恶化。这不公平,在经济上也是无效率的。
不仅是美国,同样的趋势也发生在今日世界上的许多国家。但追溯美国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在某些时期,美国人也曾面对同样的问题。世界看起来一片灰暗,接下来我们就要着手修正这个问题,就要开始向积极的方向去努力。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我仍在努力推动历史上曾发生过的变革可以重新出现在美国。但对于社会科学家来说,要想明天会更好,就要求我们认真对待我们的职责,不仅是做好的、富有挑战的、经验性的研究,而且要求我们认真对待研究选题,选择那些可以切实帮助我们的公民同胞的研究选题。
来源时间:2020/4/18 发布时间:2020/4/11
旧文章ID:213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