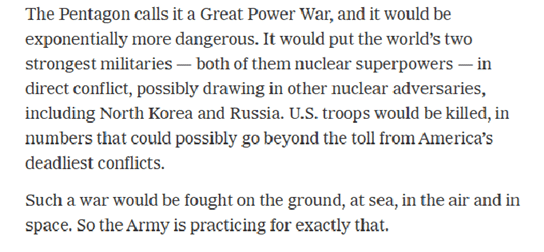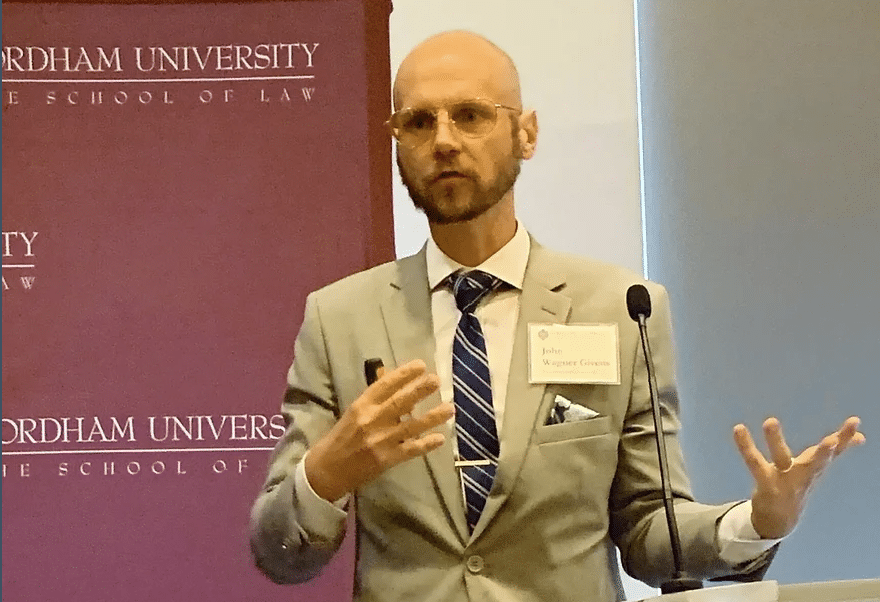于滨:美国对华政策中的“文明”问题
作者:于滨 来源: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
内容提要: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政治的泛种族化愈演愈烈。美国国务院前高官斯金纳在文明/种族层面界定美国对华政策,为双边关系注入新的不稳定因素。本文以20世纪初美国国际关系研究为切入点,考察百余年来文明/种族问题在美国内外政策中的特定含义,梳理二者之间的共生(symbiotic)现象,进而探究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地区研究和对华政策中更为深层的观念。种族问题在美国内政外交中表现出的韧性和力度,既源于历史沉积,也有强烈的人工塑造的痕迹。在美国高度意识形态化和日益种族化的话语体系和决策观念中,改善中美关系的难度极大。对此,中方应未雨绸缪,对未来双边关系继续恶化做好充足的心理准备;同时冷静应对双边关系已经开启的长期震荡和低谷期,继续推进文明对话,以期减少文明/种族因素对中美关系的影响,为未来改善双边关系创造条件。
关键词:中美关系、国际关系、文明冲突、泛种族化、冷战
突破中美双边关系的底线,使本来就相当脆弱的中美关系日益滑向“修昔底德陷阱”。不仅如此,特朗普团队欲“高屋建瓴”,将世界上两个最大国家之间复杂的共生/互动关系,推向所谓“文明冲突”(即种族冲突)的不归之路。
一、斯金纳的“文明”“快闪”
2019年4月29日,时任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主任凯伦·斯金纳(Kiron Skinner)表示:美中之间的竞争是两个文明和两个人种之间的斗争,是美国从未经历过的。为此,她所主持的国务院正在制定一项类似冷战期间由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提出的对付苏联的“遏制”战略,以便应对中国这样一个“非高加索人种的强大竞争对手”。相比之下,冷战期间美国与苏联的竞争不过是“西方家族的内部之争”。
一位非洲裔女性外交高官从白种人的视角出发,透过具有强烈种族色彩的所谓“文明”棱镜来审视世界两强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不仅在美国外交史上前所未有,即便在当下“政治正确”占主导的美国外交圈内,也是一个匪夷所思的现象。对此,美国政治精英的反应相当复杂。斯金纳的论点虽得到一些极右人士的支持(如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等),但在华盛顿圈内却遭到了几乎一边倒的批评。除了难以认同斯金纳露骨的种族主义和蹩脚的历史观以外,建制派还担心“文明冲突论”不仅不利于团结非西方盟友共同遏华,还会弱化美国对世界的道义感召力。建制派最为忌讳的是,“文明冲突论”会给人以某种印象,即美国与同为白种人的纳粹的关系远超其与中国的关系。斯金纳的“大战略”虽颇具争议,但却很快淡出公众视野,支持者和反对者似乎都无心恋战,斯金纳本人在2019年8月离职前也从未公开回应众多的质疑和批评。她在任时鼓吹的“文明冲突论”会在多大程度上体现在美国国务院的对华大战略中,人们还要拭目以待。
然而这番“斯金纳快闪”还是揭示了美国外交理念中一些深层问题。多年来,“种族”在美国外交中一直是一个被刻意回避的符号。在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1993年发表的《文明的冲突?》中,其论断主要基于宗教、文化、历史和语言等因素,未直接涉及种族问题。2001年“9·11”恐袭事件后,“文明冲突论”盛行一时。即便如此,小布什政府顶住巨大压力,拒绝将整个伊斯兰文明当作西方的敌手。亨氏文章问世四分之一世纪后,美国外交决策的最高智囊机构为何在对华政策上把文明与种族和肤色直接挂钩?这种以“文明”包装的“惊人的野蛮”是斯金纳本人的“无知”或心血来潮,还是美国对华政策中更为深层的理念和战略焦虑的表露?是特朗普及其团队的独有现象,还是具有更广泛的、超越时空的政治文化基础?中美建交40载,双方在经贸、社会、文化等方面深度交融,如果美方执意将种族问题引入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那么这一变量在对华政策中将如何操作(operationalize)?当年凯南提出的对苏“遏制”战略,在他本人看来是在“绥靖”与第三次世界大战两个极端选项中的第三条道路;以文明冲突主导美国对华大战略是否会排除凯南式的“妥协”?如此众多悬而未决的问题,不是斯金纳快人快语、说完走人就可以了结的。
有鉴于此,本文首先以美国外交和国际关系理论发展为切入点,考察百余年来文明/种族问题在美国内外政策中的特定含义,梳理二者之间的共生现象,进而探究美国对华政策中更为深层的观念。观察和分析美国高度意识形态化和日益泛种族化的政治生态,有助于应对中美关系已经开启的长期震荡和低谷期,也有利于把握中美双边关系互动的底线、方向和力度。最后本文在理论与政策的交汇层面,观察“斯金纳现象”与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地区研究和外交决策的互动关系。
二、种族的诱惑与尴尬
斯金纳将中美关系置于文明/种族层面探讨之时,正值种族问题在美国国内呈井喷之势,这与百年前的美国何其相似。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完成本土开拓并征服西半球,开始摆脱孤立主义,走向充满诱惑却又难以把控的外部世界。面对强国林立的“老欧洲”和广袤、动荡的非西方世界,刚刚起步的美国国际关系学(IR),却是以“种族”(即白人至上主义和信奉适者生存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为基准来透视复杂多变的国与国关系。在国际关系学者笔下,处于国际秩序顶端的是“文明”的欧洲人及美洲、澳洲和南非的白种人,最底层的是黑人,二者之间的是其他各色“野蛮”人种。在这一“文明”vs“野蛮”的等级建构中,有色人种“文明”程度的提升,必须由“宽宏大量的”(magnanimously)白种人加以“教化”才能实现。不仅如此,生物学上“劣等”的有色人种之间没完没了的冲突,需要白种人以武力加以控制。有色人种的这些秉性不仅使奴隶制、帝国征服、殖民主义和种族灭绝的行为名正言顺,也催生了为之理论化的国际关系研究,即事实上的“种族关系理论”(interracial relations)。
在那个种族至上(centrality of race)的时代,美国第一份聚焦外交问题的杂志1910年创刊时,取名为《种族发展研究》(Journal of Race Development),九年后更名为《国际关系杂志》(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1922年美国外交委员会将其确定为旗舰刊物,杂志再度更名为《外交季刊》(Foreign Affairs)并使用至今。与此同时,彼时的美国政治学被认定为美国白种人“最宝贵的财富”,很多政治学家极为崇拜纳粹德国高效率的统治机能。
20世纪初,当快速崛起的美国步入国际社会之时,所谓“文明问题”也充斥着“英语文化圈”(the Anglosphere),“文明”与“野蛮”被认为是西方(白种人)与非西方(有色人种)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然而这一“文明”讨论的背后,也有西方老牌殖民国家(英国)与新兴大国(美国)的利益交换:前者惧于德国的快速崛起,而且已经难以支配广大的殖民帝国;年轻而富有活力的美国则跃跃欲试,有意在西半球之外有所作为。英国作家吉卜林(Rudyard Kipling)在他著名的《白人的负担》一诗中,呼吁美国承担更多统治非西方的责任,以便把那些“半人半鬼”的“郁闷的侏儒们”提升到“文明”的水平。至少在英语世界中,文明与种族问题已成为一枚硬币的两面,相互衬托,不分彼此。
百年前美国学界对种族问题的执着有其特定的国内背景。南北战争以后,美国经济发展进入快车道,但在此后百年中,南方数以百万计摆脱奴隶身份的有色人种(主要是黑人)仍然生活在大规模的种族隔离政策的禁锢之中。对于主流社会来说,种族问题挥之不去,又无法摆脱,只能用“隔离”的方式冷处理,这在西方国家中是独一无二的。
英语世界以外,美国政治生态和社会的这一特殊建构也不乏魅力。比如,1933年德国纳粹上台之初,苦于无法名正言顺地“处理”大批犹太人和其他“劣等”族群(吉普赛人、残疾人等),美国以立法方式固化的种族隔离制度为其提供了一个现成的范本,具有很强的可复制性和可操作性。为此,德国在20世纪30年代派遣大批律师、学者和官员赴美,实地考察美国的种族隔离法,并以此为蓝本制定了针对犹太人的《纽伦堡法》(Nuremberg Laws)。
其实早在希特勒上台十多年前的1921年,美国官方就开始限制来自被认为是劣质基因的南欧和东欧移民,其中很多东欧移民是犹太人。1924年新移民法正式颁布,美国大幅度削减了来自东欧、南欧和亚洲的移民配额。根据丹尼尔·奥克伦特(Daniel Okrent)的新作《移民免入》,当时反移民的急先锋是美国东北部,尤其是波士顿和纽约一带热衷于优生学的各类精英,其中包括很多“进步”人士。时任美国副总统小卡尔文·柯立芝(Calvin Coolidge,Jr.)公开宣称,“生物定律”证明南欧和东欧人属于劣等人种。这一针对“劣等人”的歧视性政策延续了40余年,期间纳粹大规模屠杀欧洲犹太人,但直至二战结束,美国仍拒绝放宽对包括犹太人在内的东欧移民的限制。令战胜国异常尴尬的是,在纽伦堡审判中,很多纳粹官员都引用战前美国主导的优生学为他们的罪行辩护。
二战前美国与种族主义的不解之缘,似乎到1945年戛然而止。在美国国际关系学者笔下,二战后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基本上承袭了古希腊古典现实主义的精髓(即对实力消长和国家利益的关注),摒弃了欧洲学派的理想主义和对外政策中的绥靖主义;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等欧洲学者中的现实主义论者,只有在美国才得以安身立命,将其学说发扬光大;20世纪初,美国虽然也有美国版的自由主义(即威尔逊主义),但很快就被孤立主义所抵消。如此叙事,构筑了美国作为修昔底德两千余年以后西方现实主义真正传承者的地位,但却完全忽视了种族变量在美国早期国际关系理论中占据中心地位的历史,给人以一步到位的感觉。直到冷战以后,美国学者罗伯特·维塔里斯(Robert Vitalis)在麻省克拉克大学图书馆中,偶然发现20世纪初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初创时有关种族问题的大量文献。此前,只有美国历史学家迈克尔·亨特(Michael Hunt)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系统地指出种族主义在美国外交中不可或缺的作用,但这一批判性论点被完全淹没在西方赢得冷战的狂欢之中。
冷战结束后,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女权主义、建构主义异军突起,挑战传统的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范式,并迅速成为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部分,唯有种族问题仍不登大雅之堂。进入21世纪,个别学者开始论及种族在国际关系理论建构中的作用,但仅限于在对历史的发掘和评判,远远谈不上理论化。美国大学的国际关系教科书基本不论及种族问题,完全回避种族在美国早期国际关系理论建构中的中心作用。
对于美国国际关系学界,种族问题确实是一个难以启齿却又无法消除的历史痕迹(inconvenient truth),冷处理也许是唯一的出路。按英国学者苏珊·佩德森(Susan Pedersen)的话说,种族问题在美国国际关系学界“命中注定要销声匿迹”(destined to disappear)。即便在亨廷顿1993年发表的《文明的冲突?》中,也有意无意地排除了任何“种族”字眼。这种人工建构的种族“中立”表象,既漂白了自身污点,也占据了道义制高点。直至2016年底,美国政界和国际关系理论界再度为种族问题所缠绕。
三、2016年:“种族”归去来兮
2016年美国大选,种族问题回归美国内政外交主场。与以往不同的是,特朗普及其反对者都攻击对方为种族主义、法西斯主义和麦卡锡主义,且愈演愈烈。奥巴马执政的八年,虽然为黑人入主白宫首开先河,但也直接促成了白人种族主义的强力反弹。美国实行民权法案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受到压抑的白人至上主义情结,终于在2016年得以井喷式宣泄,特朗普“使美国再次伟大”的口号,至少在民主党及其支持者看来,是要使美国白人再次伟大。而在白人至上主义者眼中,美国的种族问题已经到了必须用暴力“解决”少数族裔在美国彻底取代白人的时刻。
(一)杰克逊主义回潮
在政策层面,特朗普政府反难民、反移民、反有色人种的激烈言辞与政策取向,被认为是典型的白人至上的杰克逊主义(Jacksonianism)。在美国的外交理论中,主流的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均来自“老欧洲”,美国开国之父的理念中多有欧洲启蒙思想的痕迹。有别于“老欧洲”的美利坚政治文化的真正成型,始于美国第七任总统安德鲁·杰克逊(AndrewJackson),他告别了欧洲色彩浓厚的精英主义,将其社会基础及合法性建置于美国殖民扩张时期不断驱逐、杀戮印第安人的“边民”大众(frontiersmen),这些白种基督徒极端敌视那些“没有德行”(dishonorable)的“危险的异类”(dangerousothers),即有色人种,必取缔之而后快。在对外政策中,杰克逊主义往往拒绝妥协,要么满盘通吃,要么洗手不干(all-or-nothing)。特朗普版的杰克逊主义也许难以复制早期赤裸裸的白人至上的种族主义,但他对有色移民、难民和中国人(包括华裔)粗言恶语,几乎不加掩饰。传统的杰克逊主义在21世纪似又以民粹的方式,露骨地表露其最原始的本能。
(二)“白化”国际关系学界的忏悔
2016年底特朗普胜选,美国主流媒体、建制派以致美国的整体价值观都陷入巨大的信任危机。然而很少有人注意到,美国国关理论界也经历了一次突如其来却又意味深长的反思。时任美国政治学会主席戴维·莱克(DavidLake)在2016年12月号的《政治观点》(PerspectivesonPolitics)上撰文指出,美国的国际关系学是由白人主导、为白人服务的建构(institution)。对于美国国关界这一持久的“白化”现象,莱克建议的解决方式是增加少数族裔和女性在国关专业的人数。
莱克希望美国国关学界多元化的动机也许不应被质疑,但其“智者的忏悔”(intellectual confession)和改革措施仅仅是对美国“白化”的国关界“掺沙子”,完全不涉及亨特早就指出的更为深层的认知体制(discursive system),这包括美国对外政策中对非西方社会持有的持久且无处不在的种族主义倾向。在亨特看来,种族等级观念与美国至上和仇视革命等信条,构成美国外交中三合一的意识形态。亨特的上述定义产生于冷战这一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冷战以后,美国进入为所欲为时代,在世界范围内不惜代价、不计后果地推进美式民主和自由资本主义,成为最具“革命性”和破坏性的国家,直接间接地削弱甚至破坏了二战后美国亲手打造的自由国际秩序。而美国至上论和美国例外论在相当程度上掩盖、取代了露骨的种族等级观念,成为美国在世界范围内摆脱国际义务、鼓吹单边主义的重要推手。
关于意识形态在美国政治生活中的作用,美国学者理查德·霍斯泰德尔(Richard Hostadter)有点睛之语:“美国作为一个国家,其命运不在于是否具有意识形态,美国本身就是意识形态的化身。”在此范式中,尽管美国学界允许相当大的自由度,个体学者可以在象牙塔中不问天下事,或纵论天下事,甚至可以公开挑战、批判民主和自由资本主义体制,但这些反体制的言论和著述很难进入国关主流,更不可能为外交决策界接受,注定要被边缘化。即便是对美国冷战战略有重大影响的凯南,一旦对美国外交的主流做法和论断提出质疑——如冷战结局、北约东扩、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等——都会被无情地边缘化;而鹰派的保罗·尼采(Paul Nitze)等总是主流派的宠儿。认知的高度一致,使得打造美国“自由霸权主义”的精英团队一直被禁锢在自我设定的范式之中。哈佛大学教授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Walt)于2018年底指出,尽管美国在后冷战期间战略性错误频频,但由于美国外交/国关领域的封闭性,美国外交基本无力自我纠错。如此强韧的意识形态建构,不是增加几个女性和少数族裔学者就可改弦更张的。
(三)身份认同与错位
事实上,在美国高度意识形态化和泛种族化的政治生态中,少数族裔和弱势群体的观念和行为常常发生扭曲和错位。奥巴马执政八年期间,种族矛盾持续恶化,以致在其任内的最后两年中,警方对少数族裔的暴力执法大幅飙升。对此,奥巴马离任前在华沙召开的北约峰会上居然闪烁其词,认为是智能手机普及之过。在美国正统意识形态稳居主导地位的政治生态中,少数族裔精英必须也只能认同以盎格鲁—清教徒(Anglo-Protestant)为主体的美国信条。同理,在美国国际关系的女权主义看来,女性是和平、务实的象征,可以从根本上改变男性主导的外交中穷兵黩武的秉性。但在美国的外交实践中,冷战结束后的几位女性外交高官却都是典型的鹰派,如国务卿奥尔布赖特(Madeleine Albright)和希拉里·克林顿。
除了斯金纳以外,在身份认同上严重错位的还有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苏珊·赖斯(Susan Rice)。2019年7月15日,赖斯在其推特上指责中国驻巴基斯坦外交官赵立坚是“可耻且极度无知的种族歧视者”,起因是赵在推特上批评美国社会广泛存在的种族问题,尤其是在住房方面。对此,赖斯甚至要求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把赵立坚送回中国。赖斯作为政府前高官,挺身捍卫美国在国际社会的道义制高点,可以理解。然而将批评美国国内种族主义的行为本身界定为种族主义,却表露了赖斯在认知上的巨大偏差。美国的族裔关系经过南北战争、民权法案、黑人总统,确有巨大进步;但美国社区仍然“黑白分明”,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如果美国之外的人对这些都熟视无睹,赖斯又是否会批评他们是美国种族隔离的事实帮凶呢?
(四)冷战与族裔
赖斯在身份/种族问题上的认知错位源于其对历史的无知。作为非洲裔并且在冷战期间修完大学历史专业的斯坦福高材生,赖斯应该明白,处于种族隔离状态的黑人等少数族裔,正是在冷战期间获得了更为人道的待遇。2003年,在美国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Jr.)《我有一个梦想》演讲发表40周年之际,笔者曾撰文指出,与苏联争夺道德制高点的意识形态之争,迫使美国政治精英很不情愿地废除了该国的种族法律。艾森豪威尔总统和肯尼迪总统都意识到,美国的种族隔离制度削弱甚至破坏了美国的外交政策。他们心照不宣的是,除非美国采取行动,废除那些针对本国有色人种普遍存在的种族歧视行为,否则美国将无法说服和指令世界其他国家效仿美国模式。应该指出,冷战期间美国精英阶层这些言行变化,并非完全出自内心,而是不得不为。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如里根和尼克松)对少数族裔和非西方世界的观念,仍然停留在20世纪初的种族决定论,只不过不便公开表露罢了。尽管如此,冷战在客观上迫使美国人开始脱离自私自利的原始和本能状态,至少做到在法律层面平等对待少数族裔。赖斯本人的成长也受惠于美国在冷战期间不得已而为之的政策。
冷战结束后,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处于国际体系之巅峰,不再受到任何限制。与此同时,美国在伦理和道德层面也傲视全球,既无必要更无压力再去与他者竞争。事实上,冷战结束后不久,美国国内就对平权运动(Affirmative Action)产生了“疲劳感”,认为多元文化是“矫枉过正”。这些思潮最终助推特朗普赢得2016年总统大选。与此同时,主流社会对穷人和弱者变得越来越缺乏耐心,越来越苛刻,以致白宫的“颜色革命”(即奥巴马就任总统)甚至加快了美国种族不公正现象的回归,比如越来越多的黑人被白人警察枪杀。对此,俄罗斯问题专家杰弗里·曼科夫(JeffreyMankoff)最近指出:“如果没有意识形态上的竞争对手来促使其反省自己的错误和虚伪,美国历史上一些更丑陋的部分就将卷土重来。”曼科夫的警示不幸言中。对此,亨廷顿在冷战结束几年后哀叹道:“没有冷战,作为美国人还有什么意义?”
身为非洲裔的美国外交高官,斯金纳将中国与文明/种族问题挂钩,这不禁打破了一个世纪以来美国外交和国关理论界淡化种族问题的“禁忌”,对世界文明史(或不文明史)也是一个巨大的讽刺。但以美国的少数族裔人士挑起与中国的“文明”之战,在美国的政治语境中不仅是一个可以理解的“非理性的理性行为”(rationality of irrationality),而且在一定意义上可能是对抗中国更有效的手段。正如在美国政治正确的语境中,保守派往往启用少数族裔人士,批评自由派的平权和扶持弱势群体的措施。同理,像章家敦(Gordon Chang)这样的华裔评论家,多年宣扬“中国崩溃论”虽未见其效,但其“优势”在于其华裔身份本身,加上逢中必反,确保了章在美国公共空间中拥有一席之地。
如今在美国的集体意识和观念建构中,中国作为西方和基督教文明以外的国家,其快速崛起之路既是无法解释的,也是不可理解的,因此它一定是不可预测的,甚至是危险的。在这个意义上,斯金纳一语道破的不仅仅是“惊人的野蛮”,而且表明至少部分美国精英已经将对华关系上升到文明/种族冲突的层面。他们也许自认为是亨廷顿的得意门生,有志于复制凯南式的宏大的遏制战略,但却自觉或不自觉地坠入种族冲突的陷阱,而这恰恰是美国政治和知识精英百年来力图忘却和极力漂白的一段难以启齿的污点。斯金纳作为美国知识精英中的一员,又身处美国外交决策部门,也许在事后才意识到自己对历史惊人的无知和健忘,不得不选择以沉默对待所有批评。
四、国关理论,地区研究,美式“旋转门”?
即便是在泛种族化的政治环境中,斯金纳的文明/种族论还是语惊四座,她对“高加索人种”的苏联的偏爱更是让人印象深刻。致力于研究冷战后期美苏关系的斯金纳应该意识到,冷战期间美国国关理论界也怀有类似的“重俄轻华”(Russia-heavy-and-China-lite)情结。
在国际关系理论层面,冷战作为一个特殊的国际体系,实际上确认了苏联这个共产主义大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合理地位。如肯尼思·沃尔兹(Kenneth Waltz)认为,两极体制的稳定性要远远优于单极和多极体制,充分肯定了苏联对国际体系稳定的贡献。约翰·加迪斯(John Gaddis)著名的“长和平论”认为,相对于多极和战乱不已的20世纪上半叶,在美苏主导的两极体制中,双方都遵循一系列成文或不成文的行为规则,这包括尊重彼此势力范围,避免直接军事对抗,承认核武器的不可使用性,不在对方领导层危机时(领导人正常或不正常死亡时)落井下石等。对此,加迪斯指出:
“[冷战体制的]稳定需要双方都采取某种审慎、成熟和负责的态度。这要求双方都有能力辨别对方的行为是领导人惯用的虚张声势,还是真正的挑衅行为。这需要双方都承认国与国之间的竞争是一种正常而非反常的现象,正如商业竞争关系一样,不应排除竞争者之间在个体和普遍层面的共同利益。最为重要的是,双方都要意识到安全不是绝对而是相对的,即自身的安全不仅取决于本国所采取的防务措施,还要考虑这些行为是否会对对方造成不安全感。”
美国国关学界主流对冷战体制的偏好,也体现在与地区研究“大户”——苏联学的互动关系上。政治学中许多概念,如发展研究(developmental studies)、结构—功能主义(structural-functionalism)、政治发展论(political development)、技术理性论(technical rationality)、政治/经济发展趋同论(convergence)、政治文化理论(political culture)、多元主义理论(pluralism)、官僚政治模式(bureaucratic politics)等,都程度不同地引入苏联学的范畴。在这个过程中,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等人在20世纪60年代创立的极权主义理论(totalitarianism)反而被边缘化,苏联学因此部分地实现了去意识形态化,与美国主流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理论体系实现有限却“正常的”互动。而推动这一互动的学者包括美国政治学领军人物、战后西方比较政治学之父、斯坦福大学政治系教授阿尔蒙德(Gabriel Almond)。
进入21世纪,中国的经济总量以及与国际经济体系的融合度,已经远超苏联的鼎盛时期;与此同时,中国在意识形态方面不挑战西方,而是兼容并取西方多种理论、经验和政策中的合理成分,结合本国实际,摸索出一条适合中国自身发展的路径。但在美国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的理论层面,中国的“痕迹”少之又少,美国国关理论的主要范式从未对中美两大经济实体所构成的事实上的“两极”秩序进行任何理论化的尝试。相反,异军突起的进攻性现实主义(offensive realism),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建立在人类最原始的贪婪本能之上,基本排除了大国之间达成均势的可能,认为国际秩序也不可能实现和平转型。而最热门的新国际政治经济学(the new IPE),更热衷于纯理论的建构,对国际经济中的现实问题(包括中国崛起)不感兴趣。美国国关理论界对中国的“冷处理”,与苏联在冷战时期受到的“厚待”形成鲜明反差。反映在政策层面,美国一直拒不接受与中国的对等关系(新型大国关系),但总有人(如特朗普)为俄罗斯“回归”西方(如G7)而不懈努力。
近期,历来“重俄轻华”的美国国关理论界一反常态,罕见地关注中国,欲将中国崛起视为某种非正当性。一方面,现实主义在国际体系层面聚焦“权势转移”问题(power transition discourse),认定崛起的中国将无法避免地冲击“守成”大国(status-quo powers),必然挑战甚至颠覆现存国际秩序;另一方面,自由派学者则对西方主导的国际自由体制的弱化和破碎感到震怒,认为中国的崛起侵蚀了西方的自由秩序。美国学界对挑战西方秩序的苏联及其继承者俄罗斯网开一面,对致力融入同一秩序的中国却百般挑剔和排斥,斯金纳的文明/种族论应该可以解释美国对待这两者的巨大差异。
相对于冷战期间苏联学的“正常化”,美国的中国学(China studies)则是高度政治化的“是非之地”,尽管这一领域不乏重量级学者和众多流派。中国学的窘境可以追溯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彼时肆虐美国的麦卡锡主义以“谁丢失了中国”为由,将问罪矛头首先指向美国政府内部的中国问题专家,认定美国“失去”中国是这些美国内部的“通共”和“亲共”人士所为。一时间,美国政府内外与中国有关者人人自危,大批左派和自由派人士都受到程度不同的指责、怀疑和迫害。而研究中国和与中国有关的美国人似乎都有“通共”之嫌。
冷战结束以后,华盛顿圈内在对华问题上的“政治正确”即必须对华强硬,否则就会被贴上所谓“红队”(red team)或“熊猫派”(panda huggers)的标签。进入21世纪,有意从政或进入华盛顿圈子的美国的中国问题学者,仍然难以摆脱麦卡锡主义的阴霾,因此时而发表“沈大伟式”的“中国垮台/威胁论”,以此作为进入决策界的护身符。对此,笔者曾有感而发:“做美国人难(总是想要解救全世界),做美国的知华派更难,做知华派中有志从政者最难。”
相比之下,研究苏联的学者鲜有此种职业恐惧。像斯蒂芬·科恩(Stephen Cohen)这样著名的俄罗斯问题学者,即便在美俄关系最困难的时候,仍常在主流媒体强力发声,主张现实主义的对俄政策。他所主持的《国家》杂志(The Nation)更是美国公共空间反俄浪潮中的理性平台。
美国学界和决策界“重俄轻华”的取向,似乎还体现在美国政界和学界特有的“旋转门”现象上。冷战以来,美国高层安全和外交决策人士中(国务卿、国家安全助理等)不乏科班出身的苏联问题专家,如基辛格、布热津斯基、赖斯等。然而,不管中国自身是强还是弱、与美国是敌是友,如此“殊荣”却从未降临到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头上。同样是研究共产主义,为何研究欧洲/白人共产主义的美国学者可以担任要职,其职业前景要远远好于研究黄种人共产主义的学者?这种差异也许纯属偶然。笔者就此询问过一些美国学者,对方要么无言以对,要么模棱两可,也许根本无法想象、更难以接受研究东方共产主义的美国人比研究西方共产主义的美国人“低人一等”的推论。美国国内对华裔和中国人的特殊情结,居然会株连研究中国的美国人!
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副院长包道格(Douglas Paal)最近指出,造成中美目前困境的部分原因是主管美国对华事务的官员不了解中国,因此对中国失去耐心。此种论点值得商榷。当年尼克松和基辛格对一个封闭的中国知之甚少,但仍然开拓了中美关系。笔者认为,如今主管中国/亚太事务的美国中高层官员不是不了解中国,而是太了解中国。中美交往40载,知华派厌华反华,部分美国的“中国通”们走到这一地步,也许是他们的前辈——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鲍大可(A. Doak Barnett)等——始料不及的。
笔者在特朗普入主白宫以后曾断言,中美关系好也好不到哪去,但坏起来是没有底线的。如今特朗普政府对华全面脱钩,极限施压。横跨学界和决策界的斯金纳抛出文明/种族论,对已经处于低谷的中美双边关系无疑是雪上加霜。
五、结语
斯金纳2019年4月底的“文明”谈话来去匆匆,中美关系似又恢复了“竞争大于合作”的新常态。然而不争的事实是,中美关系的各个层面在特朗普任期内已遭受重创。特朗普执政两年半来,中美关系在和平时期下滑幅度之大、速度之快,下行空间之大、未来之不确定,在双边关系史上绝无仅有。至于有无所谓“两党共识”,或是目前美国国内的对华关系大辩论有何结果,其实都是无关紧要的了。而文明/种族问题的显现,反映了美国政治精英在对华战略层面,涌动着一股难以遏制、甚至是非理性的情绪和冲动,这种情绪和冲动也在特朗普眼花缭乱的对华动作中若隐若现,为中美关系的下滑起到加速器的负面作用。
百年前美国崛起之时,对外政策中文明/种族成分凸显,并伴随着以白人为主体的美国对外部世界的强烈征服欲;进入21世纪,种族问题在美国内外政策中沉渣泛起,对已成颓势的美利坚是强心剂还是精神鸦片,还要拭目以待。无论如何,那个持续了大半个世纪、充满自信、相对包容、有一定自我更新能力的美国,似已成过去时。这无论对美国本身,还是国际社会,都是一个挑战。
“斯金纳现象”对美国的对华政策会产生何种影响,是一个值得继续密切关注的问题。本文认为,种族问题在美国内政外交中是一个常量,只是在不同的时期以不同的程度和表现方式呈现出来;其消长沉浮既源于历史沉积和惯性,也有强烈的人工塑造的痕迹,在不同的社会环境、政治生态和学术环境中,会以不同方式和不同程度有意无意地表露,而且不会完全消亡,尤其是在美国国力沉浮的拐点(百年前和现今)。在美国高度意识形态化的话语体系中,华裔、中国和中国人也因此常常与“黄祸”(the Yellow Peril)、邪恶之类的标签相连,强烈地影响美国对华观念和政策的形成、制定和实施。
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政治的泛种族化愈演愈烈。几乎在所有问题上,左右、黑白、自由—保守势力之间,都竞相攻击对方为种族主义。尽管这一泛种族化趋向并非始于今日,特朗普及其对手都在最大限度地利用甚至强化种族问题,攫取更多政治资本,为2020年大选排兵布阵,其结果是造成美国政治进一步种族化、碎片化和极端化。在这个意义上,“斯金纳现象”也属自然表露,而非心血来潮。在认知和历史层面,西方观念中所谓的文明冲突,实际上是各类冲突的最高阶段和最后阶段,且无可化解。
对此,中国学界和决策界应给予足够关注。在具体应对中应避免两种极端倾向:要么完全无视种族因素在美国对华战略中的存在,要么以简单的情绪化方式加以抨击;而是应该把握大局,冷静应对,在目前中美关系的低谷期未雨绸缪,对未来中美关系进一步恶化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同时在双边和多边场合继续推进文明之间的对话、共存、共荣;秉承中华文明世俗、务实和包容的传统,以和而不同、多元共荣的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应对不文明、非文明和反文明、带有强烈种族色彩的“文明冲突论”;尽量减少、化解文明/种族因素在中美关系中的成分,为未来逐步改善双边关系创造条件。
作者:于滨,美国文博大学政治学教授、上海美国学会和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
来源:原文刊载于王缉思主编:《中国国际战略评论2019(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19年12月版;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
来源时间:2020/1/23 发布时间:2020/1/22
旧文章ID:205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