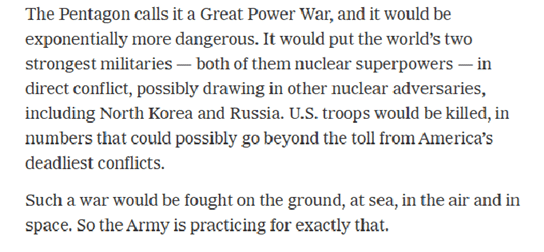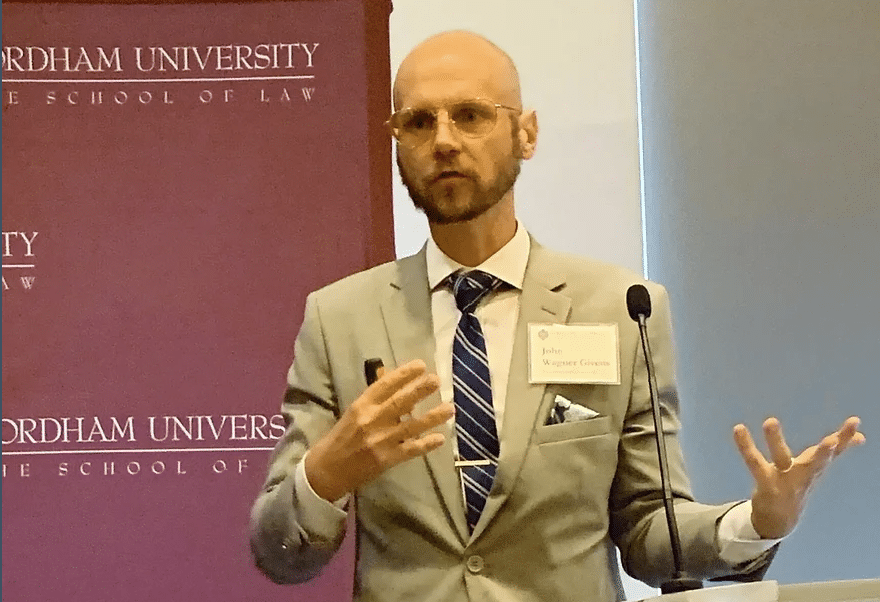刘元玲: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国内气候政策评析
作者:刘元玲 来源:《当代世界》2019年第12期
内容提要
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国内气候政策出现了大幅倒退。在联邦层面,特朗普坚持“美国优先”的执政理念,对气候变化的科学基础持质疑态度,在相关人事安排和政策落实方面呈现明显的“去气候化”特征。在地方层面,各州政府对气候变化问题的态度呈现两极分化的态势,难以形成合力。部分地方政府虽然希望做出积极应对,但心有余而力不足,成效有限,难以对全球气候治理产生积极影响。鉴于美国是全球第二大碳排放国,其失衡、低效的国内气候政策具有明显的外溢效应,不仅对美国自身,而且对其参与的双多边气候合作以及全球气候治理都产生了十分消极的影响。
关键词
特朗普;美国气候政策;全球气候治理
美国作为能源生产和消费大国、全球第二大碳排放国,在新能源发展、环保科技创新等与气候治理相关的领域优势明显,因此其国内气候政策走向和成效如何,将对全球气候治理产生重大影响。2017年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以来,一改其前任奥巴马政府的“亲气候”立场,使美国国内的气候政策出现大幅倒退。失衡、低效是目前美国国内气候政策的显著特征,这一消极的气候政策严重影响了全球气候治理的效能。
美国联邦与地方的气候政策新动向
美国国内气候政策是指美国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所采取的减排、减缓和适应等国内政策的总称,其可以划分为联邦和地方两个层面的政策举措。气候变化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及其与经济发展、能源使用、产业结构等部门的密切关联性,使得对该问题的有效应对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宏观层面的政策制定与落实。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国联邦气候政策出现了大幅度倒退,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在关于气候变化问题的观念认知方面,特朗普不认同气候变化的科学基础及其产生的影响,也不主张对该问题加以积极应对。他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观念认知体现了共和党在该问题上的传统消极立场。自1990年以来,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历次发布的气候变化评估报告均作为应对气候变化的权威文件被国际社会广泛认可,其核心结论是全球气候变暖正在发生,将对人类社会产生长期负面影响,但人类还有可能通过积极应对获得可持续发展的未来。这一评估成为各国政府制定气候政策、设立制度、落实行动的重要科学依据,也是全球气候治理的科学基础。然而,特朗普对IPCC的报告结论不以为然,质疑全球气候正在变暖,否定人为因素对气候变暖的影响,因而拒绝对此问题做出积极应对。他在2016年参加总统竞选时就声称:“奥巴马在解决一个实际上不存在的问题,他将气候变化看作当今世界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我认为其重要性很低,我不相信气候变化,除非有人给我证据看。”总统后,特朗普依然在不同场合声称气候变化是“骗局”,是“旨在削弱美国竞争力的谎言”。特朗普的这种认知与言论,不但遭到身边亲信的反对,而且受到民主党的谴责。此后,特朗普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保守认识虽有所松动,但其仍认为气候变化即便存在也并非不可逆转,是可“变来变去”的现象,无须积极应对。总体而言,特朗普落后的观念认知对美国国内气候政策造成了巨大负面影响。
第二,在人事安排方面,特朗普政府在应对气候变化相关职能部门任命的几乎都是反对或质疑气候变化的人。诸如“亲气候”的知名专家托德•斯特恩等遭到排挤。2017年2月,特朗普任命斯科特•普鲁特担任美国环保署署长,这位前俄克拉荷马州总检察长曾多次指责和质疑环保署的权力,还联合其他二十几个州状告奥巴马的“清洁电力计划”违宪。2018年7月,普鲁特离职后,特朗普授意前煤炭行业游说人士安德鲁•惠勒继任环保署署长,不但激起许多民主党人和环保人士的强烈反对,而且连缅因州的共和党参议员苏珊•柯林斯也表示反对,称惠勒致力于降低造成气候变化的排放标准,将把美国带往错误方向。特朗普内阁任职时间最长的官员之一、美国能源部长瑞克•佩里曾嘲笑气候变化是“世俗碳邪教”,并称气候科学家操纵数据以获得资金。白宫顾问、极力反对气候治理的科学家威廉•哈珀认为,气候研究浪费钱财,有损科学界形象,更像是某种“印度教”的东西。特朗普的这些人事任命在联邦层面为气候变化反对论者提供了舞台,与之相应,这些人在相关职能部门采取的举措又为特朗普实践反对气候治理的理念提供了支持。
第三,在气候政策方面,特朗普政府对奥巴马的气候遗产进行了“急刹车式”的暂停、搁置甚至废弃处理。奥巴马政府未能成功通过立法来保持联邦气候政策的稳定性和持久性,因而只能依靠行政命令的方式出台相关政策。奥巴马第二任期内推出的以“清洁电力计划”为核心的《总统气候行动计划》是其最重要的气候治理遗产。然而,2017年1月,特朗普上任伊始就宣称《总统气候行动计划》是“愚蠢且不必要的政策”,并用注重化石能源开发利用的“美国第一能源计划”取而代之。此后不久,特朗普大幅削减环保署的预算,并对其进行大规模裁员。2017年5月,美国政府公布2018财政年度预算草案——《美国优先:一份让美国伟大复兴的预算蓝图》,同年特朗普还签署了《推动能源独立和经济增长的总统行政命令》。“这说明特朗普或共和党的认识已直接转化成联邦政府的行动:一方面大幅削减与气候相关的科研预算,甚至包括执行多年、口碑甚好的‘能源之星’计划和先进能源研究计划,宣布退出《巴黎协定》并停止向绿色气候资金注资;另一方面要求直接撤销之前与气候变化相关的4项总统行政命令,立即对‘清洁电力计划’相关条款进行审查,解散由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与管理预算办公室召集的温室气体社会成本机构间工作组等。不到百日,当年‘奥巴马气候新政’就已经被彻底从联邦政府政策中删除。”这些举措在美国国内激起强烈不满,前美国环保署署长、民主党人吉娜•麦卡锡甚至将其称为“倒行逆施”。2018年8月,特朗普政府又宣布将在2020年后冻结奥巴马时代提出的旨在降低交通碳排放燃油减排标准,而交通领域的碳排放占美国总体碳排放的30%左右,这一举措使得奥巴马的气候遗产几乎被铲除殆尽。
综上所述,特朗普执政以来的联邦气候政策出现了大幅倒退。由于观念上的怀疑否定、人事安排和政策部署的“去气候化”,美国联邦政府的气候政策呈现明显的“走一步、退三步”的状况。在联邦政府政策影响下,美国地方气候政策也呈现了明显的倒退,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地方政府数量有所减少。美国国家制度的设计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切政治都是地方政治”,联邦的意志能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得以落实,地方政府的作用非常关键。美国50个州和1个特区政府及其下辖的数万个城市、郡县政府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的政策立场差异很大,甚至呈现两极分化的状态,既有像加利福尼亚、纽约这样积极行动的州,也有像俄克拉荷马、德克萨斯这样消极应对的州。在“去气候化”成为联邦政府气候政策基调的情况下,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地方政府数量明显减少。2013年,美国有29个州拥有可再生能源组合标准,到2019年时减少为25个州加华盛顿特区。2014年,美国共有38个州编制了温室气体排放清单,制定了气候适应计划,但到2019年11月减少为23个州加华盛顿特区。行动积极的地方政府在特朗普执政以来也遭到来自联邦层面自上而下的打压与制约。2019年9月,特朗普宣布撤销加利福尼亚州独立制定更加严格的汽车尾气排放标准的权力,并禁止其他州制定此类规则,这进一步挫伤了其他地方政府应对气候变化的积极性。
第二,地方政府应对气候变化的成效有限,达不到美国国家减排目标所需要的规模。早在2016年5月,美国密歇根大学和北卡罗来纳大学的研究人员在对美国44个地方性气候政策进行评估后指出,美国地方性气候政策虽然数量众多,但缺乏实操性,因而减排效果有限。国际社会曾一度对美国地方气候政策与行动抱有希望,期望它们能以某种方式如期兑现美国在《巴黎协定》中的承诺。但在倒退的联邦气候政策的影响与压力下,不断有地方政府退出应对气候变化的项目,使得这一希望成为泡影。2018年,美国甚至出现了碳排放量增加的情况,增幅为3.4%。此外,由于缺少联邦政府的支持,地方政府推行的气候政策只能聚焦于政府行为或社区建设等方面,将减排、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推广至不同领域的尝试收效甚微。
总之,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立场出现了反转,联邦层面的气候政策甚至出现了根本性逆转。面对倒退的联邦气候政策,国际社会一度将希望寄托于美国地方层面的气候政策。然而,部分地方政府的努力虽然取得一定成效,但总体而言是心余力绌。2018年,美国碳排放不降反升也说明地方气候政策根本无法对冲联邦气候政策倒退带来的消极影响。
美国国内气候政策倒退的原因
2017年以来,美国国内气候政策出现大幅倒退是由很多因素共同作用造成的。在联邦层面,愈演愈烈的政治极化导致共和、民主两党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出现认知分裂、难以达成共识,这是美国气候政策出现倒退的根源。在地方层面,一方面受消极倒退的联邦气候政策影响,另一方面受制于千差万别的地方实际情况,诸多州关于气候治理的认知日趋消极,政策效能不断下降。特朗普本人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消极认知立场也是导致美国气候政策倒退的重要因素。
第一,政治极化导致共和党与民主党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对立日益加剧,这是造成美国气候政策倒退的根源。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共和、民主两党在环境保护、气候变化等问题上的分歧就日趋明显,立场日渐对立。共和党对待气候变化的主流立场是质疑并否定气候变化、拒绝改变美式生活方式、反对以减排来应对气候变化,并且这一立场随着时间的推移愈演愈烈;而民主党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持积极立场,在观念和政策层面都主张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并以此来吸引更多选民支持。两党之间的理念和立场分歧通过各种方式渗透给选民,而选民在此问题上的认识差距又进一步加剧和固化了两党之间的分歧。政治极化导致的认知分裂造成立法、行政和司法部门相互掣肘,从而带来联邦层面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失衡与低效。无论哪个党派执政掌权,这一态势在过去三十多年都没有发生实质改变。特朗普执政进一步加剧了两党的政治对立,进而对制定高效、平衡的气候政策产生负面影响。
第二,受联邦气候政策倒退的影响以及各地自身禀赋的制约,美国地方政府的气候政策也出现了倒退。一方面,美国地方政府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立场也呈现分歧对立状态,这是两党在联邦层面的斗争向下传导的结果。民主党占优势的蓝州多数代表的是金融界、中产阶级、高级知识分子的利益,其对气候议题较为积极;而共和党占优势的红州则多是能源重工业、制造业等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因此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更为保守。另一方面,各个地方资源禀赋不同,具体情况千差万别,他们往往各自为政。例如,各州间的减排目标差异大、措施考虑不够周全、许多目标的达成遵循自愿原则,使得基于地方实际而产生的气候政策很难统一,从而不能形成合力共同应对气候变化。2019年,美国能源署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无论是绝对排放量还是人均排放量,美国各州与能源有关的二氧化碳排放差异很大。”各州的土地规模、可用燃料、企业类型、气候、人口规模和密度都对该州的总排放量和人均排放量水平发挥着直接影响。例如,华盛顿州拥有丰富的水力资源,完成减排任务相对容易;特拉华州拥有丰富的煤炭资源,因此推动低碳减排的工作就阻力较大。此外,地方政府相关立法所具有的权威性不足,难以像联邦立法一样改变社会各界对机会、成本和风险的认识,进而刺激他们做出有利于气候治理的选择。有些地方政府的财政预算中没有明确的应对气候变化的资金,而特朗普执政后联邦政府分配的资源少之又少。即便是资金充裕、政策积极、行动力最强的地方(如加利福尼亚州),其减排行动也仅仅局限在有限的范围内,无法对冲那些消极应对的高碳排放州的影响(如得克萨斯州),也无力抵消倒退的联邦气候政策所带来的影响,甚至还要耗费精力应对联邦政府的打压。
第三,特朗普本人是导致美国气候政策出现倒退的直接影响因素。一方面,特朗普质疑、否定气候变化的科学基础,并通过自己强大的自媒体宣传能力掀起了一股质疑、否定气候变化科学基础的浪潮,影响了数量广泛的国内外民众,削弱了美国应对气候变化的认知基础。另一方面,特朗普奉行“美国优先”的执政理念,以“美国能源独立”为目标,注重对化石能源的开发使用和出口,降低环保监测标准。特朗普回归传统能源,旨在通过促进任内经济增长获取短期经济收益,巩固执政基础,这不可避免地造成联邦气候政策的倒退。此外,特朗普执政后对奥巴马时期积极的联邦气候政策进行暂停、搁置甚至废弃,在机构设置、人事安排以及财政分配等方面都呈现明显的“去气候化”的倾向,对地方政府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举措不仅不予以支持,反而实行压制和约束,使得地方政府气候政策出现倒退。
总体上看,当前美国国内气候政策倒退的主要原因是愈演愈烈的政治极化,以及由此导致的两党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认知分裂,这不但影响了联邦政府气候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也向下渗透并影响到地方层面的气候政策。虽然美国仍有部分地方政府主张积极应对气候变化,但由于缺乏联邦政府层面的顶层设计,它们基于自身现实所采取的气候政策基本上是各自为政,难以形成合力,成效有效。
美国国内气候政策倒退的影响
美国曾经是全球气候治理最重要的参与者之一。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国内气候政策出现倒退不仅对其本土气候治理,而且对其参与的双多边气候合作和全球气候治理进程与效果都产生了显著的消极影响。
一是对美国生态环境与经济可持续发展带来消极影响。短期来看,由于缺乏积极有效的应对,气候变化已经对美国农业发展、土地利用、水资源保护和民众健康等带来损害。例如,干旱、暴雨等极端天气的增加对美国作物产量、家畜安全和乡村生活带来越来越严峻的挑战。气温和降水变化导致山火增多、地表臭氧污染加重、空气质量恶化,进而使民众健康风险增加。长期来看,消极的气候政策对美国国家利益造成的负面影响是显著的。根据美国环保署最新的研究报告,如果不对气候变化加以遏制,其造成的种种后果将在21世纪末给美国造成数千亿美元的损失,包括供水短缺、基础设施瘫痪以及由空气污染导致的平均寿命缩短等。英国剑桥大学的研究报告指出,除非《巴黎协定》的目标能够实现,否则到2100年全球平均气温将上升4摄氏度……这将会使美国的人均GDP损失超过10%。
二是致使美国曾经参与的双边气候合作陷入停滞。特朗普执政后,美国与欧盟、印度、中国等主要经济体的双边气候合作均陷入停滞。例如,奥巴马执政期间曾试图推动美国与印度之间的双边气候合作,如今该议题已经彻底退出了特朗普的议事日程和关切范围。目前,特朗普政府已将重点放在推动美国向印度出口化石能源的议题上。奥巴马执政期间,美国与欧盟在“如何共同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分歧与合作并存,到了特朗普时代,美欧双方在该问题上的合作几乎无从谈起。中美气候合作经过从无到有、从边缘到中心、从次要到主要的转变过程后,在奥巴马执政时期一度成为中美双边合作的亮点,成为大国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典范。然而,特朗普政府对待气候问题的态度及其倒退的国内政策,使得中美双方应对气候变化的合作陷入停滞。特朗普政府发动针对中国的“贸易战”,导致两国关系遭遇严重冲击,使得双边政府间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氛围几乎荡然无存。
三是导致多边气候治理平台的未来发展更加举步维艰。特朗普执政以来,将其落后的气候观和倒退的气候立场带到多边气候治理平台,阻碍了通过多边机制应对气候变化所具有的可信度和效能。例如,美国曾积极推动“亚太清洁发展和气候伙伴计划”,通过多边合作满足各国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并应对温室气体排放、能源安全等方面的挑战,同时依托全球环境基金推动各国开展形式多样的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然而,特朗普执政后将这些多边项目束之高阁,相关国际合作陷入停滞。事实上,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已不再主动在多边治理舞台增加气候议题,甚至中断在多边机制中对气候议题的讨论。例如,2019年白宫代理幕僚长米克•马尔瓦尼公开声称,2020年在美国举办的七国集团峰会将不设置气候变化相关议题。尽管仍有一些多边机制抛开美国达成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声明,但总体而言,缺乏美国的参与和支持,这些努力的成效将大打折扣。此外,特朗普决定退出《巴黎协定》,也会对全球气候治理造成严重负面影响。正如曾推动达成《巴黎协定》的美国国务院前气候官员安德鲁•莱特所言:“如果我们只是一个低排放的小国,影响不会那么大。但我们是一个有着很多权力和影响力的大国,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缺席会使整个世界的气候治理倒退。”
结语
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国内气候政策出现大幅度倒退,总体呈现失衡、低效的特征。从联邦层面看,愈演愈烈的政治极化使民主党与共和党在气候变化问题上陷入认知分裂,双方难以达成共识。日益严重的政治极化导致美国政府难以出台平衡、高效的联邦气候政策。从地方层面看,由于受党派政治极化的影响和联邦气候政策倒退的压力,以及地方气候政策本身的诸多局限,其治理效果十分有限,无法对冲倒退的联邦气候政策所带来的冲击。美国国内气候政策倒退不仅对其自身经济社会发展造成消极影响,而且使美国参与的双多边气候国际合作陷入停滞,对全球气候治理造成严重冲击。
来源时间:2020/1/13 发布时间:2020/1/7
旧文章ID:204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