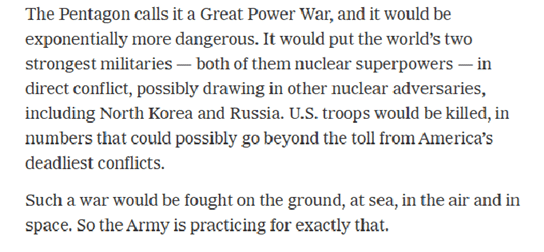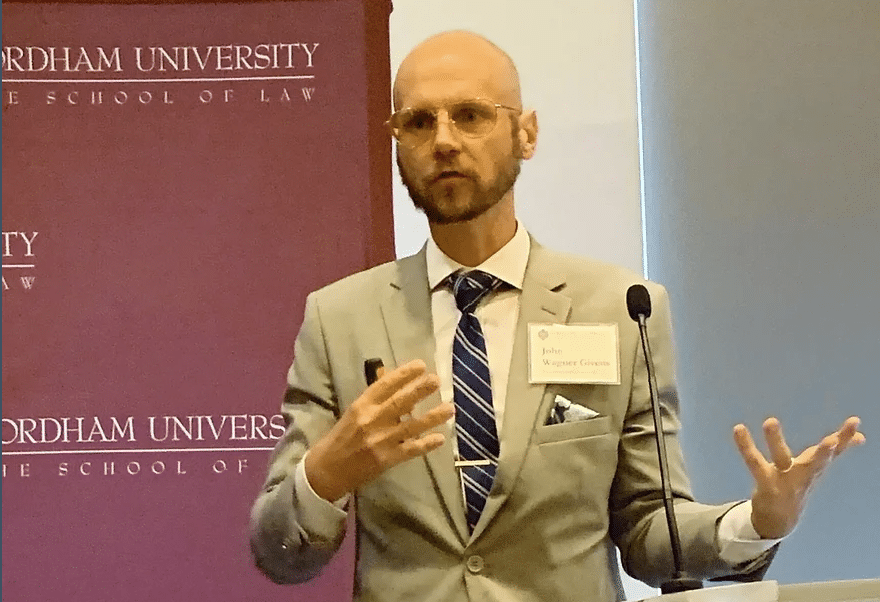美国经济不如想象的那般竞争和自由
作者:马丁•沃尔夫 来源:FT中文网
一切始于一个简单的问题:“美国的手机资费究竟为什么这么贵?”为了找到答案,托马斯•菲利蓬(Thomas Philippon)围绕当今美国企业实际上如何运转展开详细的实证分析,最终推翻了几乎所有人不假思索接受的有关世界最大经济体的很多认识。
菲利蓬在他的极具说服力的重要着作中写道,过去20年,竞争和竞争政策僵化,导致了严重的后果。美国已不再是自由市场经济的故乡,竞争不比欧洲更激烈,监管机构并不更加积极主动,新一批超级明星企业与前几代企业没有根本区别。
身为纽约大学(New York University)教授的菲利蓬是目前在美国任教的杰出法国裔经济学家之一。其他人还有最近的诺贝尔奖得主、麻省理工学院(MIT)教授埃斯特•迪弗洛(Esther Duflo)、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前首席经济学家奥利维尔•布兰查德(Olivier Blanchard)以及目前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Berkeley)任教的伊曼纽尔•赛斯(Emmanuel Saez)和加布里埃尔•祖克曼(Gabriel Zucman)。
然而,除了国籍以及不把有关自由市场的陈词滥调视为理所当然的倾向之外,很难看出这些人有太多的共同点。对菲利蓬有争议的命题持怀疑态度的人可能会声称,一名法国经济学家必然从意识形态上反对美国式资本主义。但菲利蓬坚称,他坚信竞争的价值。的确,《大逆转》(Great Reversal)有一章专门论证这个问题。此外,他论证的每一步都基于对数据的细致分析。
他干脆利落地总结了研究结果:“首先,美国市场的竞争性已减弱:很多行业的集中度高,领军企业地位固化,它们的利润率过高。其次,这种缺乏竞争损害了美国消费者和员工利益:它已导致价格上涨、投资减少和生产率增速下滑。第三,与普遍观点相反,主要的解释是政治上的,而不是技术上的:根据我的研究,竞争的减少是因为进入壁垒增加以及反垄断执法不力,而大量的游说和竞选捐款支撑着现状。”
所有这些都得到了有说服力的证据的支持。例如,美国的宽带上网价格大约是可比国家的两倍。在美国,航空公司的每位乘客利润也远高于欧盟。
更广泛地说,这项分析表明,“市场份额变得更集中,持续时间更长,而利润增加。”此外,在各个行业,市场集中度上升带来了更高利润。总的来说,影响是巨大的: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税后利润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几乎翻了一番。
市场集中度上升的原因有很多。在制造业,来自中国的竞争起到了一定作用,它把实力较弱的美国国内竞争对手挤出市场。对于其他经济领域,我们需要其他解释。上世纪90年代,包括零售业巨头沃尔玛(Walmart)在内的超级明星企业,推动着投资率和生产率上升。然而在2000年代发生了相反的情况:市场集中度不断上升,推升了地位固化的企业的利润,而投资率和生产率增速双双下降。
这种集中度上升的恶性形式,反映出新进企业数量显着减少,而对合并交易的容忍度上升。换句话说,美国经济正目睹竞争显着减少,垄断和寡头垄断相应增加。
为了进行论证,该书将美国与欧盟进行比较。许多读者可能会笑:毕竟,欧盟难道不是一场经济灾难吗?然而,在比较实际人均GDP的变化时,答案是:并非如此。
从1999年到2017年,美国实际人均GDP增长了21%,欧盟增长了25%,就连欧元区也增长了19%,尽管其对金融危机处置不当,造成了损害。在欧盟,不平等程度和收入分配趋势也不那么负面,因此收入增长得到更平均的分享。
简言之,将欧盟与美国进行比较是无可非议的。这些比较显示,无论是在利润率还是市场集中度方面,欧盟都没有出现美国那样的急剧上升。在美国,自2000年以来,工资和薪金占企业总收入(即所谓的“增加值”)的比例下降了近6个百分点,但在欧元区一点儿也没有下降。这推翻了一种假设,即技术是劳动力收入占比下降的主要驱动力。毕竟,技术(还有国际贸易)对大西洋两岸的影响大致相当。
请注意,菲利蓬对产品市场竞争的差异提出了一个狭义的主张。他强调,欧盟经济并非在所有方面都更强大。相反,“美国拥有更优秀的大学和一个更强大的创新生态系统——从风险资本到技术专长。”
然而,在过去20至30年间,欧盟的产品市场竞争已经变得有效得多。这反映了单一市场内部有针对性的去监管化——这在英国退欧悲剧的背景下颇具讽刺意味,因为放松监管是由英国驱动的、发端于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的政策创新——以及更为激进和独立的竞争政策。大西洋两岸已将注意力转向保护和促进竞争的必要性。
一个有趣的观点是,相比个别成员国或美国,欧盟建立了更为独立的监管机构。这是欧盟内部相互不信任的健康结果。在监管方面,欧盟成员国痛恨自己受其他成员国突发奇想的影响,因此更喜欢完全独立的机构。这对国内监管机构薄弱的国家尤其有益。监管机构的独立性也使得游说在欧盟的回报相对较低。
这方面的证据很明显。一个欧盟成员国的产品市场监管程度在1998年时越高,此类监管随后下调的幅度就越大。同时,对欧盟成员国的影响也比非欧盟成员国大得多。
这些变化反映了政治上的差异。在美国,反对放松监管和支持有利监管的游说要激烈得多。总的来说,有强有力的证据证明,不可避免地被大公司主导的这类游说可以奏效。不然为什么人们愿意为游说买单?
有关金钱在美国政治中扮演的作用的数据甚至更为戏剧化。国会议员每周要花大约30个小时筹集资金。美国最高法院2010年对“联合公民”(Citizens United)一案做出奇葩判决,裁定公司等同于个人,金钱等同于言论(判决认定通过资助来播放批评其他候选人的竞选广告是合法的——译者注)。这已被证明是美国朝着一个富豪统治国家演变过程中迈出的一大步。
就像近来以诚实得让人捉摸不透而闻名的前众议员米克•马尔瓦尼(Mick Mulvaney,现任白宫代理幕僚长,在为总统辩护时经常说出令人发笑的老实话——译者注)在2018年4月所说的那样:“如果你是一名从来不给我们钱的说客,那我没和你说过话。如果你是一名给过我们钱的说客,那我可能会和你谈谈。”你的确可以接触到用钱可以买到的最有实权的国会议员。
在美国,公司游说活动的规模是欧盟的两到三倍。美国的竞选捐款是欧盟的50倍。
《大逆转》还考察了三个关键行业的情况:金融、医疗保健和“科技巨头”。
在金融方面,一个令人吃惊的发现是,中介成本(银行家和经纪人吸收储蓄、然后将其输送给最终用户所收取的费用)一个世纪以来一直保持在两个百分点左右。那么多计算机竟然未能改变这一局面。所以金融是一台抽租机器。这真的必须改变。
关于美国,有两件事是大多数局外人永远都不会理解的:其枪支法律和医疗体系。美国在医疗保健上的支出(略低于GDP的五分之一)远高于其他高收入国家,但结果要差得多。这是怎么回事?
答案是,美国的医疗制度产生了从上到下的抽租垄断:医生、医院、保险公司和制药企业都从这个油水丰厚的系统中分一杯羹。
最后,菲利蓬分析了他所称的“GAFAM”(谷歌(Google)、亚马逊(Amazon)、Facebook、苹果(Apple)和微软(Microsoft))。他展示了这些科技巨头在经济中的分量并不比过去的巨头更大。但是它们在整体上与经济的联系要小得多。因此,它们对生产率增长的影响相对较小也就不足为奇了。
作者有说服力地挑战了这样一个观点,即这些企业的垄断地位是规模经济和网络效应的自然产物。因此有些事是可以并且应该做的。按照激进程度的升序,这些措施有:防止占主导地位的公司进行收购,或者强迫它们剥离资产;通过强制要求与其他网络的互操作性和数据可转移性,来限制其滥用主导地位的能力;以及将它们分拆。
《大逆转》还指出,通过限制性合同、职业许可和准入限制,劳动力市场的买方垄断正在上升。放松管制需要关注这些障碍。
正如自亚当?斯密(Adam Smith)以来的经济学家所知道的那样,企业自身将以极大的热情追求对竞争的限制。结果就是收租资本主义,它既效率低下又在政治上不具有正当性。然而困难在于,现有企业购买它想要的政治和监管保护可能太容易了。
美国应该要什么?菲利蓬提议的答案是:自由准入;监管机构在采取反垄断行动时准备好犯错误;以及保护消费者应该享有的透明度、隐私权和数据所有权。美国采取行动的一大障碍是金钱在政治中的普遍作用。结果是寡头垄断和寡头统治的双重弊端。
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在很多方面都是《大逆转》中描述的有缺陷的资本主义的产物。相反,美国需要的是另一位泰迪•罗斯福(Teddy Roosevelt)及其有力的反托拉斯行动。人们还可以想象这一幕吗?所有信奉竞争资本主义优点的人都应该希望如此。
来源时间:2019/11/20 发布时间:2019/11/20
旧文章ID:20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