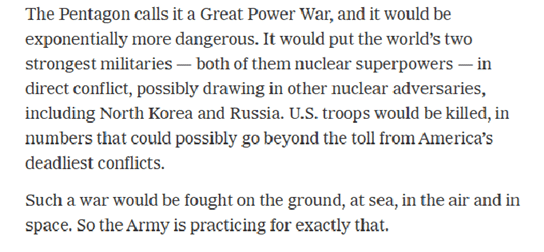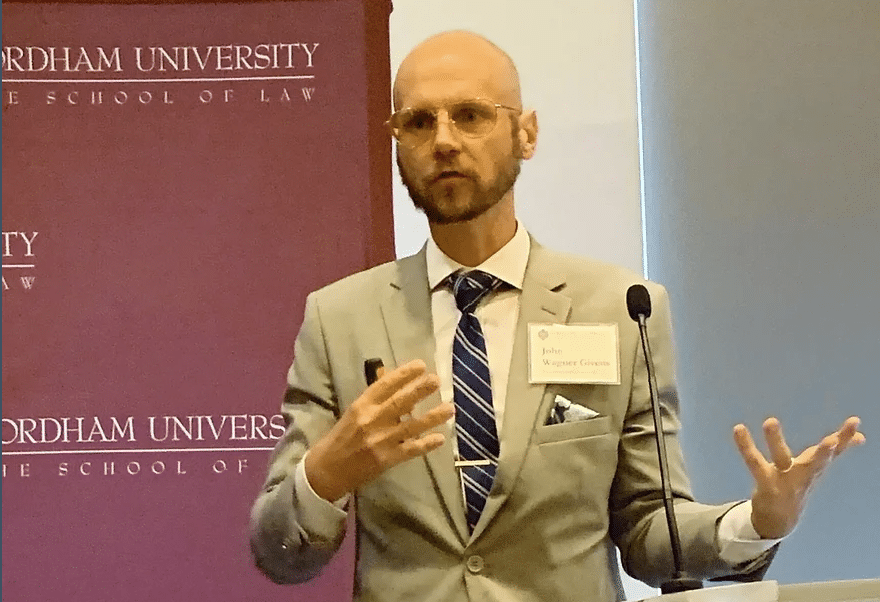特朗普也难以改变的美国外交大战略
作者:归宿 来源:政见CNPolitics©
二战结束以来,美国有一个主线为“追求在国际舞台上领导地位”的外交大战略。它由四个相互联系的部分组成:保持军事优势、构建和维持盟友体系、将其他国家纳入由美国主导的国际制度和市场、防止核武器扩散。七十多年来,无论世事如何变迁,谁是美国总统,这一大战略一直保持稳定,延续至今。
美国为何能维持外交大战略?一些学者认为,主要原因在于美国的实力以及它在国际上的单极地位,还有一些学者认为这是美国的价值观使然。伯明翰大学国际关系教授Patrick Porter则指出,美国外交大战略得以保持稳定的关键在于美国的经济军事实力和外交政策习惯。另外,美国政府部门、智库研究机构及企业等“圈内人”组成的外交政策精英集团,在影响和推动外交政策习惯形成的同时,也起到防范外交政策发生重大转折性变化的作用。
什么是外交政策习惯?
外交政策习惯是一种路径依赖:政策决策者通过某种固定的逻辑和方式分析、处理问题。“习惯”在决策思路上不同于严格考察成本收益比的因果推论、刻意追求某种规则和范式的意识形态,在决策过程中也有别于传统官僚中政府部门决策的讨价还价、组织和个人利益的驱动。它更多是一种集体性的惯性、先入为主的观念。
外交政策习惯有利有弊。它有利的一面在于,习惯的力量可以形成制度规范,使得外交政策议程制定、政策工具设计更为聚焦,并且防止政策精力被“圈外人”天马行空的幻想分散。但另一方面,政策习惯也是一种自我限制。面对国际形势发展的剧烈变化,习惯有时候无法应对实际情况,并且可能会导致监督缺失,产生政策失误。
美国的外交政策习惯从何而来?
研究者认为,美国“领导世界”的习惯根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称霸全球的相对实力和国际地位。二战在摧毁多数欧洲老牌强国的同时,也刺激了美国的工业扩张、加强了国家能力。二战后,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一度垄断核武器、远程轰炸机等战略武器,美元也成为国际储备货币。这些因素确立了美国政策精英重塑国际安全秩序的信心。
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全球乱局,也改变了美国传统的孤立主义思维,让当时的美国外交政策精英迫切要求将美国的实力和技术优势转化为美国设计制度下的全球霸权。这一大战略也通过建立北约和马歇尔计划等得以实现。虽然在60年代和70年代,大战略由于越南战争、美国国内的民权经济危机等内外因素暂时受挫,它在里根上台后又强势回归,并延续至今。研究者指出,此外交政策习惯对政策精英圈子有“极大的吸引力”、“远胜过于任何公众意见”。
研究者也说明,外交政策精英们对于大战略中的一些具体问题可能存在不同意见,比如人权问题、是否参与多边机制、是否对某个特定事件实行干涉介入。但总体而言,政策精英们希望美国依然能掌控全球秩序的主导权,害怕美国从国际舞台上撤退,反对美国放弃对盟友的义务。他们认为这些会导致国际政治重回阵营对抗、经济停滞的状态,并可能引发更大的灾难。在政策精英们看来,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是唯一的大战略,在这个大前提下才可以有具体的政策辩论。
外交大战略有没有可能被改变?
研究者指出,美国的外交大战略是否会改变,取决于外部环境变化程度是否足以改变现状,以及决策者是否愿意克服国内的重重阻力来做出改变。改变美国外交大战略的典型案例就是尼克松的外交政策。
在美国面临诸多内外挑战的情况下,尼克松下决心减弱美国在其它地区的影响,接受“多极世界”的现实。尼克松与中国建立直接联系,并与苏联缓和关系,将苏联看作后霸权世界一个将长期存在的对手和伙伴。但要做出这一改变,尼克松就得在国际舞台和国内政界都经营权力政治。尼克松通过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搞秘密外交,并越过国务院、国会中的传统外交政策精英,将外交安全事务决策集中在一个小圈子里。尼克松下台后,这一做法也就随之终止。
特朗普会不会改变美国外交大战略?
特朗普作为政治“圈外人”闯进白宫,其秉持的“美国优先”理念,对二战后的美国外交大战略构成了严峻挑战。对于大战略,特朗普也想改之后快。但事实上,特朗普执政以来,他对于美国外交大战略的继承的一面要超过改变的一面。这既体现于特朗普在对中、俄的强硬姿态,也表现在当特朗普轻举妄动时,外交政策精英们的抵制和反对。后者在叙利亚撤军事件中就可见一斑。
美国的外交大战略及其稳定性也有助于解释和预测中美关系。美国由于追求国际领导地位,自然就将快速崛起的中国视为主要对手,并全力加以遏制。从这个角度看,中美竞争乃至对抗或已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精英们的某种共识,这也将是未来两国关系发展的重要背景。
参考文献:
Patrick Porter, Why America’s Grand Strategy Has Not Changed:Power, Habit, and the U.S. Foreign Policy Establishment (2018).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42, No. 4 (Spring 2018), pp. 9–46, doi:10.1162/ISEC_a_00311
来源时间:2019/1/18 发布时间:2019/1/17
旧文章ID:177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