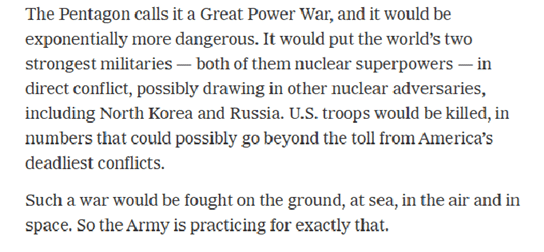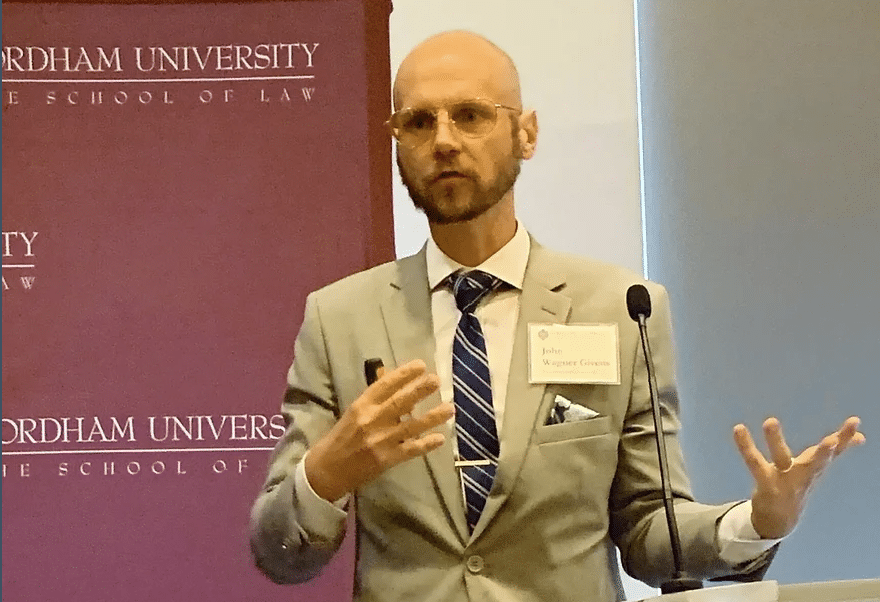美国对外援助的战略功能——以特朗普政府援外政策争论为背景
作者:丁韶彬 来源:《当代世界》2018年第11期
内容提要:二战结束以来,美国政府大部分时期视对外援助为国家利益之有效和必要工具,国会参众两院和共和、民主两党也对此形成基本共识。特朗普政府出于“美国优先”理念和对军事实力的信奉,试图在减少赤字的同时增加国防投入,多次提出削减援外等领域预算的方案,但在美国各界的多数反对和批评下,没有获得国会的支持。美国社会对于对外援助政策功能的普遍认同,对理解对外援助的本质,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即维护必要的政治联盟、促进投资和贸易等经济利益,塑造负责任大国形象,与外交和其他途径相配合增加广泛的国家利益,都使适度规模的对外援助成为必要。
关键词:对外援助;国家利益;特朗普政府
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原先的竞选口号“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和“使美国再次强大”(Making America Great Again)成为其执政理念。在这些理念指引下,特朗普政府宣布退出气候变化《巴黎协定》后又宣布有条件重返,宣布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后又下令研究重返,指责并要求盟国分担义务和费用,对中国发起规模空前的“贸易战”,断然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不承认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等等,都成为备受国际社会关注的议题。
2017年3月16日,美国总统行政办公室发布了《美国优先:使美国再次强大的预算大纲》(以下简称“预算大纲”)。此后,美国政府又先后于2017年5月和2018年2月向国会提交了2018财年和2019财年的联邦预算。以上三份文件都对对外援助等外事预算进行了大幅削减,由此引发美国社会的持续争论和关注。相较于前述其他议题,削减援助预算所引发的政策争论,并没有引起多少国际关注。然而,分析这一争论的内容,有助于理解对外援助的一般功能及其在美国对外关系中的地位。在中国不断增加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援助和经济投入的背景下,美国关于对外援助问题的争论,对理解当前中国的对外援助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美国对外援助实践的历史演进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外援助成为美国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工具。自杜鲁门政府实施在当代国际关系中具有重要历史影响的“马歇尔计划”和“第四点计划”以来,美国历届政府都创设了大量影响深远的对外援助账户和项目。例如,艾森豪威尔时期的“粮食和平”(Food for Peace)项目;肯尼迪时期的和平队(The Peace Corps)项目——这一时期美国国会制定了《对外援助法》,成立了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尼克松时期的泛美基金(IAF)项目;卡特时期的美国非洲开发基金会(USADF);冷战结束后老布什政府的“支持东欧民主”(SEED) 账户,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9·11”事件之后小布什政府的千年挑战账户(MCA)和抗击全球艾滋病倡议(GHAI);奥巴马政府的三个总统政策倡议:全球饥荒和粮食安全倡议——哺育未来(FtF)、全球健康倡议(GHI)以及全球气候变化倡议(GCCI),等等。所有这些举措在美国对外援助史上都非常引人注目。
美国对外援助的一个重要和突出的总体特征是,尽管不同时期的政府或国会对于对外援助的重视程度有所差异,但自杜鲁门以来的多数美国政府都把对外援助视为直接或间接服务于国家安全的对外战略工具。早在1950年,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68号文件(NSC-68)就强调“马歇尔计划”和“第四点计划”等对外援助项目的战略意义,并提出进一步增加对外援助支出的政策建议。其后,里根政府在1987年美国历史上第一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把对第三世界援助政策、防务政策与国际经济政策概括为遏制战略的三要素。1988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也强调,对外援助“促进了重要的国家利益,帮助在全世界传播美国的价值观和原则”,“美国的援助项目代表了高杠杆的投资,以相对较小的支出取得很大的回报”。老布什政府在1990年和1991年连续两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也强调对外援助的重要性,并在后一份报告中提出对外援助是美国对外政策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工具。小布什政府2001年9月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则第一次把发展(即援助)与防务和外交并列为国家安全三大支柱,即所谓3D战略。而奥巴马政府除了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强调发展的重要性,还制定了美国历史上唯一一份《四年外交与发展评估》(QDDR)报告,该报告题为“通过民事力量领导”(Leading Through Civilian Power),强调外交和发展等民事因素与防务的同等重要性。此外,奥巴马还签署了美国第一份国际发展政策文件——《全球发展总统政策指令》(PPD),提出要把发展提升为“美国权力的一个核心支柱”,使发展、外交和防务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共同促进美国国家安全。
当然,美国国内也有过多次对于对外援助政策的批评和争议。这些批评和争议甚至导致援助预算的削减,比较典型的是从冷战结束前的1986年到2001年“9·11”事件爆发前的十几年间。里根在1988年1月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就抱怨:“虽然联邦预算总体上有所增长,但1986财政年度的对外援助减少了29%,1987财政年度又减少了11%,1988财政年度又面临削减。现在,安全援助账户已经大大低于维持国家安全利益所必需的水平。”克林顿政府时期,由于冷战的结束,美国孤立主义力量抬头。国会轻视多边机构,迟迟不批准拖欠的联合国会费,对美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中所承担的经费份额也非常不满。国会中的主导观点认为,对外援助作为国家安全战略工具的意义已经减弱,这导致包括对外援助在内的政府对外事务拨款连年下降,1996—1997财年甚至达到历史的最低值。由于对外援助的减少,美国第一经济援助大国的地位竟在1989年和1993—2000年间被日本取代。但其后,美国对外援助支出在小布什时期迅速恢复,并实现了倍增,达到年均500亿美元左右的水平。奥巴马政府时期也维持了这一支出水平。
根据美国国际开发署公布的最新数据,二战结束以来,1946—2016财政年度,美国提供对外援助总计11743.2万亿美元,其中经济援助7933.4亿美元,占67.6%;军事援助3809.8亿美元,占32.4%。2016财年,美国共有19个联邦机构通过74个账户提供了494.7亿美元的对外经济和军事援助;全部19个机构通过67个账户提供了近340.2亿美元的经济援助,其中国务院和国防部还通过7个军事援助账户提供了超过154.5亿美元的军事援助。
特朗普政府的援外预算削减计划
2017年3月16日,特朗普政府发布《美国优先:使美国再次强大的预算大纲》。在致国会的信中,特朗普强调,政府将“重新把促进美国人民的安全置于优先位置”,预算大纲的核心是“在不增加联邦赤字的情况下重建美国的军事力量”。为此,国防支出将大幅增加540亿美元,同时大幅增加司法部和国土安全部移民执法预算以及应对暴力犯罪等涉及国民、社会和国家安全的相关经费支持。
显然,在不增加赤字的情况下增加安全预算,必然导致其他方面预算的减少,其中国务院、国际开发署和财政部国际项目是削减最多的领域。在预算大纲中,特朗普提出了许多实际上减少美国国际责任的预算计划,如减少对联合国及其附属机构的支持,包括减少对联合国维和行动和其他国际组织的援助;终结气候变化倡议项目的援助;把一些军援从无偿援助改为贷款,允许受援国用美国援款购买美国武器;减少对包括世行在内的多边发展银行的资助。同时,以提高援助资金效益为由,特朗普提出终止或减少一些重复资助的项目,如终止紧急难民和移民援助账户;终止重叠的维和和安全能力建设及重复的应急项目,如综合危机基金(Complex Crises Fund);对通过其他渠道也能够获取资金的组织和项目,如东西方中心(East-West Center),也将停止支持。此外,大纲突出了美国的战略利益,把经济和发展援助重新聚焦于对美国最具有战略重要性的国家。
基于预算大纲的理念和思路,2017年5月23日,特朗普政府向国会正式提交了其首份联邦预算——2018财年预算请求,其中要求为“国务院、对外事务及相关项目”(SFOPS)提供财政支持420.5亿美元,含对外援助270.5亿美元,比奥巴马时期的2017财年授权拨款分别减少了30%和35%。不过,在众参两院于2018年3月先后通过并经特朗普签署生效的《2018财年综合拨款法案》中,国会实际批准了541.8亿美元的对外事务经费,其中对外援助399.2亿美元,比2017财年实际分别减少6.1%和4.2%。此外,从最终的2018财年拨款法案的文本内容来看,国会还是为2017年相同的账户提供对外援助拨款。特朗普的许多援外改革计划,如停止资助综合危机基金、把运行数十年的经济支持基金(ESF)与相关项目整合为经济支持和发展基金(ESDF),都没有获得国会的支持。
2018年2月12日,特朗普政府向国会提交了其任上的第二份联邦预算——2019财年联邦预算,“国务院、对外事务及相关项目”预算经费再一次被削减至418.6亿美元,其中对外援助286.0亿美元,分别比2018财年国会拨款减少22.7%和28%,并且第一次取消了自2012财年开始包含在这一部分预算中的海外应急事务(OCO)资金预算请求。不过,在两院的拨款委员会分别于2018年6月和7月通过的法案中,国会对这一部分的经费支持仍维持在2018财年的水平。
从特朗普政府提交的预算大纲以及两个财政年度的预算请求来看,其大幅削减援助预算,取消和合并相关援助账户,尤其是减少发展援助和对多边机构的资助,固然有提高援助效益的考虑,但实际上涉及一个根本的问题,即依靠什么来保障国家安全?主要靠军事力量,还是军事与民事(外交和发展合作)并重?“9·11”事件以来,小布什政府和奥巴马政府选择了后者,两届政府都把发展合作(对外援助)、外交与防务并重,并将它们视为国家安全的三个支点。特朗普则更为强调美国面对的世界充满安全挑战,他把军事力量视为国家安全的根本保证,并否认对外援助和外交的安全功能。
美国对外援助的战略功能:政策争论
目前来看,尽管特朗普政府多次提出削减对外援助支出的计划和预算,但并没有获得美国国会的支持。不过,由削减援外预算引起的关于对外援助功能和本质的争论,则更具有启示意义。总体来看,支持削减者势单力薄,而反对削减者人多势众。
特朗普削减预算的支持者多为保守主义智库人士,包括从彻底批判对外援助的激进人士到认为需要改革对外援助以有效服务美国国家利益的温和派。2017年7月发表在美国外交协会(AFSA)主办的《外交》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代表了对外援助的激进批评声音。文章作者托马斯·迪西特(Thomas Dichter)曾在60多个发展中国家从事了50年国际援助工作,曾任和平队志愿者和国别主任,后来在多个非政府组织从事发展项目的研究和咨询工作。迪西特列举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对于对外援助的各种批评,认为每个国家的发展取决于自身的文化、社会和政治特性;援助不仅对于发展是无效的,还造成了许多国家的援助依赖。那么,国际援助产业为何不减反增?作者的答案是,“对外援助已经成为一个大产业,一种援助产业复合体(Aid-Industrial Complex),它以‘销售’为核心衡量标准,自利使变化不可能发生:事实上,自利阻止了变化”。因此,作者主张把人道主义援助与发展援助分离,减少发展援助。如果考虑到这篇文章发表的刊物和时机背景,那么可以说其观点呼应了特朗普削减援外预算的理念。
温和派中比较典型的是美国传统基金会(The Heritage Foundation)的观点。早在总统选举启动前的2016年2月23日,传统基金会就公布了一份题为《2017联邦预算平衡大纲》(Blueprint for Balance:A Federal Budget for 2017)的建议报告。该大纲提出的基本理念和许多建议均在特朗普的预算大纲和预算请求中有所体现。例如,这份大纲建议:终止浪费和重复的项目;充分资助国家安全,加强国防;10年内,减税1.3万亿美元,减少支出10.5万亿美元,减少赤字9.2万亿美元。在“国务院、对外事务及相关项目”部分,该大纲的建议主要包括:终结海外投资公司,撤销美国贸易和发展局,取消对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人口基金、气候变化《巴黎协定》、全球环境基金、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等多边机构的资助,禁止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资助,反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加大对国际组织的监督力度等。大纲中提出的减少对多边机构的资助、强化预算平衡、加强国防经费预算等建议,在特朗普的预算方案中都得到了充分体现。需要指出的是,传统基金会2018和2019财年的财政建议报告依然沿用了2017财年报告相同的标题、核心观点,以及基本相同的具体建议。概而言之,至少在减少援助、强化军事、减少对多边机构的资助和美国的国际责任、重组援外机构等方面,传统基金会为特朗普政府提供了重要支持。
然而,反对特朗普政府削减援助预算的阵营力量明显大得多,他们来自前国家政要、国会议员、发展领域的非政府组织、著名学者,乃至普通公众。早在2017年2月27日,121名美国退役将军致信国会两院和两党领袖,表达他们加强外交和发展与加强防务对确保美国安全同样重要的信念,敦促国会“确保用于国际事务预算的资源与我们面对的不断增长的全球威胁和机会同步增长。现在不是退却的时候”。而创设总统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PEPFAR)等多个援助项目的美国前总统小布什也反对削减。他在2017年4月13日接受采访时说,继续对外援助“既符合美国国家安全利益,也符合美国的道德利益”。同年4月26日,九名美国前驻联合国大使致信美国国会领导人,呼吁维持对联合国及其机构的资金支持。曾于1993—1996年出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的奥尔布莱特(后担任国务卿)直言,削减联合国预算,将会损害美国国家利益。此外,100多名宗教领袖也致信国会,反对削减援外预算。他们在信中说,“我们感谢美国的全球发展和外交项目,这些项目拯救了生命,保护了宗教自由,也维护了美国的安全”。
美国重要智库对外关系协会(CFR)的一篇文章则从国际竞争的角度称,特朗普削减对外援助预算,在南亚和中亚向中国的影响力敞开了大门。文章认为,按照特朗普的援助方案,美国在中亚地区的援助资金将大幅减少,但与此同时,中国正在迅速增加对整个地区的援助,尤其是看得见的基础设施项目援助,这将使美国处于不利地位。“一带一路”倡议扩大了中国在中亚五国的影响,并使华盛顿处于竞争地位。更为贫困的南亚地区,接受美国医疗援助项目更为广泛,而特朗普大量削减全球卫生预算,将给该地区应对各种疾病、改善营养、提升健康带来巨大挑战。另外,在美国计划减少援助时,中国正在努力扩大在印度洋的覆盖范围和影响力,加强与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等各国的援助关系,使之成为印度洋的主要外交和经济伙伴。
著名国际关系学者斯蒂芬·克拉斯纳(Stephen D. Krasner)在《美国利益》上撰文,强调对外援助对于美国应对安全挑战的意义。他指出,国防经费已经是对外事务经费的15倍,虽然强大的军事力量对于解决美国面临的一些安全挑战至关重要,但是对于防范跨国恐怖主义、流行性疾病和大规模移民的影响等重要挑战,仅靠国防部的资源无法得到充分解决。克拉斯纳认为,对外援助具有非常多的功能,从或多或少的直接贿赂,到支持不那么有吸引力的外国统治者以某种方式助益美国利益;从建设国家能力,到帮助选定的国家走上巩固民主的道路等,这些都可以有效应对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非传统挑战。
概而言之,美国国内反对削减援助预算的声音远远大于支持者,这使得特朗普的削减计划连连受挫。不过,特朗普政府极有可能在其今后任期内的财年预算中继续推动削减援助预算的方案,斗争似乎还要继续下去。
结 语
特朗普把援外资源与安全或国内福利对立起来,削减援外预算以补充国防支出,其背后的理念是美国优先和对军事力量的信奉。其政策的支持者或者出于与特朗普相似的理由,或者认为援助无助于受援国的发展。其政策的反对者,即援助的支持者,实际上来自两个视角:美国利益视角和国际主义视角。美国利益视角的援助支持者,强调援助对于美国本国安全、政治或经济利益的重要性;而国际主义视角的援助支持者,强调援助为受援国所必需。正如特朗普削减援助预算引起的政策争论所显示的,除了发展和慈善领域的非政府组织和宗教界人士主要基于国际道义和受援国需求考虑外,削减援助预算的其他反对者或援助支持者都是以维护美国国家利益为出发点的。美国利益视角强调援助为国家利益所必须,是一项必要的战略支出,其功能为军事实力所不可替代。从这种视角来看,即使对外援助没有促进受援国的发展及其人民的福祉,也维护和增进了美国的利益,它就是必要的。
实际上,各大国对外援助政策的变动——无论大规模削减还是增加,都会引起争议。美国关于援助政策争议的一个重要启示在于,一个在全球有广泛影响和利益延伸的国家,不应当把援助支出与其他支出和国内福利对立起来,也不应仅仅从援助对受援国的发展效用来考量援助的必要性和有效性。维护必要的政治联盟、促进投资和贸易等经济利益,塑造负责任大国形象,与外交和其他途径相配合增加广泛的国家利益,都使适度规模的对外援助成为必要。
注释略
作者系陕西师范大学哲学与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来源时间:2018/12/9 发布时间:
旧文章ID:175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