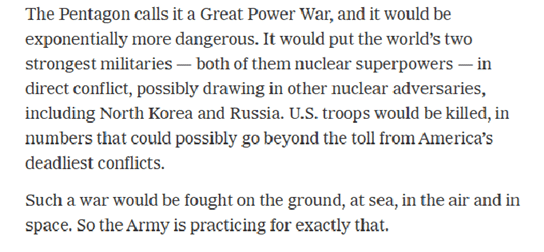马克·格里夫:公共知识分子怎么了?
作者:马克·格里夫 著 吴万伟 译 来源:共识网
多年来,美国期刊中没有数字化的精英一直是《党派评论》。去年该刊的守护者最终也让其数字版上线了。其某些神秘性仍然得以保留,因为版式依然不好使用,在搜索的时候显得笨拙和令人绝望。即使在最新的数字形式中,该刊仍然不失其卓尔不群的姿态。
《党派评论》的极端重要性并非源于最近的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姿态。最初在该刊上发表文章的传奇人物可以在任何一家优秀的图书馆中找到,也可以在当时还默默无闻的未来之星投稿者的文集中找到,如玛丽·麦卡锡(Mary McCarthy)、克莱蒙特·格林伯格(Clement Greenberg)、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索尔·贝娄(Saul Bellow)、伊丽莎白·哈德威克(Elizabeth Hardwick)、莱斯利·菲德勒(Leslie Fiedler)或者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除了这些人外,《党派评论》还拥有欧洲思想精英的作品或英文原文或译文:萨特、加缪、让·加奈特(Jean Genet)、波伏娃(Beauvoir)、厄斯特·荣格(Ernst Jünger)、卡尔·雅斯贝斯(Karl Jaspers)、戈特弗里德·贝恩(Gottfried Benn)加上艾略特(T.S. Eliot)、奥威尔(Orwell)、奥登(Auden)、斯蒂芬··斯彭德(Stephen Spender)等。
《党派评论》获得了冉冉上升的未来明星的最初作品或名家的最好著作,虽然它的资金极度短缺,编辑部人手少得可怜。但读者在该刊上最初读到的内容后来大都成为美国本世纪中期文学的课程经典。
但是《党派评论》在过去几十年里的确因为在辩论中的立场非常重要,如果辩论中没有它的观点就会被认为是大有问题的。该刊比20世纪中期的其他任何出版物都更可能是被卷入小型文化战争的令人尊敬的掩护马(stalking horse)。争吵涉及的问题是被笨拙地称为“公共思想”领域,即“公共知识分子”驰骋的舞台。加州大学历史系教授拉塞尔·雅各比(Russell Jacoby)在1987年文化战争初期对“公共知识分子”的定义不过是“面向民众和受教育读者写作的作家和思想家。”《党派评论》表现出来的习惯性主动出击体现出的是已经过去的世界,那些人政治立场强硬、文化水平高深、思想论证严谨、与大学格格不入,因为他们的目标对象是更广泛的非学术界读者群。该刊据说比我们当今拥有的任何论坛都更具影响力和生命力,相比之下更显示出当今出版物和编辑的蹩脚水平。《党派评论》成为标志自1960年代末期以来“我们丧失的东西”的典型化身(该杂志创建于这个时期的事实与此后持久衰落的阶段可能并非偶然的巧合。)
我们对于“公众”的集体看法出了毛病。
十多年前,还是研究生的我坐在耶鲁图书馆期刊室阅读《党派评论》的纸质版。我读完了从其1934年创立到开始走下坡路的1955年的所有文章。维持几十年的发展势头是一个了不起的奇迹,其强大威力足以在一两个月内彻底征服20多岁的年轻人,他本来可能对即将到来的伊拉克入侵而激动不已,迫不及待地中断课程学习去谷歌上搜罗来自《美国有线新闻网》(CNN)、《国家》和《新共和》的各种消息。
除了好奇心之外,我阅读该刊有两个目的。首先是学术研究。我已经开始了一项课题研究,十年之后将成果集结成为一本书,那是另类的20世纪中期思想和文学史。12年前的另外一个阅读目的是开始创办一本小刊物《n+1》。我一直被那些呼吁复兴公共知识分子主义的人称为笨蛋,但是我很清楚他们的解决办法是多么令人不满意。我和其他创办人在没有获得资金支持的情况下想象了一个开玩笑的标题来表达对现状的不满:“思想危机的解决办法:资深学者撰写时事评论。”更年轻的一代能够介入吗?我在图书馆搜索和我们创办刊物都隐藏了迎接时代考验的努力。21世纪之后的思想生活会如何呢?我们的世界仍然像从前一样拥有丰富的可能性吗?我们失掉了什么?
从幼稚地首次阅读《党派评论》给我留下最持久印象的发现是该杂志的确好得难以置信。该刊比我期待和想象的要好得多,可以说是本世纪最伟大的美国杂志。人们一年到头都能在上面看到精彩纷呈的系列文章,从冬季到秋季(季刊)或1月2月到11月12月(双月刊)每期的每篇文章都引人入胜,每期至少都有一两篇大师的文字。
但是,该刊之所以精彩其实与通常的说法或怀旧论者的解释大不相同,尤其不同于当今普遍理解的所谓迎合大众心理或竭力吸引“普通读者”的做法。在我看来,这一发现让我的“我们丧失了什么”的意识变得复杂起来,在一定程度上我至今仍然感到困惑。我们是否失掉了什么东西?光靠“意志”或“影响力”或“参与程度”能够重新辉煌吗?
如果你问让《党派评论》成为伟大期刊的条件,即转向调查20世纪中期“公共思想”的创造历史的必要条件,就可能面对某些难以驾驭的历史特殊性。
首先是美国共产党的刺激。《党派评论》最初是美国共产党纽约总部的青年俱乐部刊物。从1934年到1937年,编辑听从苏维埃的指令撰写无产阶级文章,刊物带有明显的共产党色彩。21岁的投稿者因为休产假离开,编辑称赞她的努力是“为苏维埃美国生产未来的公民”。接着从1937年开始,文化政策的变化导致共产党抛弃了青年俱乐部,两位编辑菲利普·拉夫(Philip Rahv)和威廉·菲利普斯(William Phillips)让《党派评论》采取独立姿态。
其次是大萧条的平等化威力。伴随全球资本主义崩溃而来的是对重建社会主义的期待,更实际的是拥有了很多自由的时间,这么多人无论老少都失业了,而且思想派系林立。正如威廉·菲利普斯在早期所写的那样“我们很多人来自小资产阶级家庭,有些人当然还属于无产阶级。但是经济危机的重压已经把我们大部分人(和我们的家庭)挤到生活拮据甚至饿肚子的困境中。”编辑部在周末之外的下午组织开放性的小说和诗歌工作坊。《党派评论》在1937年的政治独立性不过是意味着没有斯大林的革命社会主义。由于摆脱了党的束缚,其第一代犹太人创立者与年轻的美国知识分子建立其联系,如耶鲁和瓦萨尔学院(Vassar)出身的如德怀特·麦克唐纳(Dwight Macdonald)和玛丽·麦卡锡。他们带来了金钱和关系网让这个刊物维持下来。正是这种混合性的人口学特征造就了该刊的特色:政治激进主义的黄金时代、美学上的高度现代主义和思想史家最羡慕的傲慢自负。
接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争爆发把欧洲知识分子赶到纽约的怀抱中。国际主义已经成为坚定不移的原则。但是人们期待最重要的变化出现在欧洲大陆,其最伟大的思想家还都留在那里。但到了1940年代,大量欧洲精英、犹太人、左派或反法西斯学者和艺术家涌进美国,变成了纽约或好莱坞的难民。大部分人渴望结识坚定承诺于同样观点和思想兴趣的美国群体。“纽约知识分子”其实是欧洲人。虽然《党派评论》在1940年因为美国参加战争而陷入内部分裂(反叛分子进入两家新刊物《政治学》和《评论》),但是对欧洲灾难的了解使得他们变得特别强大。该刊的成功证明了国际名家和来自布朗克斯的犹太人无名小卒汇合的合理性。
这个特征也让刊物在机构上更有潜力。知识、左翼、反共和欧洲移民的亲身经历的结合,所有这些都通过大都市的美国文学和艺术网集中起来,这是罕见的融合。随着美国成为孤独的西方超级大国,美国国务院试图笼络欧洲以便摆脱苏联的影响,对这种融合的需求越来越大。《党派评论》获得了一种既得利益者的支持。正是这个其成功因素让有些历史学家感到遗憾,他们说该刊的威望有些名不副实。对批评家来说,就好像批判性思想的桀骜不驯者团队已经成为别人的武器。该刊与既得利益者的联系标志着理查德·霍夫斯塔特(Richard Hofstadter)在1963年的《美国人生活中的反智主义》的著名宣言中令人不舒服的一面。在其他地方反对市侩主义的《党派评论》已经成为“美国思想界的机关刊物(house organ)。”但这个机关刊物已经变成了社会共识的代言人?
所有这些都被此阶段的那些烦恼者很好地咀嚼消化。有些人哀叹《党派评论》的激进主义,有些人哀叹其所谓的自由派美国主义和爱国主义。不过说出来的话常常是《党派评论》的作家和评论家拥有我们没有的勇气和自由。特别奇怪的是,这些后来的颂词特别集中在不受大学束缚的自由上面。那些在思想论坛上面对公众和“受教育的读者”大声疾呼的勇敢者,在思想广场的光天化日之下自由驰骋,他们不受到专业化和专业主义的破坏,也没有装腔作势的毛病和意识形态的侵扰。(拉塞尔·雅各比在后来曾经回顾到“不是过于富有戏剧性,但我有时候仍然忍不住想到我们见证了新知识分子阶级的崛起,他们使用一种仅仅知识界才能看懂的新学术风格,那些学人已经背离了公共生活和公共事物。”)
从个人角度看,我认为我们时代所缺乏的这些旧条件或者微调并不预示着像从前时期那样伟大的公共思想的新生。我也认为“大学”不应该为已经出现的变化承担责任。如果我要试图表明到底什么东西产生了与我们时代不同的差异,我会被带往其他地方。我觉得我们对“公众的集体观点”出了毛病。
受《党派评论》的数字版重现的刺激,《高等教育记事评论》邀请我对比该刊和当今2015年的“思想界现状”时,我承认我的心一下子沉重起来。在天使不敢踏足的地方涌进来大量傻瓜蛋,在当今时代,在你听见历史电钻的呼呼声中,很难区分哪些是昙花一现的泡沫哪些是真正的基石。但是我的确感到肯定的是有关当今“公共写作”和论战的普遍的好意的论证其实是误入歧途的,攻击大学的言论惹人讨厌。这与那些挑《党派评论》毛病的挽歌作者的做法并非没有任何关系。
因此,我想指出怀旧派对《党派评论》的看法有些是错误的,至少从1930年代到1950年代的主要阶段来说。首先是它被去除了激进派色彩,或者仅仅变成了既得利益者的政治工具。该刊的确不再是托洛茨基主义者,支持美国反对纳粹的战争,但它仍然保留未来社会主义的前景,而这可能是令《纽约时报》的头发都吓得竖起来的景象。我认为要点是人们并不总是需要弱化激进的政治观点以便得到掌权者的认真对待。在所有方面都保持优越和实话实说或许更好些,让愿意妥协者前来找你才好。
第二是它彻底美国化,逐渐认为其远大志向是美国民族主义,美国是权威和世界思想的真正源头。其实真相正好相反,欧洲仍然是别的世界—更大的世界,纽约知识分子继续认为欧洲是他们必须依靠的和用来盗火的奥林匹斯山。我们更加新颖的唯我论没有别的地理场所可以求助和模仿,虽然美国思想已经风行全球,但它似乎还非常幼稚和危险,与1945年或1960年证据显示的情况不同。
第三,最复杂的是《党派评论》及其思想家和理论家的观点让他们生活在大学之外。对那些富裕的畅销书作家或者1920年代的小期刊现代主义者来说,这或许是真实的,但是在1950年代已经不符合事实了。更民主的思想意味着更少思想家拥有“独立的谋生手段”,意味着几乎所有人最终都不得不靠教书谋生。欧文·豪(Irving Howe)成为布兰迪斯大学教授,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成为哈佛教授,莱昂纳尔·特里林(Lionel Trilling)和杜皮(F.W. Dupee)已经在哥伦比亚大学,悉尼·胡克(Sidney Hook)和威廉·巴瑞特(William Barrett )在纽约大学。汉娜·阿伦特在纽约新学院大学,索尔·贝娄的大部分时间在芝加哥大学,莱斯利·菲德勒在蒙大拿大学,而贫穷的戴尔莫·施瓦茨(Delmore Schwartz)则在任何能找到的大学讲授创造性写作课程。甚至《党派评论》的编辑菲利普·拉夫和威廉·菲利普斯也都教书去了。该刊后来得到罗杰斯大学和波士顿大学的资金支持。
在2007年2008年大萧条到来后,我不无遗憾地提醒朋友和学生注意到20世纪的大萧条虽然带来了灾难但对于思想界来说却是惊人得好。我认为我们现在拥有了思想繁荣所需要的混乱、不公和经济不平等,只要看看当今的美国就明白了。在薪水和发展前景方面,作家、教师、辩论家和梦想家阶级、小资产阶级或无产阶级已经确实变得更加平等了。或许他们需要更加平等,真正采取关注美国大众生活的措施,但对现状的厌恶当然是足够强烈的。至于去政治化过程,一方面学生热衷于激进社会变革的哲学中,另一方面清醒地观察当今秩序的腐败。我不知道谁的书架上没有马克思的著作或者女权主义者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Wollstonecraft)、乔姆斯基和娜欧蜜·克莱恩(Naomi Klein)的著作。我们失掉的东西是真正的党派政治,取而代之的是以音乐为中心的附属文化,那些成为年轻人组织或自我组织的主要灯塔。随手翻翻过去30年的任何一本杂志的封面,你就会发现网络杂志(zines)和自己做运动的朋克摇滚(DIY punk rock)的远大志向。(嘻哈音乐(hip hop)或许通过不同的渠道发挥了平行功能)。但那可能是另外一个场合谈论的话题。
这里谈到大学问题。当今时刻的高等教育经济学对我们许多人来说或许很糟糕,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和当今考生。但是,这再一次不应该成为对公共思想或者公共辩论的先验性的坏事。正好相反。大量愤愤不平的自由思想者实际上并没有饿肚子,他们集聚在当地的很多运动中心,他们的职业活动使其掌握了能够参与辩论的大量的知识和技能,拥有24小时接触研究性图书馆的机会,这些或许成为空前的公共辩论家。
但是,我认为“大学普遍化”的哲学的和道德的影响仍然是从20世纪最后十年到现在的最深奥思想现象,迄今为止的解释都非常糟糕。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不知道自从退伍军人权利法案(the GI Bill)以来的人口变化或历史原因,我们有足够的统计学资料。我的意思是我们并没有提供说服力强的猜测性历史或者对思想发展产生定性影响的富有深刻见解的描述。
令人困惑的是,“思想大学化”列举了若干重叠的变化。最重要但没有得到充分认识的是这样一个过程,其中每个社会阶层的几乎所有未来作家都逐渐获得了大学学位。另外一个变化是很多作家取得的进步,记者、评论家、诗人、小说家和批评家、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无论是否终身教授,都从其阶段性的大学教书的生活经验中吸取营养。(这种情况在1940年代和1960年代公共思想的“黄金时代”几乎就已经开始了)。第三,必然结果是职业融合,从前独立的文学艺术(小说、诗歌、甚至文化批评)逐渐被当作学分课程和授予学位的课程来讲授,毕业证书螺旋上升的需求让新锐批评家和知识分子去选修这些课程和获得学位以便靠讲授这些课程来支付房租。
我们的任务是让“公众”变得更精彩,更具怀疑精神和反抗精神和更加危险。
但是,大学的严肃性、强度和高贵性并没有因为作家与商业领域的仍然维持的纽带而传播开来。大学仍然是个偶然现象,是文学面孔上的污点。讨厌学界人士,认为当教授不利于作家和批评家的创作实践,这些仍然是在商业性著作中维持一席之地所必须的品质。也就是说人们必须在精神上与大学保持距离,同时在经济上依靠大学。我大胆地提出大学以及广义的文化的长期趋势应该是变得更加包容,同时在其终极幻象—“真实世界”看来也越来越不重要了。重要的是看得见的身份认同、人文和艺术学科的开放性专业知识权威、或高傲的口吻或大学风格—所有这些大学技能(和薪水)帮助你面向大学之外的公众发言。(这并没有回答艺术和思想会产生什么样的无意识的影响和决定性)但是,这绝非一个不可避免的结论。
这里我想做出个人忏悔。在《n+1》初期,我们预料的概念实际上取决于能否打动那些没有充分认识到的学界人士的心弦。我们这些创办者都20多岁,都有大学学位(我们中有一把把的文学硕士、艺术硕士甚至副博士学位),但没有工作。仰望那些已经更上层楼的人,那些愤愤不平的教授候选人似乎是等待我们释放的天然资源。就我而言,敢肯定如果我们重新创立了经典的公共知识分子模式,在公众眼中树立起严格论证的形象,观点深刻、论证合理,而且没有“文献综述”的累赘和对导师的言听计从,这些年轻教授们将会聚集在我们的旗帜下,就像从前的那些人一样提出经典的公共知识分子式的深刻见解。只要想想那些悲催的副教授们,甚至刚刚拿到终身教授岗位的人都异常沮丧,都拥有需要严厉批判的众多内容(拥有银行家的研究文献)扔掉惯常的谨慎,挣脱牢笼自由翱翔的场景。漂亮的鸟儿,自由飞翔吧!
巨大的个人失望—这让我困惑了很长时间–是年轻教授们基本上没有送给我们想要印刷的著作。我知道他们的专著质量很好,他们是卓越的思想家和作家。但是先要声明一下,我遭遇的问题绝不是学术界的陈词滥调,不是晦涩难懂或者专业化、专业术语和“没有能力”向非学界人士说话。令人尴尬的真相正好相反。当这些杰出学者在考虑为公众写作时,他们似乎很高兴地把困难抛在身后,双脚跳入口语的大海,随意添加不自然的笑话(坦率地说并不可笑的笑话),在电视上侃侃而谈,采取一种亲密的油腔滑调的口吻。简而言之,他们非常真诚地好心地要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似乎公众和广大受教育的读者比他们适应性、灵巧性和批判性都更少。为公众写作惊醒了大众媒体的俚语。公众就意味着好玩儿、粗俗和嘻嘻哈哈。甚至在大众文化的很多所谓“知识分子的”但自贬身价的媒体上,采用居高临下的恩赐态度用没有任何特色的时尚杂志的行话对读者讲话当然是真实的,任何其他选择似乎都不合适。
需要强调的是,这不是从前的“公共思想”和《党派评论》对民众讲话的方式。请不要责怪年轻教授,(应该说,研究生们比教授做得好多了,他们仍然为《n+1》投稿)。
假如我们尝试对从前的公共知识分子观点做出不同的边缘性描述。20世纪中期的“公共思想”揭示了在机构上具有欺骗性的文化。它吸引了很多人去描述大学里讨论的哲学的、美学的、甚至政治的观点。它将这些观点传播给读者和主要是大学老师和大学工作人员的订户—这些季刊是靠订阅、慈善基金会和大学补贴提供资助来维持的。但是这些刊物创造的文化消除了大学出身或地位标志,拥有对纯粹的学界空间困难和挑战的共同认识。这些期刊设想了一个来自“真实世界”的欲望和要求呼唤成立的领域。这个认识或幻觉最终得到方方面面的拥抱和支持,如作家、读者和订户,甚至还有真实世界本身的某些部分,即商界、附属性媒体和政治界,甚至政府和公民社会的“官方”机构。这种集体认识在某种方式上呼呼促成了该空间的出现。
但是让这种复杂的安排发挥作用的额外哲学因素和各方维持幻觉并使其显得真实的(我们谈论的是观点领域,公共的共享观念就是现实)是对“公众”充满激情的估计。在此意义上,激情不一定是高尚的或高贵的,甚至也不是吸引人的或有商业价值的,正如我们当今在提及奢饰品品牌时使用“激情”一样。它是某种中性的观点或者期待,即你能够或者应该比现状更好些,你自然想比现状更好,愿意做出某些努力变成更有本事和更有价值的人,这是每个体面人都要做的事。我对《党派评论》时代的公共知识分子的真正写作的认识是,它总是瞄准想象的大众头上稍高一点儿的地方,这个高度必须是他们稍微抬抬脚就能够得着。但是,这种写作似乎总是稍稍超过《党派评论》作者群现有的水平。这些知识分子竭尽全力关注,踮起脚尖,仔细掂量利弊,最终成为他们渴望加入的公共思想大合唱中更有思想深度和更具影响力的高音歌手。他们也是大众,但是这个大众是人们渴望的更好和更高的大众。他们因为敢于挑战公众和自我,敢于探索艰深的问题而暂时出类拔萃,因而赢得了权利向平等者组成的大众讲话。
激情也毫无疑问包括了战后阶段的强制性的、不断改善的、警惕性维度。这种思想认为公众必须有所改善否则就会变得更坏。公民精英的激情总是要指导民众,让他们变成公民而不是“群众”。据说法西斯主义和苏维埃主义都是群众疯狂的结果。退伍军人权利法案和国家支持下的1945年后高等教育范围的扩大依靠的就是作为国家和民族等概念的基础的公众认识,这种公众如若不加改善将是危险和不稳定的。这样的公民应该为国家而战,从技术上和经济上说,将与国家的全球对手进行激烈竞争。公众必须坚持某种“民主”观念和意识形态才能保持稳定,这是连最糟糕的精英主义者也都赞同的观点。因此,20世纪中期的共识是高等教育应该能“制造”或塑造自由社会的公民,这是人们能从那个时代听见的最好也是最糟糕的声音。
我们那些珍视大学的人像其他人一样强烈地觉得,与从前的概念相比,“公众”意识形态已经发送了戏剧性的改变。毕竟,这是在越来越卑贱的、蔑视的、反民族主义的“公众”版本,大学在政治上受到贬低,人文科学的价值因为职业前景不佳而受到蔑视,国家对公立高等教育的兴趣大幅丧失。1970年代至今,从上到下的从高官到民众的全体国民的冷漠反映出一个新发现,那就是从前的价值观和公众的可怕是错误的。聚集起来的大众不再是个威胁,也不再有此需要。越南战争之后不再需要公众服兵役,因为拿军饷的志愿军无需再有激动人心的抗议。国家也不再需要公众进行大规模的生产,因为劳动力也被出口。美国私立大学培养出来的少数全球性精英群体将设计所有新技术和金融工具用以帮助美国的发展和GDP的高速增长,虽然增长以几何数级但财富分配并不平等。
把学生和教授放在舒舒服服的大学里享受的大众性国民教育带来的不是稳定而是抗议,这种状况在1960年代后期开始出现,尤其是加州公立大学体制中最优秀的大学。公众中的其他人并没有起来制造麻烦,虽然他们被新秩序抛在后面。惊恐的和能干的民主社会公民不再能从电视、好莱坞或恭维大众的各种形式的交流中找到声音,就好像我们喜欢变成哑巴和无能之辈,没有地方找到思想激情的刺激和惊醒。美国公众和多数人所需要的不过是持续不断地消费,只要这个要求不至于给国家造成太多的负担就行,那样的话可能需要在短期通过实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来完成。即便工资增长停滞,商品仍然会以新的低廉全球化劳动力的成果形式出现,劳动力价格低得惊人的成本可以被放在各种信用卡上。我只是回顾了我们都学会感受到的历史和老掉牙的常识。
果真如此,任何地方的知识分子能够用华丽的修辞的文笔消除影响就不够了。就优先选择的辩论而言,理想将继续留在我们世界的一角,我们应该试图将其放在适当的位置。21世纪的公共知识分子的观点应该少些知识分子色彩,少讨论知识分子的方法和地点,他们应该来自各个行业领域,竭力恢复人们对公众的最高评价。如果你不接受当今媒体传递给我们的公众构建,公共思想就是最宝贵的。知识分子要记住:你我都是公众。它就是现在的我们,就是还没有上大学的孩子时的我们,或者是退休后的我们,你可以选择喜欢的最佳时刻。但是公众一定不能是不比你聪明不比你努力的人。最好是想象公众类似于你希望成为的那种人。(知识分子停止为自己与大学有瓜葛而感到羞耻将是聪明的,无论这种联系是紧密还是松弛。那样的看法是懦夫的表现,而且常常无关紧要。)
如果有一个任务,那就是参加到创造新型大众的活动中,这种大众更聪明、更具怀疑精神和反抗精神、更有能力自我保护、对精英和稳定来说也更加危险。说到教育,这种大众对大学应该是为有钱人而不是公众办的观念来说更加危险,对不知不觉产生的美国大学应该为全球富豪服务而不是为地方或全国的政治服务的观点充满敌意。重新创造公众观念,即平等、优秀和自主的公民并不能单单指靠公共知识分子,它需要各方面的努力。但是,如果需要有人来揭露令人厌烦的媒体的虚假公众文化和“宏大观点”的真面目—愚蠢,恐怕还真是非知识分子莫属。
作者简介:
马克·格瑞夫(Mark Greif)纽约新学院大学文学研究副教授,《n+1》杂志创始人和编辑。著有《人危机时代:1933-1973年美国的思想和小说》,刚刚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
译自:What’s Wrong With Public Intellectuals? By Mark Greif
http://chronicle.com/article/Whats-Wrong-With-Public/189921/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thought/zhongxi/20150215121146_all.html
来源时间:2015/2/16 发布时间:2015/2/15
旧文章ID:20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