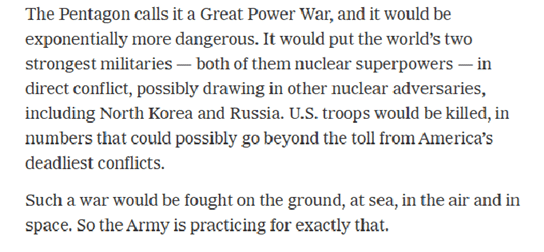弗格森骚乱与阶级偏见
作者:戴维·布鲁克斯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在过去几个月所有关于弗格森的讨论中,有一个特征就是与民权运动时代的类比显得何其单薄。人们想方设法把弗格森与塞尔玛游行(Selma)和吉姆·克劳法(Jim Crow)联系起来,但是有些地方对不上。
一定程度上,那是因为我们已经从简单转向了含混。在我们的国民生活中,民权斗争是再分明不过的对错之争。而关于弗格森的争论,在最明智的人当中引发的反应也是一言难尽的。
新奥尔良圣徒队(New Orleans Saints)近端锋本杰明·沃特森(Benjamin Watson)在Facebook上发表了一篇被人疯转的短文,文中透彻地表达了这种复杂性。沃特森列举了弗格森之乱引起的12种不同的情绪,包括:
“我愤怒,因为那些代代相传的冤案故事,好像现在就在我们眼前继续发生着……我觉得被冒犯了,因为我看到了一些侮辱人的评论……我在反省,因为有时候我会去站在‘我们’这一边,而不去看这类情境下的事实如何。”
然而,还有一个原因导致和民运时代的类比是不恰当的,那就是种族主义的本质已经变了。它已经从基于基因的偏见,转向了基于阶级的偏见。
要解释这一点,我需要先说一说历史。在18、19世纪的英国存在“体面”社会和贫民窟的区别,后者有时也称为“乌鸦窝”(因为贫民住宅区让人联想起那些偷东西的乌鸦所生活的犄角旮旯)。
生活在这些贫民窟里的人,在言语中往往被当作动物而非人类。比如在1889年《宫廷期刊》(The Palace Journal)上的一篇文章中,阿瑟·莫里森(Arthur Morrison)有这样一段描写:“黑暗、无声、不安的影子纵横交错——人寄居在这个散发恶臭的污秽之地,就像每一个充满毒害的角落都有妖精在呼吸。女人凹陷的眼睛带着黑眼圈,苍白的脸在偶尔点亮的煤气灯下时隐时现,那模样太像没遮盖好的骷髅,以至于她们一望过来,就能把我们吓到。”
在那个时代,“体面人”对贱民世界的生活既厌恶又好奇。他们会去穷人聚居区过贫苦生活,这种贫穷之旅仿佛是如今的真人秀,或《杰瑞·斯布林格秀》(The Jerry Springer Show)里的厮打。
时至今日,我们再一次面临尖锐的社会割裂,一方是“体面”的精英阶层,一方是与精英阶层无缘的人。在一个世界里,你身边的每一个人都至少上过大学,大家极少接触到另一个世界的特征:监狱、冰毒、发薪日贷款、婚外家庭形式盛行。在这个世界里,人们认为自己可以左右自己的命运。在那个世界里,有的人奉行一个如今很普遍的座右铭:“怎么做都是一样的结果。”
阶级差距的拉大会造成阶级偏见,阶级歧视。这种偏见是基于一种对能力的本能态度产生的。“体面”阶级的人有着精英的美德:管控功能、坚毅、耐得住性子。而对那些身在贱民世界的人的看法是,他们缺少这些特质。他们没有规划。他们暴戾、可怕。鉴于童年创伤、贫困压力等等因素,这样的看法有一些属实的地方。然而它经过扩散转移,变成了一种恶毒的、不假思索的刻板印象。过不了多久,把这些人当动物来描述的情况就会出现。
这种阶级偏见适用于所有穷人,无论白人还是黑人,他们的人群特征是重合的。但是阶级歧视与潜在的、历史悠久的种族主义结合起来,会酝酿出一种格外恶毒的东西。如今人们只需看一眼肤色,就能得出一整套普遍认为的底层人特征。
民权运动时代始终在辩论什么是民权问题,什么是经济或社会问题。现在,这道界线已经被抹去。所有的民权问题,同时也是经济和社会问题。阶级歧视和种族歧视是纠缠在一起的。
在弗格森这样的事件发生后,总是会有人说,我们需要就种族展开一场全民对话。这不无道理。我们都需要提高我们感同身受的能力,让我们能更好地设身处地,去想象那些与我们境遇不同的人是如何生活的。对话是有用的,但我觉得小说、艺术品,或者像克劳德·布朗(Claude Brown)的《乐土上的男孩》(Manchild in the Promised Land)这样的书,或许更有用。
不过,归根结底,我们需要的不是一场全民对话;我们需要一个全民计划。如果整个国家能通过奥巴马总统发起的“弟兄守护人”(My Brother’s Keeper)这样的活动,共同去改善所有种族的社会流动性,那么社会差距会缩小,阶级歧视会消退,种族偏见也会间接地减少。
友人之间是不会坐下来谈论他们的友谊的。他们在一起做事情。透过共同的事业,大家克服分歧,成为朋友。
翻译:经雷
来源时间:2014/12/8 发布时间:2014/12/4
旧文章ID:8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