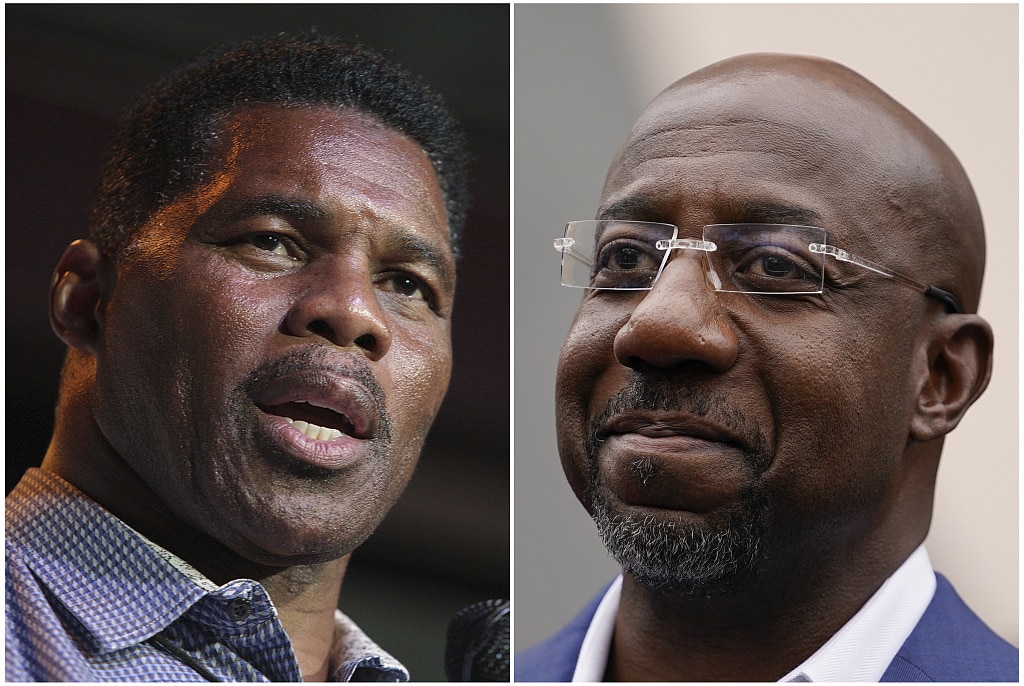美国革命给美国政治文化带来了什么?
作者:埃里克·方纳 来源:东方历史评论
许多人将唐纳德·特朗普在竞选活动中表现出来的种族主义、仇外心理和暴力视为一种反常现象,就好像理性的辩论是美国政治的默认模式一样。然而特朗普之流并非前无古人,美国历史上曾经也有过一些总统候选人就是靠着诉诸于人们被夸大的恐慌、真实的愤懑情绪以及出于本能的偏见而在选举中获得种种利处。特朗普的“前辈”中有19世纪50年代反对移民的“一无所知运动”参与者(注:Know Nothing,“一无所知运动”是美国19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由本土美国人发动的一场政治运动,该运动致力于控制移民入境),“种族隔离”时代的白人至上主义政治家以及更晚近的包括乔·麦卡锡和乔治·华莱士在内的政治贩子和煽动者。更不用说体面一点的,比如尼克松这种——他的“南部战略”(Southern strategy)利用了南方各州白人选民对黑人在民权运动中所取得的成果的怨恨情绪。(尼克松可以用“体面”这个词来形容这点足以说明自1970年代以来,我们在政治上的标准实在没有多少提高。)暴力在美国政治史上亦不鲜见。在19世纪的美国,每到选举时期,国会里会发生斗殴,各大城市则会爆发骚乱。一直到了20世纪,生活在南方各州、想要行使选举权利的黑人还会面临三K党以及类似群体的暴力报复。
这一切的起源是什么?艾伦·泰勒(Alan Taylor)对此给出了一个惊人的答案:这一切起源于美国为独立所进行的斗争(美国革命中发生的多场革命)。泰勒认为,种族主义、暴力、用污言秽语辱骂对手……所有这一切从一开始就是美国政治文化的一部分。泰勒决意与那种已然进入到历史研究领域中的冷战宣传分道扬镳,这种宣传认为:美国革命与“恶劣的”法国、俄国革命不同,这两个国家发生的革命最后都蜕变为暴力的阶级冲突,然而美国革命则是一场由团结的美国人民发动的反抗英国统治者的克制而又不失礼节的斗争。他明确指出,事实上,美国革命是一场的激烈的、拥有诸多面向的斗争,其中保皇党和爱国者,白人与黑人、印第安人之间都处于冲突之中。正因为此,他的新作的书名才叫做《美国革命中的诸多革命:1750-1804年间的美洲大陆历史》(American Revolutions: A Continental History, 1750-1804)。
泰勒不认同殖民时代本质上是美国独立前奏这样一种为很多人所接受的观点。他指出,在18世纪中,整个英属北美的殖民者与母国的关系变得越发紧密,而非渐行渐远。他们“为英国宪法感到欢欣鼓舞”,为英国对法国所取得的军事胜利而庆贺,视英王为自己与天主教敌人作战的支持者。在经济上也是如此,他们与英国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不同殖民地的领导人与英国政府的联系比他们之间的联系要多。当第一届大陆会议于1774年召开时,约翰·亚当斯说,代表们“相互很陌生”,彼此之间都不了解对方的想法和经验。
那么,导致北美殖民地走向独立之路的原因是什么?大多数对即将到来的美国革命的叙述集中在美洲东部城市发生的抗议活动,这些抗议活动针对的是英国政府为在殖民地征税以及为迫使殖民者更大程度上臣服于自己所采取的行动;泰勒对当时在西部正发生的事情更感兴趣(在殖民时代,所谓“西部”是指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的区域)。英国在七年战争中获得胜利,法兰西帝国因之丢掉了北美大陆,阿巴拉契亚以西区域的控制权从此落入英国手中。紧接着,英国政府颁布了《1763年公告》,该公告禁止殖民者在阿巴拉契亚以西区域定居,以避免与印第安人发生无休止的战争。英国政府力劝想要获得土地的殖民者考虑去之前属于法国和西班牙所有的地区,比如加拿大,东、西佛罗里达州,还有加勒比海地区的一些岛屿,可是没有多少人对这些地方感兴趣。殖民地居民“如今认为自己应该做想做的事情”,一位英国官员在1768年这样写道。到了1774年,居住在“公告线”以西地区的定居者达到5万多人,那里的定居者、印第安人和土地投机商之间经常爆发暴力事件。英国人发现自己的处境极为艰难,一方面,他们因尝试阻止殖民地居民在西部定居,此举引起了人们对其假想中的专制的反对;另一方面,他们因为未能执行《1763年公告》中的政策而遭到蔑视;另外,他们的所作所为似乎是站在了抵制外人入侵自己土地的印第安人一边。泰勒写道,到了1775年,在西部定居者心中,“大英帝国全部的信誉和影响力都已不复存在了。”
泰勒没有忽略英国政府对殖民地征税所招致的日益严重的危机——毕竟,这是人们更熟悉的故事:从1765年的《印花税法案》到波士顿倾茶事件以及1774年英国政府通过的《不可容忍法案》(Intolerable Acts),再到独立战争爆发和美国独立。但是,他还就殖民者之间越发剧烈的分化进行了研究。反抗英国统治的领导人依靠的不仅仅是有关税收、代表这样一些抽象的论点("No 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而且也有赖于一些超出法律管辖之外的委员会和暴徒的力量;他们在反对者身上泼上柏油,黏上羽毛。 泰勒写道,”爱国者以自由的名义压制言论自由,私自拆开私人邮件,恐吓他们的批评者。”当独立战争最终于1775年爆发时,美国社会分裂成了许多块。泰勒写道,这场战争的发动者并非是“团结一致的美国人民”,争取独立的战争很快变成了一场内战,许多家庭破裂,邻里反目,地方发生的暴力事件比军队之间的战斗更加惨烈。 他指出,“一个被掠夺一空的农场比一次光荣且胜利的冲锋更为常见。”美军将领纳撒尼尔·格林(Nathaniel Greene)这样写南部各州的偏远村镇,“辉格党人和托利党人相互厮杀起来如同猛兽般凶猛,整个国家有被他们毁为一旦的危险。”
即使在爱国者的行列里,冲突也迅速爆发了。在一个国王、贵族和严格的社会等级制度的世界里,托马斯·杰斐逊在《独立宣言》中所宣称的“人人生而平等”这样的话语成了团结所有无依无靠者的战斗口号。阿比盖尔·亚当斯(Abigail Adams)恳求她的丈夫约翰·亚当斯要“记住女士们”,她指出,女人和男人一样,那些自己没有发言权的法律约束不了她们;今天的很多人们都能够记起她的这番话,而我们对亚当斯的回应则不太熟悉。亚当斯不但完全不理会妻子的这番话,而且还指出,革命者有关自由和平等的说辞让许多人们开始要求更大的权利,这让他感到惊讶,也令他感到惊慌:“我们被告知,我们的斗争令所有地方的政府组织变得松散;儿童和学徒不服管教;许多学校、学院的氛围变得骚动不安;印第安人轻视他们的监护人,黑人对他们的主人表现得越来越无礼。”亚当斯在美国独立问题上是激进派,但在这个新国家社会结构的问题上,他的立场完全不激进。对他而言,这种为追求平等而发生的动乱是对自然秩序的冒犯;而对于其他人来说,这正是美国独立战争的本质所在。
那些刚刚获得权力的普通人抓住机会针对那些长久以来令他们厌恨的事情采取行动。在战争期间,被指控囤积货物的商人遭到了城市里暴民的攻击,地方委员会给必需品制定“公平价格”,以此来打击猖獗的通货膨胀。国会引入征兵制,但是允许应征入伍者找他人替代,或者支付20英镑,那样就可以免服兵役,可是大多数殖民地居民付不起这么多钱。其结果是,乔治·华盛顿的军队中那些无法逃脱兵役的人越来越多——根据泰勒的描述,这是由一群“学徒、暂住者、乞丐、醉鬼、奴隶和契约移民”所组成的军队。随着军队中的穷人越来越多,大陆议会往往不能按时提供薪酬和用品。一名士兵抱怨说,像他这样的人“对未来没有什么期望,如果美国要维持其独立的地位,他们这样的人就必须成为富人的奴隶。”
西部边境发生的战斗尤为惨烈。印第安人与英国结盟,他们烧毁殖民者的定居点,而爱国者的军队则会摧毁掉印第安人的村庄。华盛顿在纽约上州亲自下令一名军事指挥官将那里的印第安人居住区“彻底毁灭”。泰勒认为,独立战争在前线“被激化”了:人们产生了一种白种人的民族主义情绪,所有印第安人,无论友敌,都被视为需要被铲除掉的敌人。
亚当斯所说的“傲慢无礼”的奴隶将有关自由的话语为自己的目的所用。 “对于那些反对自己的同类企图奴役他人者,我们认为这些高尚的人们将来会取得了不起的成就,”波士顿的一个黑奴群体于1773年带着嘲讽的口吻这样宣布道。可是,成为解放者的是英国人,而不是爱国者们。1775年,弗吉尼亚州的总督邓莫尔伯爵(the Earl of Dunmore)宣布,任何一个加入他的军队的奴隶都将获得自由。后来,英军指挥官宣布,任何一个属于爱国者的奴隶,只要能够逃离英国控制的地区都可以获得自由。(与此同时,英军协助保皇党保留他们对奴隶的控制权。)在北部的殖民地,有些奴隶为获得自由,加入了华盛顿的军队。但在南方,泰勒写道,“爱国者们一方面为维护奴隶制度而战,一方面也为白人的自由而战”——弗吉尼亚州的法律所做的规定能最好地说明这一点:白人参军者能够得到一百英亩的土地,外加一名奴隶。
泰勒称他的书为一部“大陆历史”,他时而会将他的注意点扩大到包括整个西半球其他地方所发生的事件。他指出,美国独立战争不是那段时期唯一一次为争取自由而爆发的起义。在秘鲁,一位名叫图帕克·阿马鲁(Tupac Amaru,这个名字来自一位印加国王)的耶稣会教士率领当地居民发动叛乱,试图把西班牙人逐出秘鲁。等到这场叛乱在1783年被镇压的时候,当地居民和西班牙人的死亡人数分别达到10万和1万人。当然,还有18世纪90年代发生的奴隶革命,这场革命确立了西半球第二个国家的独立地位,这个国家便是海地(美国直到1862年一直拒绝在外交上承认海地,这是美国对革命做出好坏区分的比较早的一个事例)。
泰勒这种对整个“美洲大陆”的全局性观察让他得以向人们展现奴隶制如何影响了美国独立战争的进程。他指出,在大英帝国位于西半球的全部殖民地中,最终形成美国的13个殖民地不到其中的一半。加勒比海地区的政治领袖和北美大陆殖民地领导人一样,都不喜欢英国议会对自己征税,但是,他们拒绝加入独立运动。这是因为奴隶人口在加勒比海地区占多数——西印度群岛上的白人只有5万,而奴隶的人数则达到275,000人,加勒比海地区的精英阶层迫切需要英国的保护。奴隶制也对英国的政策产生影响。法国于1778年加入战争,协助美国对抗英军,自那一刻起,英国政府所面临的最迫切问题便是防止自己在加勒比地区最富硕的殖民地落入其他国家之手。英国政府派到西印度群岛的援军比派到北美大陆的援军更多。1781年,驻守约克镇的英军投降,北美大陆的战事实际上已经终止;然而,西印度群岛的战事又持续了一年,直到乔治·罗德尼爵士(Sir George Rodney)指挥舰队打败了法国海军,战争才最终结束,英国对牙买加的统治才因此得以延续。总体而言,泰勒写道,如牙买加和巴巴多斯这样重要的蔗糖生产地对英国而言比反叛的北美殖民地要“重要许多”。
独立的实现并没有平息战争所引发的动荡。成千上万的保皇党人逃离美国,其中不乏知名律师、商人和英国圣公会的高级教士,他们的离开让那些雄心勃勃的新人获得了成为位高权重之人的机会(在南方各州,这意味着人们可以以非常低廉的价格买到属于那些已经流亡海外的保皇党人的土地和奴隶)。在边境地区,白人与印第安人之间的冲突仍然在不断发生。州政府的政治演变成了农民与债权人之间的竞争:前者请求法律中止对欠款的追讨,后者则在努力捍卫自己的财产权。上层阶级人士意识到各个州里的民主政治已经过格了,他们对此作出了自己的回应。《邦联条例》(the 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制定了最初的国家政府框架,联邦政府的权力远小于州权。在一群民族主义者看来,联邦政府的权力太小了,他们认为,只有一个更强大的中央政府才能控制住民众的激情以及有效地处理好与印第安人和欧洲列强的关系。
这时候,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出场了。在大众的记忆中,汉密尔顿总是被他伟大的对手杰弗逊抢尽风头,近来由于百老汇音乐剧《汉密尔顿》的上演,他才获得了人们的顶礼膜拜。在这部音乐剧中,汉密尔顿是一个贫穷但雄心勃勃的移民,他所获得的崇高地位正体现了美国给普通人所提供的向上流动的机会。泰勒笔下的汉密尔顿则是一个狡猾的奋斗者,他借由姻亲关系成了一个大家族的成员——这是北美殖民地最富有的家族之一,由此获得了地位的提升,他对革命所释放出的“民主精神”大加斥责。美国革命中的汉密尔顿一贯倡导富商和大地主的利益,而非心系人民。他在制宪会议上所做的一次长篇演讲里警告说,在公共政策问题上,“人民群众……很少做出正确的判断或者决定”,他主张仿照英国的君主制和上议院,设立终身制总统和参议院。代表们恭恭敬敬地听着,然后对他的建议不予理会。但是,这部宪法的确加强了联邦政府的权力,它禁止州政府干预对欠款的追讨,禁止其侵犯公民的财产权利。汉密尔顿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他在文章中提出了应该批准美利坚合众国宪法的种种理由,后来这些文章都收入了《联邦党人文集》;在调动民意对宪法的支持上,汉密尔顿发挥了关键作用。
汉密尔顿在西印度群岛长大,他对奴隶制没有好感。虽然他的岳父母都是大奴隶主,他依然在纽约州推动奴隶制的废除。然而,他在《联邦党人文集》里的文章没有提到宪法中对奴隶制进行保护的条款。在南卡罗来纳州和佐治亚州的坚持下,美国宪法允许各州在未来的至少二十多年里继续从非洲或西印度群岛往国内输入奴隶,其结果是又有20万名奴隶被带到了美国。宪法还给了蓄奴州更大的政治权力:它们可以将本州内奴隶的实际人口乘以五分之三算进总人口,以作为美国众议院议席分配的用途;同时还规定了逃奴遣返原则。琳达·科利(Linda Colley)最近指出,成文宪法常常会成为“实施控制的武器,而不只是给人们带来解放和权利的文件”。这个说法对于美国而言当然是成立的。
事实证明,这些共和国的缔造者们总体上不愿意去面对奴隶制存在于这个本应致力于自由事业的国家的事实。太多的历史学家宣称这些革命者们对人类权利的阐述让这个新国家走上了通往废除奴隶制的道路。开国者中的许多人希望奴隶制会消亡,希望革命思想对将来社会变革的领导者有借鉴作用,这当然是没错的。但是,从美国革命到《解放奴隶宣言》之间并不存在一个直接的目的论的线索。事实上,美国独立后,奴隶制急剧发展,直到美国内战以前的南部各州成为了闻名于现代世界的最大的奴隶社会。废除奴隶制度的是一场血腥的内战,而非自由的逻辑(许多国家缺乏在政治辞令中对自由和平等的承诺,然而它们却可以用不那么暴力的方式废除奴隶制),内战的结果是宪法得到修订,公民权利、公民身份与种族不再相关联。
泰勒在书的最后几章里简短地回顾了一番美利坚共和国早期的政治历史。虽然开国者们没有建立政党的打算,宪法里也没有对政党的存在做好准备,然而因为经济政策上的分歧以及对法国大革命做怎样的反应才是恰当的这个问题也存在不同意见,政党很快就出现了。到了18世纪90年代中期,华盛顿和汉密尔顿领导的联邦党和杰斐逊领导的民主共和党各自获得了自己的支持者。这两个政党都是走的下三路。联邦党人妖魔化移民,他们称移民会对新共和国构成威胁。1798年,他们推动国会通过《外侨和煽动叛乱法案》(Alien and Sedition Acts),该法案大大延长了外国人入籍需要在美国居住的时间;另外该法案授权总统可以将任何一个他认为会对美国“和平和安全”构成威胁的外国人驱逐出境。在1800年的竞选活动中,联邦党人将杰弗逊描述为一个危险的无神论者(而且还有个奴隶姘头),如果将他选为总统,则会鼓励人们“杀人、抢劫、强奸、通奸和乱伦”。在富有的弗吉尼亚种植园主的带领下,民主共和党人谴责他们的对手是精英主义者,他们强调自己对普通白人在政治平等和经济机会上所做出的承诺,与此同时激发起选民在黑人和印第安人面前的优越感。这一切熟悉到令人沮丧。
埃里克·方纳(Eric Foner)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德威特·克林顿历史学讲座教授, 当代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历史学家之一。其重要著作包括:《汤姆.潘恩与革命时期的美国》(1976)、《美国内战时代的政治与意识形态》(1980)、《除了自由一无所有:黑人解放及其遗产》(1983)、《重建:美利坚未完成的革命(1863-1877)》(1988,该书获得象征美国史学界最高荣誉的班克罗夫特奖和其他学术大奖)、《美国自由的故事》(1998)和《谁拥有历史:在变化的世界中重新思考过去》(2002)。
本文选自《伦敦书评》,东方历史评论受权译介
翻译:陶小路
来源时间:2016/10/21 发布时间:2016/10/21
旧文章ID:115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