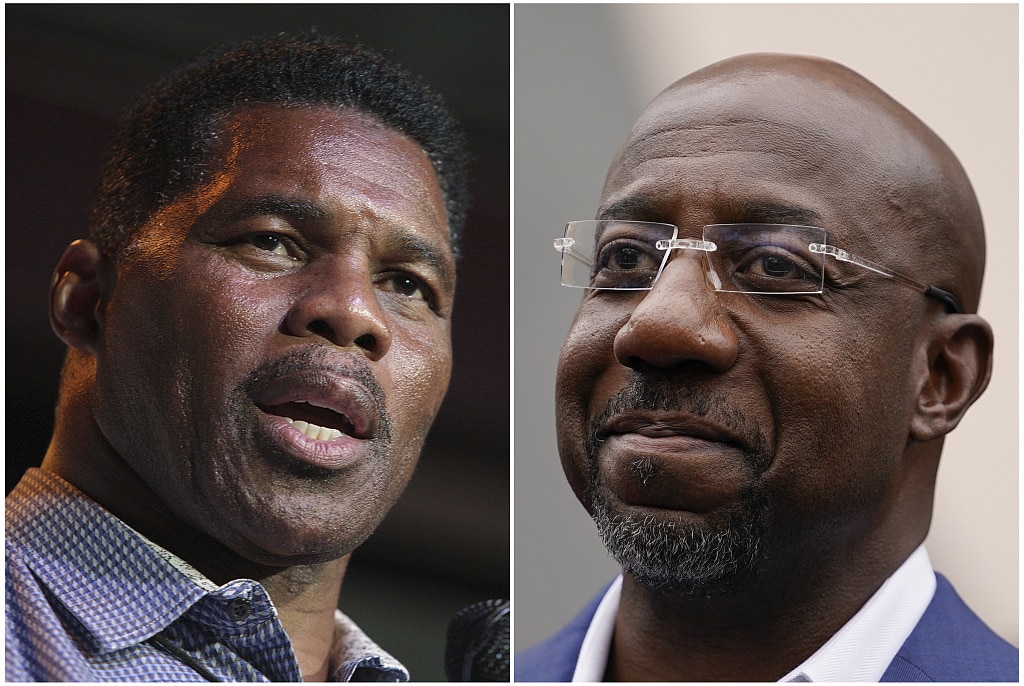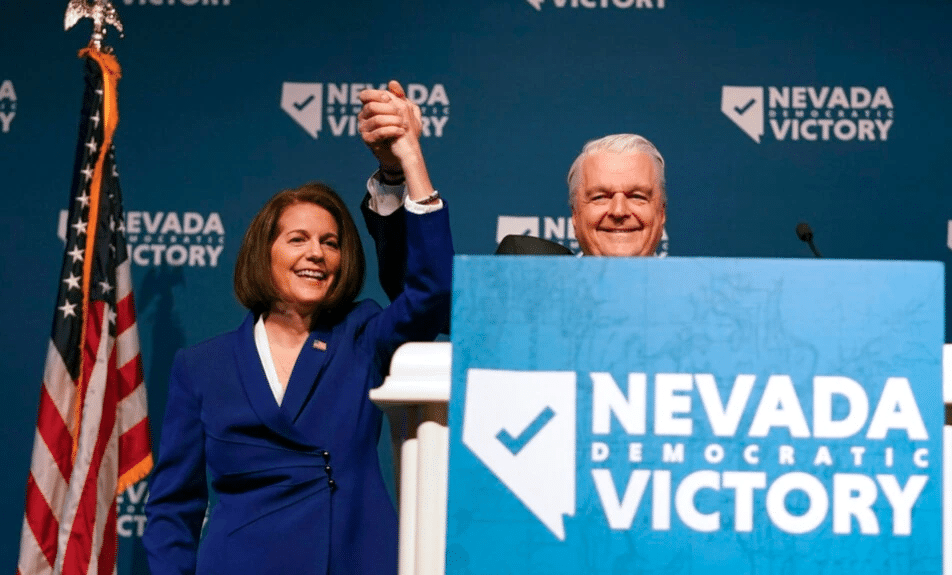她和白宫的距离 就是她和丈夫克林顿的距离
作者:王一鸣 来源:观察者网
(作者注:在本文中,比尔·克林顿将被简称为克林顿,而希拉里·克林顿则简称为希拉里)
上世纪最后几年,在克林顿深陷莱温斯基事件,对科索沃战争的界限最为摇摆不定的时候,国务卿马德琳·奥尔布赖特站到了最前面,几乎凭着一己之力扛住了五角大楼对于派遣部队的质疑和压力,并最终推翻了米洛舍维奇。
一段时间内,评论界喜欢把那称之为“马德琳的战争”,作为美国首位女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对于这个称谓十分敏感,她指责到,“你们会将越南战争称为麦克纳马拉(时任国防部长,对越战的推动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的战争,就应该将科索沃称为奥尔布赖特的战争,而不是马德琳,这是对女性的歧视”。
有点儿微妙。她的意思其实是,你们不用刻意强调“马德琳”这个女性名字来凸显这是一位女性完成的战争,没有必要说这些,收起你们的直男癌,在这场重大而深刻的政治和军事活动中,女性和男性没有什么不同。
彼时还是1999年。时间过去了近20年,这些年里,美国政坛接连出现了首位黑人国务卿、首位黑人总统、又一位女国务卿。而现在,甚至在稍稍偏多的人看来,美国很有可能出现历史上首位女性总统。
今时今日,多元价值在美国政坛拥有无与伦比的合法性,任何具有明显性别、种族、阶级概念的观点表达,都是极端的政治不正确。在首场辩论即将临近的时刻,甚至是危险至极的。近期,连特朗普都收敛了自身的直男属性,对待女性和少数族裔群体的态度明显转好。希拉里摔倒之后,也没有跟上去补刀她的健康问题。
谈及这些,是想要预先埋下伏笔。或许本篇的某些段落,直男逻辑会不得已显露出来,Feminist如果能够搁置对于这些文字的阅读不适,仅就其意欲揭示的道理进行理解,将是笔者极大的感激。
毕竟,我们没有饱含对任何一方的同情抑或仇恨,这些文字的出发点仅仅是希望把问题说明白,而它也仅仅代表一种新的分析问题的角度,即:
——如果,仅仅是如果,希拉里没有成功当选美国历史上首位女性总统,与其去对比她和特朗普差了些什么,不如去对比她和那位更为熟悉,并且已经成功当选总统的克林顿先生差了些什么。
某种程度上,她和她的丈夫之间的距离,就是她与椭圆形办公室之间的距离。
不同点——诚信与聪明
作为任何一名政治活动家,诚信这一概念,几乎是著身立命的全部依赖。然而作为一名极其出色的政治活动家,没有人比克林顿更敢于把这不当回事。
早在小石城当州长之时,当地居民就给这名年轻力盛的州长先生起了个外号叫作“狡猾威利”(Slick Willie)。一方面,选民们认为他做的不错,在阿肯色这样的小地方,他已经突显出了自己极其出色的经济治理能力,总是能够摆平各式各样的实际问题。然而他从不吐露自己的想法,永远难以接近,政敌们对其居高临下的嘲笑总是恨之入骨。另一方面,大家都知道这是个好色的州长,几乎注定会有很多风流韵事,只是他永远掩藏得很好。
克林顿的竞选之路遭遇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没有去越南”的问题,在那个人人都会操着“Nam”的简称以彰显自己对越南事务之熟悉的年份,克林顿竟然先是通过后备训练队的借口非法逃掉了兵役,而后又通过一封虚伪而热情的长信转而拒绝了后备训练队这个借口,从而没有承担任何艰辛的个人义务,在牛津大学舒爽的宿舍里休养筋骨。
当这些事情被他的对手们费尽心机揭发出来的时候,克林顿仅仅是通过一场脱口秀直播就将这一事件的诚信含义放松到了一个较为随意的标准,释义成一种年轻的调皮。对于那个年代的任何一个名竞选者而言,对于越南义务的背叛相当于对于整个国家的背叛,然而正如评论员马拉尼斯后来所说,克林顿“像一名象棋大师一样应对了兵役”。
这种能力恰恰是希拉里所不具备的。整个阶段的竞选,“邮件门”给她带来的折冲实在太大,尽管企图重走其丈夫的老路,把一切说成是所有人都会因偷懒而犯下冒失的错误。然而,时过境迁,克林顿夫妇不再是当初顽皮的少年映像,她看起来富于心计,参加了无数脱口秀节目,却始终无法摆脱这个阴影。
从“邮件门”的1.0,2.0再到3.0,这种损耗是不断绵延的,摇摆的选民和希拉里自己一样,永远不知道下一个版本会出现什么更为致命的信息,永远不知道一个人还可以复杂到怎样的程度,永远不知道自己距离美国政治的真相有多么遥远。诚信的底线不断被拉低,每一次新消息爆出来,就会有新的一拨选民转身离开。更为致命的是,这是一种灰心和沮丧的离开,几乎确定不会再恢复。
再去看她的丈夫。所有人都知道,克林顿极端聪明,聪明到可以充分利用选民对诚信的容忍边界,最大限度地争取个人利益。无论是兵役事件还是为其职业生涯带来重创的莱温斯基事件,每一次危机出现的时候,他都极有胆量地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坚定地矢口否认,等到确凿的证据被披露后,再转而以克林顿式的方式搪塞一切,淡化这一问题的处理。
很多评论界人士都会提到,在那样的丑闻下,如果被自己亲口否认的事实狠狠地扇了一记耳光,换成任何一位总统,几乎注定会如同尼克松一样遭遇弹劾。而克林顿就是能够做到鸡贼般地苟活下来。
不仅活了下来,在莱温斯基事件被坐实后不久的中期选举中,民主党丝毫没有受到影响,甚至反而赢得了更多的席位。人们惊讶地发现,克林顿已经和选民们达成了一种浮士德式的交易——人们会为他投票,但是已经学会了放弃对他的信任,人们只是觉得国家有一个足够善于总统事务的聪明人是可以的,至于他做的那些不甚重要的承诺,大可置之不理了。
克林顿成功地戏谑了诚信,成功地教化了选民。聪明可以代替诚信,成功的经济繁荣可以代替失败的个人道德,美国人民和他之间淡淡的关系就是一纸契约,选民对他的精明不亚于他对选民的精明。
然而这一切必须建立在聪明和诚信同时出现的前提下,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希拉里的智商高于克林顿,她不过是一名毕业于威尔斯利学院和耶鲁法学院的杰出律师,但在控制选民、深谙世故这方面的本领,希拉里远逊于她精明的丈夫。甚至莱温斯基事件的出现,表明她其实是这种精明最大的受害者。
然而现在,如同被他的丈夫传染,无论是“邮件门”还是“健康门”,她总是在事情爆发的第一时间负隅否认,又在稍晚的时候面对被揭穿的窘境。然而她不具备回天的本领,在这场愈演愈烈的针对个人诚信问题的声讨中极为被动,甚至有可能因之失去一切。
如果拥有诚信,希拉里可能如同往年任何一位朴实的候选人一样以年迈而慈祥的姿态步入白宫;如果拥有聪明,希拉里可以同其丈夫一样把选民的忠诚玩弄于掌心,不过是另签了一份浮士德式的契约;如果不够聪明,又失去了诚信,事情或许就如现在这般窘迫,她的确位于天平的低处,但是一切已经在缓缓向对方倾斜。
不同点——能量与健康
这一点希拉里被欺负惨了。特朗普几乎是以赤裸裸的性别优势在践踏希拉里的个体尊严,这种践踏他在竞选初期可以用在杰布·布什身上,如果一个政治家族的代表深负众望、文不禁风,看起来蔫蔫的,再怎么讽刺都不为过。
但是希拉里是一位女性,而且是一位上了年纪的女性。这位女性二十五年前在与她的丈夫在新罕布什尔州首次亮相的时候是惊为天人的,没有人在竞选初期就能让自己身边的女人有南希般的第一夫人之感。这位女性后来在参议院的工作是年富力胜的,在国务卿的任上是极为勤勉的,或许因为过于勤勉,导致其非常疲倦,在退休之后许久都不肯表态是否竞选总统。
现在有评论提到了,她是在评估自己的身体。2012年卸任之时,希拉里的核心忧虑一定是——如果有四年的休息缓冲,是否还能够换回两个健康而完整的总统任期。
按照年龄来看,68岁并不算小,尽管美国政坛如里根、哈里曼这样在古稀之年迎来自己政治巅峰的大有人在,然而希拉里是第一位女性尝试者,她的竞选年龄在历届总统中排名第三。而按照一种直男式的解读,女性在这样的年纪,真心很柔弱。
二十五年前,当克林顿以46岁的年龄参选时,他是何等的“Energetic”(特朗普经常形容希拉里Not Energetic)。在一次政府预算被国会驳回的尴尬中,克林顿找到了国会里更为年轻气盛的右翼代表纽特·金里奇,接下来的这场对话让这位一向不把克林顿放在眼里的年轻人毕生难忘——
“你知道我是谁吗?”“不知道。”“我是你小时候玩的那个大橡皮小丑,每次你一打它,它就会弹回来。”克林顿停顿了一会儿,又接着说,“这就是我,你打得我越狠,我弹回来得就越快!”
这真的是只有在年轻人的嘴里,才能够听到的话!在特朗普看来,或许一个总统就该有这样的气魄!
克林顿的第一个任期,整个国家的对外事务糟透了,特别是还出现了索马里危机这样的让美国政府名誉扫地的事件,克林顿感受到了极大的压力。不久的海地危机中,美国强大的军队被香蕉共和国雇来的一群乌合之众所赶跑,克林顿政府再次颜面尽失。
在一次对俄罗斯的访问中,美俄双方的安全官员都获得了可能会有暗杀活动的情报,然而克林顿坚持要完成访问,他的理由是,“我绝不会像在海地一样怯懦地离开。”
随后不久,海地问题也得到了解决,克林顿终于在自己的对外事务上扳回一局。他的助手们发现,克林顿在面对那些最为严厉的攻击时,其反应着实令人叹服,在历经个人的灾难之后,克林顿会变得更加投入,竭尽全力向自己的目标靠近,在威胁面前近乎残酷、无情、疯狂。他们认为,这是克林顿最大的政治优势。
而这一点,加注在25年后的妻子身上,实在是有些过重了,希拉里不可能再拥有这种负荷的能量储备。即便没有这次的摔倒事件,媒体也早就发现,希拉里难以在巡游演讲中保持状态的连贯性,如果中间没有经过适当的休息,嗓子会哑得很明显,咳嗽会显著增多。
最为可悲的是,在特朗普的挑衅下,希拉里被迫采取了一种男性方式的竞选风格。在希拉里的演讲中,我们常常能够感觉到她吊着嗓子站在男性的声带高度发出标准的美式演说的声音,那些必须要一浪高过一浪的连续的排比句对她来说难度太大,很多场竞选视频里,都可以看到她十分吃力,在激昂处常常出现破音。
单从演讲的角度讲,她大可不必如此,特里莎·梅的议会质询中,她从来都是按照自己的声音和字频习惯快速地完成演说。然而美国大选毕竟不同于英国议会质询,它需要一种宏大的演说意识和雄厚的感召力,这都是需要极为充沛的体能储备的。
据说,在竞选初期,希拉里的团队给她的人设其实是睿智祖母的形象,然而在特朗普的咄咄逼人下,这位祖母的气力被严重地消耗掉了。
事情永远是这样戏谑,她经过了极其审慎的深思熟虑,走出了参选的这一步,却遭遇了生理意义上可能出现的最大挑战。当一个满负阳气的男人站在你面前微微抬起下巴,一个女性所意欲保持的刚愎节制是那样的脆弱,出手抵抗又是那样的不堪一击。
相同点——精英欲望与个体自卑
那种认为美国近三十年的政坛将连续为布什家族和克林顿家族交替统治的说法是极其失当的,布什家族由于部分地继承了里根总统的精英团队和“康乾盛世”,可以勉强算作存在一种家族式的影响力。
然而克林顿夫妇没有家族。这个家庭成立之时,两个人几近身无分文,甚至没有自己的住房,直到后来希拉里参加参议院竞选时,才不得不根据参选要求在纽约购买了属于自己的居所,而这笔费用还需要依赖筹资人的资助。
这个家庭成立以后,他们也不过只有一个孩子。去看看布什、罗姆尼那样的一张相框很难装下的大家庭的合影,你就会知道克林顿夫妇是何等的逆袭,能够走到今天又是有多么不易。
他们所仰赖的是一种源自骨子里的精英意识。这种意识的血脉从肯尼迪兄弟、邦迪兄弟到克林顿夫妇,是民主党区分于共和党的重要品质之一。
同所有政坛年轻的出类拔萃之辈一样,克林顿是罗德奖学金的获得者,在美国,这个奖学金可以定论终身,完美地解释一个优秀的人的一切。而希拉里在高中时进入了美国优秀学生奖学金竞赛的决赛,是第一个在威尔斯利学院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讲的学生,并且在工作后两次当选全美百名杰出律师。
克林顿是天生的政治家,对自己的能力充满自信,从不怀疑。在民主党蛰伏的多年间,他一直在估价他的潜在对手的实力,并且一再得出结论,尽管没有足够的金钱和资历,然而自己的政治技能和才华要显著强于他们。
1991年的夏秋,老布什身携冷战和海湾战争胜利的巨大光芒,支持率一度高至90%。民主党内所有稍有名头的竞选者全部退却了。只有克林顿敏感的捕捉到,长期的冷战对峙严重压抑了美国经济的生长力,美国民众已经对战后的新图景出现了巨大的期盼,而布什总统对于国内事务过于忽视,这将有可能让他付出丘吉尔式的代价。(二战期间丘吉尔挽救了整个英国,却在战争尚未结束时被选举下台,由被视为更善于经济治理的艾德礼取代首相,该事件被誉为选举政治中的“丘吉尔现象”。)
最终,他使这一切成为事实。
她的妻子同样热衷政治。她本可以简单地选择成为学历最高、最有魅力的第一夫人。如果那样,她注定会比南希更知道如何做一只美丽的花瓶。然而她选择了在克林顿入主白宫后辅助政事,并牵头负责了国家医保改革和儿童健康保险项目。
在克林顿即将结束他的总统任期时,她已经马不停蹄地开始了自己的参议员竞选。在纽约州担任州长期间,她赢得了东北部民主党核心阵营的认可和支持,而在美国白人女性眼里,她早已成为一面具有极其深刻标榜含义的旗帜。
他们的精英意识贯穿整个政治生活的始终。即便在克林顿卸任以后,人们发现他仍然通过四处的演讲、顾问、非正式外交渠道、自己的基金会和筹备希拉里的竞选班子深刻地影响着民主党的政治风向。
直到这个基金会的很多做法被逐渐揭露,人们才意识到过往二十年,是克林顿夫妇在民主党内枝繁叶茂的二十年。克林顿评价奥巴马的那句“他以前只配给我端咖啡”绝对不会是随口说说。
这种精英意识是好的。自肯尼迪政府以来,已经很久没有在总统的位置上出现才华横溢的年轻人的身影,我们有理由相信克林顿和希拉里也能够如肯尼迪一般,为国务院带来一群出类拔萃之辈。
然而,他们又是自卑的。
上帝赋予了他们过人的才智,却没有赋予其在事业起步时足够的社会地位和财富。他们不得不通过自己的努力争取周围人对他的认可。越是在其十分虚弱、毫无靠山的时候,维系于其内心的生存欲望就越强大,而这将必然给他们施政纲领的独立性带来极大的代价。
特朗普是聪明的,他比克林顿夫妇更为富裕,并依仗自己的富裕打压希拉里,意欲离析出美国的阶级分野和仇恨。他感知到了民众对于政治经济联姻现象的深刻憎恶,便打着对抗金钱政治的旗号脱引而出。然而希拉里从本质上就没有钱,她无法脱离克林顿强有力的募资班子,也无法不向东北部和西海岸的金融、科技势力作出承诺。
这样的事情本是美国选举政治的常态,十几年前在克林顿那里甚至更为直接。克林顿首个任期的外交政策是布什总统的旧部在运作,经济政策是各大财团代言人团队的共同成果。在一次有关预算问题的关键辩论中,他几乎是完完全全按照格林斯潘的意思作出了缩减财政赤字的决定,他的一个朋友曾经说,克林顿的身体里没有一根骨头,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生存。
这种个体自卑也将直接作用于他们对团队的态度,他们并不会像肯尼迪相信邦迪和麦克纳马拉那样相信别人。在克林顿的幕僚中,他对所有可能威胁到其当下和未来统治地位的人物都充满防范。
其总统任内,国防部长换了三届,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换了两届,最为重要的国务卿之职或是给了克里斯多弗这样的和事佬,或者是给了奥尔布赖特这样的话题女性,而刚刚赢得海湾战争身孚名望的鲍威尔将军和公认的极为聪明出色的国务家霍尔布鲁克始终无法进入其核心班底。按照某篇评论中的一句话,“克林顿政府的班子更像是一群从学院逃跑的难民,所有位置都遭到了不合适的安排”。
同样的现象再次出现在希拉里身上。在副总统候选人的提名中,希拉里没有选择曾担任欧洲盟军最高总司令的海军上将詹姆斯·斯塔夫里迪斯将军,也没有能够说服党内仅次于桑德斯的进步派伊丽莎白·沃伦,而是又一次从国会山搬来一位约翰逊式的老参议员蒂姆·凯恩。
按照克林顿夫妇的习惯,自己必须要成为总统团队中的最大话题,能够压住自己声音的力量必须越少越好。这种自卑使得总统与身边所有人都保持着淡淡的距离,克林顿的首任国防部长阿斯平曾向人抱怨,总统的很多想法都是从电视上或是报纸上听到的,整个波斯尼亚危机期间他仅见过克林顿三面。
相同点——缺乏外交事务的应有重视与职业敏感
人人都知道,克林顿长于国内经济事务。在他的首个任内,道·琼斯指数和纳斯达克指数几乎翻了一番,失业率由8%下降到5.5%,高科技产业蓬勃发展,商业活动的方式出现了革命性的变化,百万和亿万富翁不断增多。某种意义上,是克林顿养育了他们,在这对夫妇看来,现在他们做出一些反哺或许真的毫不为过。
经济上的巨大成功冲昏了克林顿,也成功分散了国民注意力。几年过后,当人们开始随着保守派转头咒骂民主党延误了重要的发展契机的时候,他们惊讶地发现,这几年,总统在对外事务上的成就少得可怜。
克林顿先天性地缺乏对外事务的基本敏感。一如其为人,整个任期没有与任何主要大国建立起信任与真诚,却囿于道德压力戚戚于索马里、波斯尼亚、海地、科索沃等地的区域性人道主义危机,并一次次给自己带来巨大的外交灾难。
长期的冷战使得美国的国务家和民众对世界矛盾的认知单一化了,气候已经松快,人们的意识却仍然板结。克林顿顺应着选民懵懂的对于和平建设和经济复兴的渴望获得了任命,接下来却不知该往哪儿走。
对于美国而言,冷战结束以后的头号任务应该是如何在对手消退的情况下重新定位自身的国际角色。如果说整个九十年代只剩下一个国家命题,那么这个命题应该是“美国权力的界限”,而绝非国内的经济发展。
很长一段时间,克林顿搞不清自己对于苏联留下的权力真空应有的态度,保持距离似乎有违胜利者的英明和道德义务,过分干预则又会不由自主地回想起上世纪中叶在中南半岛的噩梦,越南战争给民主党留下太过严重的阴影和分裂,直接挫败了半个世纪以来的政党信念和合法性。
在最为重要的十年里,民主党人由于缺少国务运筹的宏观战略,踉踉跄跄地勉力完成了几次维和任务的考验,却使得美国对战后国际角色的定位这一重要的历史使命被严重拖延,直至共和党上台后并形成报复性反弹的保守势力。
普利策奖获得者,著名记者戴维·哈尔伯斯坦观察到,“那些对自己的信仰怀有坚定立场,带着满腔政治进入国会的年轻保守党人士是如此痛恨他和他的妻子,以至于超越了意识形态,成为强烈的个人攻击”。
回到此刻,美国再次处于转折的关键节点,新世纪的第三个十年永远是蕴藏着危险的,希拉里站在门口,再次懵圈。
某种意义上讲,她在任国务卿期间和奥巴马共同采取的对亚洲和中东地区的压制策略颇有共和党的新保守主义遗风。然而伴随中东地区的僭主一个个倒下,留下了马蜂窝般的权力烂坑,无人收尾、无法捡拾。
而在亚洲,剧变正在发生。奥巴马苦心孤诣的TPP遭到了所有总统候选人的集体弹劾,对南海的意志力又严重不足,对介入存在极大的恐惧。甚至,连菲律宾这样的哨岗也开始反叛,其引发的连带效应将极大地动摇美国太平洋权势的可信性,其深远影响不可估量。
某种意义上,特朗普比希拉里更能理解时代风貌,特朗普的孤立主义是基于对于选民的心理判断,在他看来,美国已经发展到了这样一个时代节点,虚无主义的文化认知将僭越多年来不必要的全球责任承载,形成更为主流的价值判断。
希拉里则没有那么复杂,她几乎是本能的偏重于国内议题,这多半出于一种源自其丈夫的旧时习惯,她的团队长于经济,自然只愿谈及国内事务;剩下一半,则源自特朗普“希拉里是最差的国务卿”的高压指责,很多对外事务希拉里确实无法说清楚,而其中有一些,她注定要承担责任。
这个节点的美国的确颇有风雨。如果特朗普当选,无论是战后几代人垒筑的国际秩序还是美国的对外政策,都可能陷入一场无序;而如果希拉里当选,或许陷入的不是无序,而是更为明确的衰退。
“自由世界”在守望“灯塔国”的国际角色定位,然而大家也都能够淡淡地感到,无论怎样,一种熟悉的美国治下的国际制度将成为旧迹,长达二十年左右的一号警察的角色,美国是无论如何不会再当了。
命途
以下的文字大概只能算作泛泛而谈。
克林顿夫妇或许还在一重意义上拥有共同点——所谓“不是一家人、不入一家门”——他们看起来分享着几近相同的命运。
代顿协议签订后,克林顿已经成功应对了波斯尼亚危机,肯尼迪敢于以毕生的勇气用古巴导弹危机挽回自己在猪湾事件中的政治损失,克林顿也做到了。索马里和海地曾经让他遭遇了几近灾难性的开局,甚至对卢旺达的恐怖不敢介入、视而不见,但是海地和巴尔干局势最终还是被他扳回来了。在第一个任期结束的时候,如果不言及战略层面的东西,他在对外事务上的评分是合格的,这使得他轻松获得了连任。
然而莱温斯基事件毁了这一切,轻松消耗掉了他在首个任期垒筑的全部合法性,没有能够如其它曾经连任的总统一样完成第一任期中由于缺乏政治力量和紧迫的经济问题而被推后的事项。
全部总统班子的注意力被用来应付镁光灯,克林顿本人则对于出头露面的场合更加挑剔,共和党在长达三年的时间内疯狂地攻击他破坏了总统这一职位的神圣地位,剥夺了克林顿进行政治变革所主要依赖的道德权威。
克林顿热衷于历史学,在任的最后时间,他全力以赴,希望能够以历史的名义得以为人们所记住,然而他的第二个任期只能在混沌与躲闪中度过。某次晚宴,他的身旁坐的刚好是美国历史家协会的成员多丽丝·古德温,这个协会刚刚完成一份对美国历届总统的评价排名报告,很遗憾,克林顿只是普通地位于中间。这一晚的大部分时间,他放弃了应该处理的很多社交事务,不断地表达自己对得到普通排名的不满,为抬高自己的名次持续进行游说。
凡事善始易获,善终很难。
希拉里现在最明白这个道理。她或许永远没有想到,这条竞选之路充满着如此多的非传统性议题的挑战,甚至是自己的健康。还有50多天的高强度工作,甚至第一场辩论即将举行。即便是肺炎,即便是身强力健的成年人,也要静养半月才能恢复,68岁的希拉里确诊6天后便重新回到人们的视线里,她知道,留给她的时间没有多少个6天了。
希拉里现在用完了自己最后一张底牌,未来数日,在辩论场上、在电视机前、在巡游拉票活动中,如果再次出现跌倒、喷嚏或者咳嗽,政治后果是致命的。人们会确信自己曾经怀疑的一切,毫不留情地疯狂散去。如果能够熬过这50天,或许,她能够重生。
这场大选的核心风貌已经改变。人们会记住它,不仅仅因为它肥皂剧般的剧情,更因为它深刻动摇了美式民主的基石。这座屹立于山颠之城的经久信仰,为特朗普和桑德斯的阶级离间所质疑,在疑似俄罗斯的插手中被嘲笑,带给了东西方大洋彼岸国家持续的不安。
选民们开始质疑从前大选中看过的那些家好月圆、和谐对抗的剧本,转而思考自己在选举中的角色和含义是什么。从来没有一届选举,两派都在呼吁选民们深刻反思自己的肩头使命,每一名选民都被一根根手指点着鼻子,特朗普们在问“你的阶级立场是什么!”希拉里们在问“你要不要拯救美国和这个世界!”
老布什会为希拉里投票,桑德斯的死士会为特朗普投票,阶级区分首次挑战到了党派意识,而希拉里是这一切变化的首位受害者。如果没有特朗普掀起这一切,这本应是一场不能更为轻松的大选。没有人知道,到底为什么会发生这一切;也没有人知道,新世纪的第三个十年,究竟在酝酿着什么。
对于克林顿夫妇而言,这是命途。
尾声
不久前结束的民主党代表大会上,克林顿深情讲述了他和希拉里的恋爱故事,那是他的开场白。故事不到三分钟,但剧情很丰富,画面很美好,一直以来人们喜爱克林顿的演讲,一直以来人们也会质疑他们夫妇的感情究竟有多少。如果某日,可以抛去一切浮华,这对夫妇或许本可以生活得很好。
希拉里后来常常会谈及从前的一段生活。在克林顿刚刚当选总统时最为晦暗的时刻,他和他的妻子正在经历远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的政治生活和国家事务的许多挫败。那段时间,据说总统和第一夫人经常是这样开始一天的,他们一起吃早饭,其间希拉里会挑选《时代》或者《华盛顿邮报》的一篇报道或者专栏,跟他分析里面所有的对待他们的不公平。她敦促总统最好忽略这些事情,集中精力处理国内事务。
她说,这或许是他们最为美好的岁月。
来源时间:2016/9/26 发布时间:2016/9/26
旧文章ID:113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