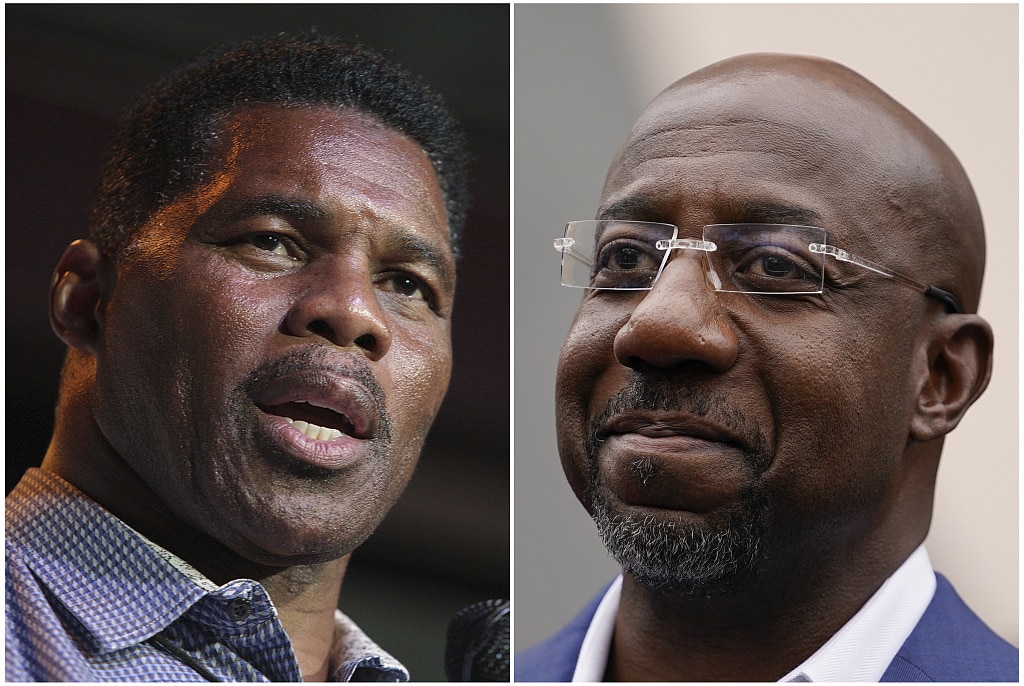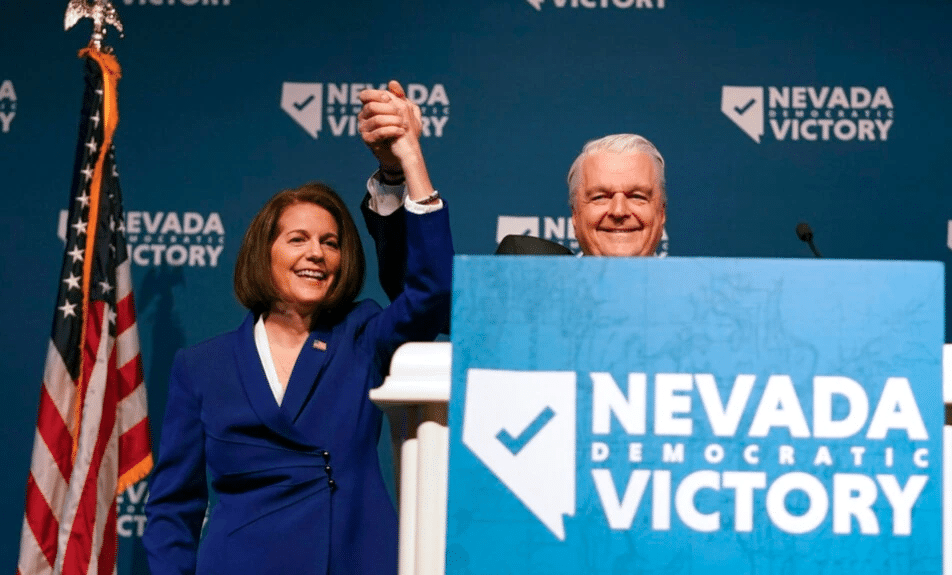美国大选揭示的专制魔影和意识形态之争
作者:周雷 来源:共识网
作者系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师
通过观看美国大选的视频资料和媒体资讯来理解美国政治,讨论它与全球政治的关联——我同意,这本身就是“构造式民主”(fabricated democracy)问题的一部分。
但是囿于眼界和渠道,以及没有国家重大课题资助不能飞往美国,也只能通过这种简陋方式来“坐华观美斗”了。
需要提醒看官的是,美国现任即将“退休”的总统奥巴马在当上美国总统时,有政治修辞分析家说,那是一次现代社会的“西塞罗和昆体良式”政治修辞家复活,奥巴马除了得到一个名不副实的诺贝尔和平奖之外,还在当选不久被美国广告行业颁发了一个最佳营销奖。
也就是说,美国的政治是高度修辞化的表演型政治,或许是这个原因,美国的演员和政客时常殊途同归(我难以想像中国的百花奖和金鸡奖获得者可以成为省长和国家主席):里根和施瓦辛格可以从演员做到高级政客,奥巴马在多个脱口秀中的表现,也证实了他其实可以成为全美最优秀的主持人——如果他愿意。
从社交媒体和传统媒体的门户网站来看,美国人也很苦恼,他们现在只能在两个最劣选择中,选择一个次劣的人当总统,然而麻烦并非如此,美国的政治模式不仅与美国有关,它是有真正全球性影响的国家和政治体。在这个意义上,美国的困境可能成为全球困境的一部分。
2016年7月22日,美国纽约时报的言论版刊登了斐萨-默罕默德(Feisal G. Mohamed)的一篇文章,他提到了我认为较为重要的美国竞选深层困境——美国正在“阿伦特式的专制”和“施密特式专制”之间摇摆,摆向任何一方,都意味着麻烦甚至灾难。
斐萨的讨论主要基于两位候选人的资格获得演讲(acceptance speech)和部分早期选战的政治叙述分析——我也通过自费购买VPN翻墙去Youtube观看了资格演讲的全程录影。
施密特是一个因为和纳粹发生勾连且拒绝反省,因此是有道德污点的学者,但是这不妨碍他的研究比任何又红又专的学者深刻。
1927年,他说了有名的话:政治的概念其实就是敌我之分,政治行动和政治动机之间的区别其实可以减除(我理解的白话就是:怎么说怎么做不重要,分清敌我最重要)。施密特的这种政治观剥除了自由政治世界的法律(合法性)和程序问题,转为无休止的政治团体“选向填写”和“选边站”过程。
公允而论,特朗普在他的候选人资格演讲(convention speech)中的话语表现,完全进入一个粗俗、粗野、粗陋的煽动型演讲模式(demagogue),他的面部表情狰狞,他的声调高亢而无聊(drone and boring);希拉里则如她一直以来的政治修辞机器的模式进行“声音生产”,她是熟谙美国政治选举机器的高清晰度政治演讲生成器。
斐萨提到,特朗普的政纲是把美国带回到一个安全社会,这个安全社会的敌人是没有记录的工人(我对美国很无知,不知道它有没有户口、暂住证和通行证制度)和伊斯兰恐怖分子——这就是施密特的建构敌人以定义自我的标志型桥段。在我看来,特朗普像是玩地雷游戏,把每个敌人都找出来标签化,插上旗子,他的上任意味着履约“排雷”(这好像是和低年龄的少儿一起看电影,他们往往对什么也不感兴趣,只是不停地问,它是好人还是坏人?)。进一步明指,特朗普的美国身份和内部团结自我建构,是通过“囤积”仇恨和标记敌人的方法获得。
而阿伦特式的专制概念,则是由希拉里的团队演绎的。斐萨认为,阿伦特认为专制的起源与民族国家有关,只有把民族国家(nation-state)这个连字符去除,通往专制之路便成为通途了。因为民族变成一个排他性的集体,它可以通过法外方式对其自身的权益进行彻底捍卫,哪怕这已经超越了国家机构和程序正义的赋权和边界。一旦这种明显和现实的危险被建构,同时民族处于危机时刻,继而兴起的是各种国家权力的越界和滥用。希拉里多次提到,叙利亚的难民已经越来越多地聚集于美国。
而阿伦特就曾经特别批评了二战期间,欧洲和北美国家拒绝为当时的二战难民提供栖身之所。阿伦特认为,在许多西方社会,正义和平等已经被意义抽空,变成强力政府或政府权力的工具。
在坚固美国安保城墙和防止极端外族势力的特朗普主义面前,希拉里嘲笑竞选对手的部落政治(tribal politics)观念,尽管她也惯于操纵恐惧,并通过建构特朗普为魔鬼(monstrosity)来获得政治红利——特朗普如果败选,不知道能否评他的竞选口碑谋一个本土安全部部长的工作做做?
在这个意义上,美国国内和国际看客不应该用“一丘之貉”简单化美国选举之争,而是要仔细辨认竞选者的“动物学”分类,并深入洞察美国社会的转型和未来去向,并察人观己。
在美国政治的深刻揭示上,语言学家乔姆斯基是不可忽视的另一种阐释力,他通常被定义为新左派,持有平权、民主、正义的民间和底层立场,他反对银行家政治、寡头政治,批判政客对恐惧的利用,对民间团结力量的消解,最终他认为朝不保夕无产阶级成为彼此孤立,自相残杀的无助个体。
乔姆斯基认为,财富的集中导致权力的集中,集中的政治权力开始寻求体制来合法化自己的政治治理和利益,同时通过商业、消费、教育的控制来生产一种建构化的消费者(fabricated consumers),无产阶级和底层社会的人长期生活在一种朝不保夕和人心惟危的动荡之中(precarious proletariats),在分化、洗脑、注意力转移之后,他们只能像看美国大碗杯、美国偶像选秀、演唱会和成功学演讲一样,在他们之前的有限政治选项的表演中,投出自己的选票。
美国的政治,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它的魅力是情感(美国政客话不离口的是孩子、母亲、家庭、祖国、未来、变革、伟大等词汇),它的毒素也是情感——更准确的表达是:对情感的控制和操纵(the intimacy of totalitarianism),最终造成一个人情化的腐败民主机制,以及一个美言不信的修辞型政治。
美国选举政治让我想起来本人儿时曾经生活过的工厂,当工厂面临现代企业制度改革而破产时,我用《铁皮鼓》中奥斯卡式的眼睛看到的是,父辈们并不是励精图治,而是每天琢磨如何从管理日渐松懈的工厂里搬用值钱的物品进入个人的小家庭。在工人的眼睛里,工厂的管理者即使把厂子弄破产他们还可以盈利,并完事后去本系统的其他工厂继续当官,并且级别不降。就像美国的希拉里从克林顿的助选者,变成竞选者,落选后再变成国务卿,再变成竞选者。
热闹的是“他们”,“我们”什么也没有。
来源时间:2016/8/6 发布时间:2016/8/5
旧文章ID:10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