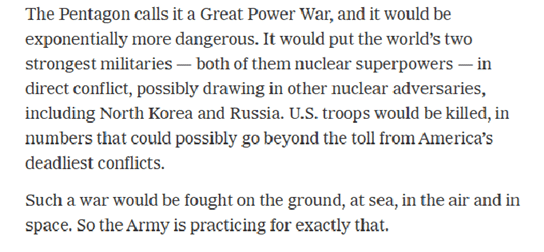精英与双轨制——漫谈美国联邦司法管辖权
作者:黄陀 来源:知乎选美
本文作者黄陀,耶鲁大学法学博士。
最近对于司法系统改革的提议和传言纷至沓来,双轨制也首次成为可能。从宏观层面上讲,一个大国的法院系统,必然要产生分化。一部分朝着更精英化的方向发展,这部分需要的并不仅仅是熟知条文和逻辑、熟悉技术细节的技术人才,而是需要对治国方略有着敏锐嗅觉、对国家政治有着高度责任心的智者。而另一部分则更紧密地与人民的日常生活结合,这里则更需要对技术细节的准确把握、对本地民情民风的洞察。
实现这种分化,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上下级法院的区分,另一种则是法院系统之间的区分。在一个比较小的范围内,前一种区分也许就已经足够。比如德国虽为联邦制国家,但并没有出现美国一样的双轨制法院系统,只是一定级别以下的法院由各州负责(但即便如此也是由州来负责,地市也是无法干预法院的)。而在更大的国家如美国和加拿大,则需要联邦和州两套法院系统来支撑。
一、精英化的联邦法院
在美国,州法体系负责的案件主要是与人民生活关系更为密切的案件,如离婚、争产、普通债务纠纷、滑倒跌伤、医疗事故以及一般性的杀人放火偷抢扒拿等等。这些案件应用的主要是州法律,影响也是非常本地化的。
而联邦法院则是一个更为精英化的群体。作为对比,全美大约有一万一千名各级州法官(包括具有全权管辖权的全权法官和上诉法官,不包括有限管辖权的次要法院如交通法庭等),但联邦法官只有不到一千人。全美各州全权管辖权的初审法院每年要处理近四千万个案件(如果算上次要法院的案件如交通罚单等,则超过一亿件),而全美联邦初审法院则只有四十万件。联邦法院是有限管辖权的法院(courts of limited jurisdiction),只有联邦宪法和联邦法律明确授予管辖权的案件才有管辖权;而州则有全权管辖权的法院(courts of general jurisdiction),除非联邦宪法、法律明确排除其管辖权,否则自动具有管辖权。
也许是受到了亚历山大·毕克尔的影响,谈到美国宪法,人们想到的更多是诸如布朗案或者马伯里诉麦迪逊之类的知名大案;而谈到司法审查、分权制约,人们想到的更多是联邦最高法院。但实际上美国并不是只有联邦最高法院才能进行司法审查,也并不是惊天动地的大案才涉及到联邦宪法。每年联邦最高法院要收到七八千份请求审查的调卷令声请(Petition for certiorari),但真正决定审查、作出详细判决的只有不到一百个案子。绝大多数案件,包括绝大多数的司法审查、宪法审查,都在下级联邦法院完结。所以,联邦法院必须作为一个体系来看待,这个体系在实际中发挥更广泛作用的,并不仅是最高法院的禅堂九老,而有着几百名下级联邦法院的法官的精英联邦法院体系。
联邦法院的存在自于宪法第三条关于联邦法院的设置,权力来源于宪法第三条的联邦法官,也常被称为“(宪法)第三条法官”(Article III judges),不但包括最高法院的大法官,而且包括联邦地区法院和联邦上诉法院(联邦巡回法院)的法官。这些联邦法官由总统经参议院批准后任命(初审法院也就是联邦地区法院的法官,一般由所在州的联邦参议员推荐),联邦法官为终身职、国会不得削减其薪水,若要免去其职务则需经国会弹劾程序。因此,这些“第三条法官”从被任命开始就受到宪法和最高政治权威的直接保护、有着不同寻常的地位和独立性,他们所组成的“第三条法院”(Article III courts)也是法律精英所向往的荣耀席位。
联邦第三条法院系统的精英地位,在1982年的北方管道案(Northern Pipeline Construction Company v. Marathon Pipe Line Company, 458 U.S. 50 (1982))背后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该案中,布伦南大法官的相对多数意见认为,国会在《1978年破产法》中设立不受宪法第三条保护的破产法庭,侵犯了第三条法庭的管辖权,因此的相关条款被宣布违宪。后来国会重新修改该法、加强第三条法庭对破产法庭的审查权才得以过关。这背后的理由是,如果国会能够随意设置不受宪法第三条保护、因而独立性较弱的“非第三条法院”,随意赋予其管辖权,那么原本属于“第三条法院”的案件被这些独立性更弱的“非第三条法院”夺走,司法独立就会受到侵蚀。
而国会之所以没有把这些破产法庭全部升格成第三条法院(或者说是扩张第三条法院的队伍),也有出于保护第三条法院精英地位的考虑:人太多了,也就谈不上精英了。
二、有所为有所不为的联邦管辖权
所谓有所为有所不为,联邦法院地位的保持,与法院在管辖权上的自律有着很大关系,概括地说,就是不该管的事情不管,该管的事情谨慎地管。经过两百多年,联邦法律管辖权已经发展出一整套如迷宫般复杂的规则,成为美国宪法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概括地讲,美国联邦管辖权既需要研究联邦司法权力本身的性质问题(如宪法第三条的“案件与争议”要求),又需要研究司法语境下怎样处理联邦与州、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此外还有司法与其他政府机关的关系问题,如主权豁免原则、政治问题原则以及对行政行为的审查等行政法问题。这三个领域里面,无论哪一个领域,处处都折射着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的司法哲学。
最为国外学者所熟知的当属联邦法院对抽象审查的拒绝。在司法权力的性质上,美国联邦法院拒绝对法条进行抽象审查,而是援引宪法第三条的“案件与争议”要求,即,法院只能管实际发生的案件与争议,不能在无具体争议或争议尚不明朗的情况下发表抽象的法律意见;必须有某甲诉某乙的情况下,才能在作出裁决的过程中宣布法律意见。
事实上,在1787年制宪会议期间,麦迪逊等人多次极力主张由最高法院与总统组成联席会议,对国会通过的法案进行抽象审查。然而最终通过的宪法,则拒绝了麦迪逊等人的提议,授予总统全权否决权——总统可以以任何理由否决立法,当然也可以进行他自己的违宪审查、以违宪为理由否决(这方面的经典例子是安德鲁·杰克逊总统否决为合众国银行续期的法案)。
而制宪过程同时也明确了,司法机关可以在具体案件的裁决中进行违宪审查,因为当时美国各州法院已经有了相当广泛的违宪审查先例。当然后话大家都知道了,就是出了一个叫马伯里诉麦迪逊的案子。那么无论是马伯里诉麦迪逊,还是麦克洛诉马里兰,还是布什诉戈尔,都是一个具体的案件。
坚持在具体案件作出审查,既是对法院权力的主动限制,又给了法院以充分的机会了解法律的现实影响从而做出更符合实际的判决。那么还有一点更隐晦的则是,坚持个案审查,给法院以机动空间,对于能回避的问题有更多的机会可以回避一时不便决定的重大宪法问题。
这就涉及到另一个紧密联系的司法原则,即宪法回避(constitutional avoidance)原则,也就是说,一个案件,如果能在普通法律的层面上解决,那么就用普通法律法规解决,能不用宪法解决,那就不要用宪法解决;即便用宪法解决,也要小心行事。布兰代斯大法官在1936年的阿什旺德(Ashwander v. 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案中的协同意见,详细阐述了这个理念:
法院不会在一个没有争议、对立的案件中决定法律的合宪性;
法院不会在必须决定宪法问题的时刻到来之前预先决定宪法问题;
法院不会作出超出具体案件具体事实所需要的、过于宽泛的宪法裁决;
法院不会在能以其它基础解决案件的情况下,决定宪法问题;
法院不会在请求方未能证明自己受到法律伤害的情况下决定法律的有效性;
法院不会支持受惠于法律之人要求决定法律合宪性的行为;
当国会立法的效力受到质疑、即便有相当严重的理由怀疑法律违宪,法院也将首先尽量试图找到一种不违宪的解释。
这么做的理由也是显而易见的:如果动辄将问题上升到宪法层面,那么宪法的威严将不复存在。显然,个案审查比抽象审查要更能实践这个原则——在具体案件中一个案件的事实与法律都可以有多种解读,选择一种避免宪法的解释,是更为容易的事情。
法院是所有时候都会主动避免宪法问题的吗?未必。所有美国一年级的法学生和来美读LLM的外国学生在民事诉讼程序上都会学一个案子,这个案子是1938年的伊利铁路(Erie Railroad)案。伊利铁路案,也是一个重大的宪法案件,它确定联邦法院在受理不同州诉讼方的纠纷时,需要适用州的普通法(这个州可能是案件所在地,也可能是法院所在地)而非联邦普通法,明确推翻了近一个世纪之前的1842年做出的斯威夫特诉泰森(Swift v. Tyson)案。
在伊利铁路案中,原告被被告铁路公司的火车撞伤,下级法院依斯威夫特案原则,应用联邦普通法,陪审团判决结果是原告胜诉。被告不服,一路上诉到最高法院。然而这个案件诡异的一点在于,争议的两方都没有要求最高法院推翻斯威夫特案,也就是说都没有要求废除联邦普通法——事实上,有意思的是,争议双方都不希望这一原则被推翻:对于原告来说,赔偿已经到手,自然不希望变更判决;对于被告来说,联邦普通法虽然在个案中的结果对不利,但系统上总体而言对铁路公司是更有利的。故被告请求最高法院审查的时候也没有要求推翻斯威夫特案,而是另行组织论点。就是这么一个上诉双方都没有提请法院作出裁决、也没有辩论的一个问题,法院却自己提了起来——判决下来,第一句话就是,“本案中的问题,是应否推翻斯威夫特案所确立的原则”,然后宣布,斯威夫特案的原则超越了宪法、是违宪的。——这份判决的作者是谁?正是上面那位号召“宪法回避”的布兰代斯大法官。
所以,只能说,个案审查、宪法回避原则,给予法院以足够的空间发挥其政治智慧,当不便决定宪法问题的时候,可以有退缩的余地而无需作出无谓的、引起争议的姿态,所谓有所不为而有所为。
此外,还有避免对立法、行政行为进行过多的干预的“时机成熟”(ripeness)原则,以及防止无切身利害方提起不利于有效裁决诉讼的“诉讼资格”(standing)原则,等等,都是在防止法院手伸得过长管得过宽。比如在“诉讼资格”原则下,一般而言,如果某个纳税人认为政府的某个开支违宪,不能以“我是纳税人、政府浪费了我的钱”为由提起诉讼,他不具有诉讼资格;或者某个公民认为某个法律某个行政规定违法违宪,仅仅是出于义愤和公民的责任感,在没有收到切身伤害的情况下提起诉讼,也是不行的,也没有诉讼资格。这就避免了对宪法问题的不谨慎裁决——比如张三其实是支持某项法案的,他担心法案的反对者会把法案告倒,于是抢先跑到法院去控告法案违宪、故意提出一些非常无力的论点令法庭裁定法案不违宪,那样影响也很不好,同时,这些原则也避免了对国会立法、政府施政的过多干预。
三、平衡克制的司法权力
同样,法院在处理与其他机关的关系时,也是抱着能屈能伸、有所不为的态度,无论是对待同级的其他机关,还是对待州法系统、处理中央地方关系的问题上。
在处理与联邦政府其他分支(立法、行政)方面,除了对国会立法的尊重、宪法问题的回避之外,最突出的两个例子是“政治问题”原则(political question doctrine)和“主权豁免”(sovereign immunity)原则。政治问题原则的核心是,不是所有的争议(哪怕可以认为是宪法和法律争议)都应当由法院来解决,如果宪法将某个问题完全划归三权中的另外两权,法院没有管辖权、无权干预。比如总统作为三军统帅的战争权力、国会的宣战权,法院一般是无权过问的,美国爱对谁宣战对谁宣战,法院管不着;卡特总统爱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管不着;国会爱弹劾谁弹劾谁,爱怎么弹劾怎么弹劾,法院管不着。政治问题,当然是政治解决。
在美国,联邦的“主权豁免”原则也是司法机关的主动创造(对于州政府的主权豁免则来自于第十一修正案的规定)。主权豁免这个东西,实际上是带有浓重的封建色彩的。所谓主权者(sovereign)以前指的是国王,而英格兰普通法院本来就是国王的信访办,以前人民有冤屈了,跑到国王那里去抱大腿,啊皇上啊可要为草民做主啊!国王只有两条腿啊,抱大腿的人多了,国王顾不来是不是,于是就出现了专职处理这些事情的机关和程序,代表国王主持正义,这就是英格兰普通法院的来源。后来有些人对普通法院不满意,又跑去抱国王大腿,于是后来又产生了一个衡平法院。但不管是普通还是衡平法院,都是在代表国王在主持正义,换言之,国王是法院正义的源泉——所以你怎么能诉国王他老人家呢?大不敬是不是。这就是主权豁免的由来——一般而言,臣民不可以在国王陛下的法院诉国王陛下的政府的。(当然,这不代表国王不可以诉你。)
美国联邦法院沿袭了这一做法,自然地将主权豁免原则应用到联邦政府。当然,在美国,坐在宝座上的就不是国王了,而是一个虚构出来的偶像,叫“人民主权”。除非主权者主动表示允许起诉,否则公民是无法诉政府的,这就等于把什么问题可以诉政府、必须以怎样的方式诉、能拿到什么样的赔偿这些问题,交回给国会和总统来决定。而国会和总统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来决定到底在何种情况下允许公民诉政府——政府的卡车司机撞人了,不赔不好吧?但过高的惩罚性赔偿,显然对政府/纳税人又不公平;过于广泛的允许公民起诉政府又会对政府产生干扰。(当然,针对官员官方行为的诉讼则是另一个话题,鉴于其复杂性这里不详述。)
在联邦主义的问题上,联邦法院同样有着能屈能伸的身段,妥善平衡中央与地方关系。前面讲的伊利铁路案,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由于宪法并没有授权联邦法院全权创制联邦普通法,因此在某些属于州法的固有领域侵占州法的地盘是不合适的。此外,如果一个案件在州法的问题上就能独立、充分的解决(adequate and independent ground of state law),联邦法院也不会加以审查。
即便是在联邦宪法、法律基础上对于州法的审查,联邦法院也常常需要谨慎行事。比如一个著名的宪法原则叫“普曼节制”(Pullman abstention),这个节制原则讲的就是,在以联邦宪法审查州法律时,如果州法院还未能对州的法律做出足够充分明晰的解释,那么联邦法院应当考虑暂时避免做出决定,以免误伤州法。也就是说,假如州法有若干种解读,有的违反联邦宪法,有的不违反,现在还不知道到底应该采取哪种解读,那么州法院系统应该首先有机会做出解释,如果他们选择了违反联邦宪法的解释,联邦法院再介入审查。这无疑是政治上的谨慎态度。
而确立“普曼节制”的普曼案,本身就这种是政治智慧的体现。普曼案决定于1941年,在普曼案中,得克萨斯铁路管理委员会的一项规定歧视黑人、使其无法充任卧铺车的乘务员。那时美国黑人民权运动已有起色,然而在社会对平权仍旧缺乏广泛共识、二战局势波诡云谲的情况下,最高法院强令一个保守州实行平权,显然是不现实的、也是缺乏政治智慧的。因为在美国官司都是很慢的,普曼节制原则要求联邦法院节制、请州法院先决定问题,就决定了这个过程被延后了很多年,说白了,就是一个“拖”字诀。战后随着大量黑人老兵回国、民权运动进一步高涨,才有了布朗案、1964民权法案等划时代的变革。所以,普曼案所体现的,也是一种相时而动的政治智慧。
四、结语
1789年9月24日,前纽约市市长、新官上任的杜安法官在曼哈顿敲响了法槌,纽约区联邦法院(今日的纽约南区联邦法院)第一次开庭,这是美利坚合众国作为一个主权的第一次司法存在。历经两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联邦法院已经牢固地建立起了自己的地位。
在美国许多地方,唯一能见到的联邦机关,就是美国联邦邮政和联邦法院——联邦的存在之少,以至于有些地方在早期,邮局和联邦法院共享一所建筑办公。然而,靠着有高度责任心和政治智慧的联邦法官,联邦的政治权威无处不在,中央的每一条法律、法规得到贯彻落实,正如美国宪法所规定的、最高法院在特斯塔(Testa v. Katt)案中宣称的,普天之下,国境线内,无论身居何处,联邦法律,就是此地的最高法律(the supreme Law of the Land)。
如果仅仅是凭着专业思维的一厢情愿,脱离了有所不为的政治智慧,那么靠着司法技艺,显然是无法维持中央权威的。美国的司法双轨制,从法院体系的角度看,由于把大量的案件剥离到联邦管辖权之外(之前提到过,州法院与联邦法院案件数量在100:1以上),使得维持这样一个小而精的、有高度荣誉感和政治智慧的群体成为可能。这样一个法官群体,依托联邦中央政治权威,上达天听下聆民怨,通过在涉及联邦法律、中央政策的重大问题上定纷止争,有效地保证了国家的安定和谐。
来源时间:2016/1/26 发布时间:2016/1/24
旧文章ID:86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