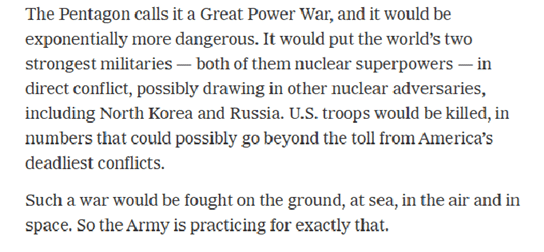宣兴章:正在浮现的世界新秩序
作者:宣兴章 来源:《当代世界》,2013年12月
在世界政治之中,秩序的变迁根植于格局的缓慢演化之中。从某种意义上说,秩序是特定格局下的交往形式。这种交往形式的变化、突变以及定型,取决于特定的技术水平、生产方式以及由此形成的国家之间力量对比的变化。因此,考察秩序的变迁,首先要考察在限定的技术条件下,全球生产力分布变迁造成的格局变化以及由此而来的对交往方式的要求。
正是在这种要求之下,由特定国家以及集团推动而形成新的秩序。全球将逐步进入动荡期在世界经济每一轮增长的长周期,都伴随着这样三种变化 :一是产业的复杂程度进一步提高,分工进一步细化 ;二是伴随着中心国家的产业升级,低端产业从中心国家向外围国家转移,引起国家间实力对比的变化;三是随着全球产业分工的变化,各国阶层结构随之进行深刻的调整。这里,全球的产业分工与各国国内社会对此的承受程度之间的互动是造成全球周期性动荡的重要原因。20 世纪 70 年代是国际关系中一个重要的分水岭。按照世界体系论的
说法,20 世纪 70 年代前后是一个霸权衰落期的开始,也是一个全体系金融扩张的新阶段。这个阶段的资本义世界经济的特征主要表现为 :“利润下降,大批资本家将寻求的活动转向金融领域,工资下降 , 产品利润的下降导致生产力重组,即降低工资、提高效率。就业的压力导致核心国家之间剧烈的竞争,进而使汇率起伏不定。”
此阶段是一个霸权衰落的阶段,是一个多极化、国家竞争激烈的阶段,也是我们生活于其间的阶段。分散的阶段开始之后,西欧、日本以及美国大量的产业向外部转移,同时资本循环空间扩大,将外部的产业与国内的产业联系起来,组成新的循环。发达国家国内的产业转移所留下的空间是依靠信息技术等高科技产
业以及金融业来填充的。因而,在这种背景之下,欧洲与美国都根据变化的情况进行了调整,这种调整所形成的发展模式几乎延续至今。霸权国家相对衰落,国家之间实力对比发生变化的同时,随着全球生产布局的调整,社会也发生深刻变化。
笔者在这里选取两个对于政治非常敏感的指标予以说明 :一是全球贫富分化加剧。虽然战后的 1950—1972 年前后,发达国家收入水平差距明显缩小。但 1972 年至今,世界范围内收入差距开始逐步扩大,无论是各国内部,还是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问题都日趋严重。据 BBC 的报道指出 :“在 1988—1993 年之间,世界人均实际收入增长了 5.7%,而全球最富裕的 20% 人口的收入增长可高
达 12%,最贫穷的 5% 人口的实际收入则反而下降了 25%。”
全球中产阶级在逐渐消亡,“这项调查从全球角度来说,中产阶级的缺乏令人担心,世界上大多数人属于收入最高或最低的阶层。84% 的全球人口只有 16% 的全球收入,全球最富裕的 10% 人口的收入是最穷的10%人口收入的114倍,
而这些差距可能还会扩大。”
二是全球失业率持续攀升。国际劳工组织的报告预计,2013 年全球失业人口将达到 2.02 亿的历史新高。2013 年发达经济体和欧盟地区失业率为 8.7%,东亚为 4.5%,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南亚分别为 4.5%和 3.9%,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区为6.7%。以上地区失业率都将比 2012年增长 0.1 个百分点,北非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失业率分别为 10.3%和 7.5%,与 2012 年的水平相当,中
东地区失业率则将达到全球最高的11.1%。报告还称,全球目前有 3.97
亿劳动者处于极度贫困状态,另有4.72 亿劳动者无法满足自身基本生活
需求。
国家既是产业的容器,又是权力的容器,同时也是社会的容器。在霸权衰落,格局重新调整之时,国际秩序开始趋于不稳定。在社会贫富分化加剧、失业率攀升之时,各国国内不稳定性加大。这进而传导至国际政治层面,引发国家间关系的调整。有的国家激进主义上升,政治动荡不宁,骚乱、种族冲突加剧 ;热点地区的矛盾持续发酵,甚至升温,这些都是全球和平的隐患。美国的第二个霸权周期与世界秩序海洋是现代世界资源运输的主要渠道。随着世界市场的扩大,海路运输也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海路运输在大宗货物的长距离运输中具有巨大的优势,这不但决定了现代大宗商品的运输方式,同时也决定了现代工业生产的布局方式。亚当·斯密写道 :“水运方式为各式各样的产业打开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市场,而这样的市场是陆路运输无法支撑的 ;正是在海岸带或航运河道岸边,各种产业开始细分和改进,而且通常过不了多久这些产业就会扩展到国家的内陆。”亚当·斯密的结论为现代科学的实证所验证。哈佛国际发展中心考察了地
理与经济发展的关系,A.D. 梅林杰、J.D. 萨奇斯、J.L. 加罗普三位著名学
者在统计世界经济与地理的数据之后指出 :“属于温带、距海 100 公里以内的近海温带在世界经济中起着主导作用。……它包括了美国海岸带的大部分、大湖区以及密西西比河流域,西欧的绝大部分,东亚的大部分(包括中国沿海、韩国和日本),澳大利亚沿海地区,新西兰,南美的智利、阿根廷沿海地区、巴西沿海的一小部分地区,北非沿岸的一部分,以及南非的南端。这些地区包含了世界上几乎所有强大的经济体,以及全球生产的相当大一部分。”
他们同时指出,“67.6% 的世界 GDP 产生于距海 100公里以内的地区,而这个区域仅占世界陆地的 17.4%。同时,世界 GDP的 67.2% 产生于占世界陆地 39.2% 的温带。近海温带占世界陆地的 8.3%、人口的 22.8%,但却产出了世界 GDP的 52.9%”。
美国与英国一样,是一个多面环海的国家。美国拥有两洋之利。国际关系学界通常不太关注的是,20 世纪 70 年代产业集群在美国的内部发生了“隐蔽”的转移。美国的大纽约地区,从 1929 年开始是美国成长为世界大国的主轴。大纽约以及新英格兰地区的汽车、化工、钢铁等工业是美国实力的基础所在。然而,从 20世纪 70 年代开始,增长中心开始从新英格兰——五大湖区转向了美国
的西部与南部,即是所谓的从“霜冻地带”转向了“阳光地带”。“从1968—1978 年之间,大多数新的工作职位,约占三分之二是在阳光地带或西部各州创造的。根据美国劳工部的计算,美国全国增加了 1840 万个新的工作职位,而南部和西部却增加了 1230 万个职位。与此同时,随着我们从工业时代摆脱出来,北部丧失了几十万个工作职位。”
在这种转移中诞生的三个经济大州是加利福尼亚州、佛罗里达州与得克萨斯州。其中加州现在的国民生产总值与中国差不多,人口接近于加拿大,拥有世界
上高新企业最密集的硅谷,同时拥有好莱坞的文化霸权。这种转移,其影响力是世界性的。可以说,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我们已经悄然进入了太平洋时代,其标志性的事件是 1971 年美国同东亚的贸易额超过了同欧洲的贸易额。
正如英国从波罗的海—北海—地中海的霸权时期进入大西洋的霸权时期,其
内部增长中心从伦敦及其周边地区转移到北部一样,美国的这种变化,也标志着美国从大西洋的霸权时期进入了太平洋的霸权时期,可以说,这是美国的第二个霸权周期。这种特性,是历史上只有一面临海的霸权国家所不具备的。在这个时期,美国的霸权呈现出若干不同于第一个霸权周期的特点。这个时期最为显著的特点是美元的全球扩张。20 世纪 70 年代的尼克松冲击之后,美元与黄金脱钩,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此后,美元、信息技术、新经济、军事威慑乃至打击,形成一个完整的霸权的闭环。维护这个闭环,遏制其他经济区内的深度合作,尤其
是货币合作,成为美国的一个核心国家利益。美国重返亚太以及在欧元区周边的一系列举措,都可以看出其背后这个霸权闭环的影子。实质上,美国已经进入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阶段。
因为,包括信息产业在内的高科技产业以及金融产业,越发展越是要依靠全球市场,并且通过对软知识的控制来实现利润,因此,美国的寄生性将越来越强 , 并且要依靠军事、国际组织、多边机制等多种方式来维护这种寄生性。美国需要依靠全球对美国的开放性维持自己的霸权,而各个区域的深度合作本来就有对抗全球霸权的作用,具有排他性。美国会依靠经济、安全等多种手段不遗余力地
破坏这种排他性。这意味着一种过渡性的世界秩序的到来。那就是,一种强调知识控制、贸易保护、政治模式输出以及干涉,加上军事控制的霸权方式将逐渐形成。太平洋时代的政治新秩序正如许多学者已经发现的一样,现代世界的经济中心一直持续而缓慢地在空间上移动。罗伯特·吉尔平说:“在过去三个世纪中,核心区所在地和经济活动的全球分布不断变化,从地中海转向北大西洋,到了我们这个时代,又转向太平洋。亚洲和拉丁美洲新兴工业国的出现改变了国际分
工,并导致国际政治经济性质和领导权的深刻变化。”
现在,这种经济核心区正向中国临海地带转移。世界经济政治时间上的周期性波动和空间上产业布局的变化以及国家实力的变化是同步的,相互交错的。随之而生的是全球治理模式的变化以及霸权方式的变化。国际关系最为基础的层面是一个时期的生产力水平,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是生产力的地理分布,由此而产生的经济力量与国家组织形式以及资源禀赋等结合,形成特定的力量格局。这种力量格局以及获取资源方式所需要的形式,共同决定了特定的秩序。这个秩序既是一个主导国家自身的需要,也是世界对于主导国家的需要。英国是民族国家的崛起,一个完全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取代封建帝国以及城邦联合体的产物,这适应了战争信贷、国家推动战略性产业发展以及大规模贸易的需要。英国由此主导建
立了一个庞大的殖民体系以及一个基于契约的欧洲体系。而大西洋时代进入美国主导的时期之后,主导国家的规模更为庞大,由绝对的民族国家开始向一种基于特定价值的多族群国家转换,全球治理的方式,也由殖民统治转化为自由贸易,以及由此之上的全球性政治经济治理结构的转换。从英国到美国,我们可以看到随着世界经济在规模、范围上的不断扩大,依赖的水域的不断扩张,主导国家的规模也越来越大,从外部获取资源的方式也越来越巧妙,治理全球的方式也越来越正式化和普遍化。伴随着这个过程的是,内部治理的意识形态越来越具有普世性,这种意识形态以及治理方式不可避免地投射到主导国家对于全球治理的方式之中,产生新的秩序。太平洋时代的故事似乎与大西洋时代有着很多相似之处。虽然国家的体量更大,但是从地缘政治上看,大西洋时代英国的角色似乎变成了太平洋时代的美国,而那时的法国角色则变成了中国。大国博弈的舞台,由浩
瀚的太平洋取代了规模稍微小一些的大西洋。如果将国家仅仅看作权力的不可分割的微粒子,那么这种地缘政治上的很多特点还是存在的。但是,考虑到国家形态、观念以及相应的国际治理框架的变化,这种规模改变在很多方面是本质性的改变。不过,这种改变在太平洋时代的开启、发展的初期是很难完成的,整套的变革需要等到世界经济中心决定性地转向太平洋的另一边。中国的发展,首先,这是一个太平洋另一边的大国兴起的过程;其次,这是一个非西方的文明中心国家形成一种新文明的过程 ;再次,这也是一个欧亚大陆临海国家将现代化推向大陆深处,并与欧洲对接,形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岛的过程。从第一个层面来说,中国要避免霸权国—挑战国的传统游戏规则,要避免落入“太子困局”。当很多人都认为某人会作为权力的继承者,进而引起权力者的警觉以及旁观者站队的时候,继承实际上可能无法实现。权力中心的转移不是一种继承,而是一
种替代。是一种生产方式以及由此产生的资源控制、管理方式的替代。最好的竞争是让传统的竞争对手无法真正参与竞争。
从第二个层面来说,在 21 世纪的上半叶,中国没有能力塑造一个自身主导的世界秩序。但是,可以参与、改造并在局部对抗现有的秩序,完整阐述自己的世界秩序主张。正如美国提出“威尔逊十四点”,完整地阐述了一个新生大国的全球理念一样,中国需要总结、概括自己的全球理念,而不仅仅是外交理念。著名学者赵汀阳在《天下体系》一书中指出 :西方本质上没有一种世界理念,而中国的“天下观”并非站在国家的立场上,一开始就把世界变成考虑政治问题的
最高存在,这种观念超越了西方。中国拥有独特的文明。西方文明基于绝对理念而建构,由律法而至法人,由法人而至企业、主权国家。为了适应没有政府的世界,虚构了一个国家诞生之前的“无政府状态”,其逻辑落点就是世界政府。而中国的天下体系理念可以更好适应全球多中心的治理,可以更好容纳文明的多样性和国际关系的民主性。中国要深入挖掘植根于传统与现实之中的秩序主张,提
出全世界,尤其是伊斯兰世界、拉美、非洲等广大发展中国家可以广泛认可
的系统主张以及制度设计。从第三个层面来说。两百多年来,世界政治权力中心又开始转向亚欧大陆。期间以及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亚欧大陆之外的岛国仍会通过均势策略控制着大陆岛。新型战略武器的发展已经部分弥补了一面临海的大陆国家的劣势,但是这只是部分弥补。新的大国的崛起,一定不是单独的国
家的崛起,而只可能是一种国家群落的崛起。这种群落不简单是拿破仑“大陆政策”式的捆绑,而是一种新型的群落关系。这种新型的关系将把现代推进到亚欧大陆的纵深,使得大陆岛重新连接为一个整体。就短期来看,中国最大的挑战就是要为世界经济放缓之时所出现的各种变化做好充分的准备。中国的弱点在于海陆兼备。就世界历史来看,海陆兼备的国家,在现代化不可避免地受到海洋性与内陆性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甚至会引起大规模的社会动荡。因而,控制、缓解、消除这种动荡的机制,就变得至关重要。
来源时间:2015/7/27 发布时间:2015/7/26
旧文章ID:49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