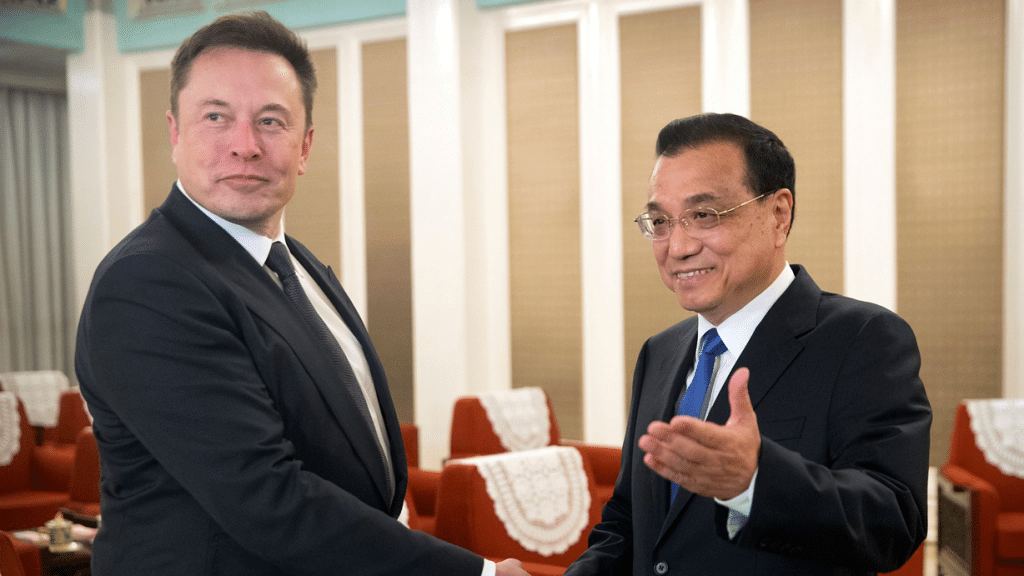张毅:第一位“雇用”中国大陆学者的国会议员
作者:张毅
2023-03-18
昨晚看到美国前联邦众议员帕特•施罗德(Pat Schroeder)因病去世的消息,心情顿时沉重了许多。
1985年底至1986年底,我作为“国会学者”(Congressional Fellow)为两位美国国会议员担任过“立法助手”(Legislative Aide)。第一位就是来自科罗拉多州的施罗德, 第二位是来自蒙大拿州的参议员、2014-2017年间出任美国驻中国大使的马克斯•博卡斯(Max Baucus)。我应当是1949年之后第一位在美国国会工作的中国大陆学者,施罗德因此是第一位“雇用”中国大陆学者的国会议员。
“国会学者项目”(Congressional Fellowship Program)由美国政治学会(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组织,参与人员主要是美国政府行政部门官员和大学教师,也包括少数外国学者。项目为期一年,大多数人会为两位议员工作(通常是一位参议员和一位众议员),时间各半年。
1981-1983年间,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工作,重点研究美国国会。1984年1月,我作为美国所公派留学生到弗吉尼亚大学攻读政治学硕士学位,主修方向仍是美国国会。1985年夏,我完成硕士学位课程,申请参加国会学者项目获得批准。由于在国会工作没有报酬,资助我留学的美国福特基金会同意延长资助一年。
美国政治学会虽然是项目组织者,但并不负责分配工作(国会议员也不会接受学会的分配),因此每个项目参与者需要根据自己的兴趣列出一个议员名单,然后逐一上门求职。1985年冷战尚未结束,美国政府对待苏共和中共态度固然有别,但国会总体反共势力仍然很强,不少议员贬义地称中国为“赤色中国”(Red China),因此我颇为担心能否找到“雇主”。
记得我最初的名单上主要是来自深蓝选区的民主党众议员,包括施罗德和加利福尼亚州的芭芭拉•鲍克萨(Barbara Boxer),原因一是共和党总体上更加反共,接受我的可能性可能更低;二是颜色深意味着议员地位稳固,不会因雇用一个来自“共党国家”的人而过分担忧选民的负面反应;三是在项目的第二阶段我还有机会找一位共和党参议员。(我在第二阶段的确找了几位共和党参议员,包括来自犹他州的保守派参议员奥林•哈奇(Orin Hatch),但都遭拒,后来民主党参议员鲍克斯决定接受我,也可以说是塞翁失马。)
令我喜出望外的是,施罗德似乎并不在意我的中国背景,面试后即决定“雇”我。施罗德当时是美国名望很高的女国会议员,能为她“打工”超出了我的期望。她生于1940年,父亲曾是飞机驾驶员,后拥有一家航空保险公司,母亲是小学教师。1961年,施罗德本科毕业后就读哈佛大学法学院,第二年与同学詹姆斯•施罗德(James Schroeder)结婚。1964年法学院毕业后,两人移居科罗拉多州丹佛市,詹姆斯入职一家律师事务所,施罗德则在当地劳工部门和学校工作。
施罗德走上政坛纯属偶然。1972年国会选举,热心政治的詹姆斯与其他民主党活跃人士商讨本党候选人人选,不料有人居然提名施罗德,商讨之后施罗德也感到可以一试。她此前从未参与政选,没有任何知名度,共和党对手因此轻敌,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也不报任何希望,结果却是施罗德胜出。1972年也是总统大选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尼克松赢得美国50个州中的49个(仅仅输掉了马萨诸塞州),施罗德在大环境如此一边倒的情况下居然能击败共和党在任议员,堪称奇迹。在此之后,施罗德基本毫无悬念地连续11次赢得连任,直至1997年退休(她连任竞选得票率只有一次低于58%)。
施罗德口才好,反应快,常能说出十分生动的精辟名句。把里根形容为“不粘锅总统”(Teflon President),就是她的创造。有人怀疑妇女能否既当议员又做母亲,她的回答直截了当:我有头脑,也有子宫,两个都运转正常。五角大楼官员在国会听证会上为战争辩护,她戏虐地讽刺:你们如果是妇女,一定会没完没了地怀孕,因为你们永远不会说不。(顺便提一句,施罗德是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第一位女性委员,坚决反对越战,1972年初次参加众议员竞选时,联邦调查局(时任局长仍是胡佛)曾专门安排线人监视施罗德和她丈夫。)

我作为施罗德的立法助手(在国会为议员工作的人大多为立法助手),主要工作包括研究政策和法案;撰写备忘录;回答选民来信;接听选民电话;邮寄竞选宣传品等。施罗德知道我的目的是要从学术角度了解国会的实际运作,因此尽量提供方便,不仅让我在华盛顿办公室工作,还安排我去她的选区丹佛市,看她实际如何与选民打交道。她甚至带我参加国会委员会听证会,她坐前排,我坐后排,居高临下地“俯视”参加听证会的美国政府官员,感觉可以说是“极其良好”。
我同时完全享受“国民待遇”。我有国会工作证,可以随意进出国会办公楼。我有施罗德办公室的钥匙,晚上或周末可以一人在办公室加班。我在国会停车场停车,在国会食堂吃饭,在国会乘坐专用小地铁,如工作需要还可以进入众议院会议大厅。1980年代中美关系之紧密,或许由此可见一斑。施罗德的“行政助手”(Administrative Assistant, 即议员助手总管)1988年曾发出感叹:现在很难相信中美开始交流还不到10年时间,也很难相信我们曾经是敌人;时间不仅可以治疗创伤,而且可以清除对伤口的记忆。(如果让他评论今天的中美关系,他大概会说很难想象我们的关系曾经如此好过。)
国会学者项目结束后的十几年间,我与施罗德一直保持联系。逢年过节,我们会互相寄卡问候,她还经常亲笔写信。1987年夏,施罗德曾参加民主党总统预选,民调支持率一时接近后来成为民主党候选人的迈克尔•杜卡柯斯(Michael Dukakis)。她来信说,我们现在格外忙乱,你快回来工作吧!几个月后她退出竞选,宣布决定时忍不住掉了眼泪,成为轰动一时的大新闻。有人怀疑她如当选总统是否足够坚强,是否能与戈尔巴乔夫等其他大国领导人谈判。在著名的NBC“周六晚直播” (Saturday Night Live)的搞笑节目中,她被演成了一个哭哭啼啼的女人。施罗德后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文章辩护,并把文章复印件寄给我。她说:我已不在去白宫的路上了,我们宣布胜利后即刻退出。

1997年,施罗德当了24年众议员后决定退休,我此时已到香港当律师,之后基本断了联系。2015年, 我突然收到她一封电邮,说詹姆斯的一位朋友在香港见到我,因此来信联系。她此时已搬到佛罗里达州过退休生活,希望我有空去看她。这些年我的确常想去佛罗里达,但终未成行,现在成了我一大遗憾。
施罗德性格爽快,乐于助人。1980年代,我有朋友被美国大学录取,担心签证被拒,希望我找施罗德写推荐信,我几次提出,她都每求必应。有一位被拒后才找到我帮忙,施罗德于是专门写信给美国驻华大使,使我朋友最终得到了签证。1990年代初,我们夫妻去科罗拉多州滑雪,计划在丹佛停留两天,她当时人在华盛顿,主动邀请我们住她在丹佛的家里,开她的车。施罗德是当地名人,我在街上开她的车,遇见好几个人眼神诧异,显然不理解为何一个亚洲面孔的人开了他们议员的车。施罗德还在家里留了一张纸条,开玩笑地称我为“张毅/江泽民”。将我与中国国家元首并列,一生仅此一例。1992年冬,我在密歇根大学法学院上学,施罗德作为国会代表团一员访问中国,行前专门写信问我是否有东西需要她帮忙带到我北京家中,并说明不要怕麻烦,因为代表团乘坐美国军机,“有很多的空地方”装东西。
我当上施罗德助手后才得知她大学本科曾学过中文,但我见到她时,应该是全还给老师了。施罗德有一子一女。女儿本科上普林斯顿大学,同样选修了中文课,毕业后还参加“普林斯顿在亚洲”(Princeton in Asia)项目,到大连理工学院教了一年的英文。
作为众议员,施罗德的主要立法贡献是促成国会通过一些促进妇女平权的法案,被称为是妇女平权的“开路先锋”(trailblazer)。肯尼迪总统顾问、演讲稿撰写人泰德•索仁森(Ted Sorensen)说施罗德多才多艺,会起草法案、发表激昂动人的演说、驾驶飞机、烘烤蛋糕、通过法律、独创名句、竞选总统。施罗德去世后,拜登总统特别发表声明,赞她在众多问题上坚持公平、明智的政策和妇女平权,结果是通过一系列法律改善了数以百万计的妇女(以及男人)的生活。
于我而言,她还是一个开明、热情和善良的美国“老板”。
2023年3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