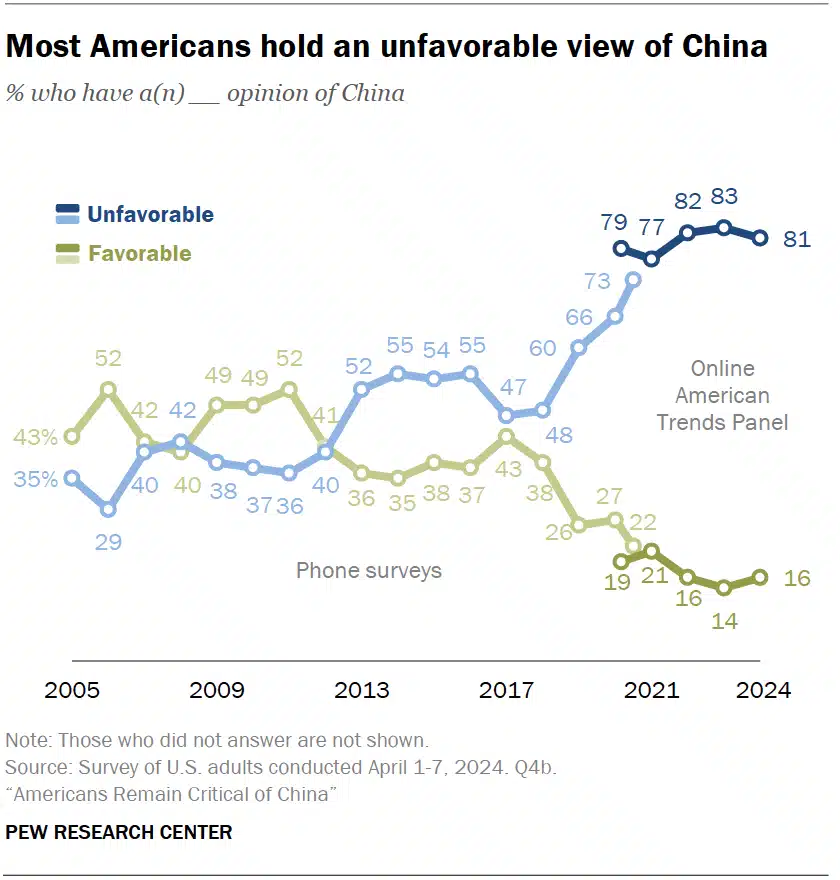王希:如何破解美国式斯芬克斯之谜?
作者:王希
2022-07-28
本文作者王希,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印第安纳大学历史系教授。本文为2022年7月16日作者的会议发言,于2022年7月25日修订。文章原标题为“如何破解美国式斯芬克斯之谜?”。
“重新认识美国”在最近成为了一句很时髦的话。2020年,我们的书无法出版,人民日报出版社却出了一本新书,是关于美国问题和中美关系的,书名就叫《重新认识美国》。同年,人民大学主办了一次系列讨论会,标题也是“重新认识美国”。网上搜索一下,发现“重新认识美国”的提法早在21世纪初就被频频使用。将历史追溯得更远一点,我们可以说,从18世纪末中国人开始意识到美国的存在开始,我们就一直处在对美国的不断的“重新认识”之中。不同的是,每次的重新认识,都带有不同的目的,使用的是不同的棱镜,自然也就产生了不同的认知结果。今天我们再次提出“重新认识美国”,一方面是因为最近美国国内政治发生了令人不可思议的变化,另一方面则是中国的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最重要的则是因为中美关系正在发生实质性的变化,所以,重新认识美国成为了“新时代”的一种政治需要和学术追求。
为什么要重新认识美国?对这个问题,因为研究者的立场和目的不一样,可能有多种回答。在后冷战时代,美国学者福山预测的“历史终结”没有出现,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遭遇了新兴国家的挑战,美国的影响力也大大削弱。即便如此,在目前的世界政治和经济格局中,美国仍然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中美两国的权力精英也都认识到,虽然两国的关系不再像2008年之前给各自和世界带来正面的、富有浪漫色彩的希望,但也还没有走到最坏的结果,双方仍然处于一种既竞争、又合作的“战略模糊”状态。为了要与美国长期地打交道,必须要清楚、准确地认识美国,读懂美国,做到知己知彼。这是中国人的古训,也是实用主义的哲学体现。
我认为还有另外一种认识美国的动机,即把美国当成一个对中国、对美国和对人类文明都非常重要的国家来研究。换言之,研究美国不是为了仰慕它,对其顶礼膜拜,也不是为了贬低它,视其为粪土,而是将它做为人类文明史上的一种独特的现象或一种先行者的实验来观察和分析。
的确,在人类文明史上,美利坚文明是一个后来者;但在近代国家发展史上,美国则是一个先行者。它在许多方面继承了欧洲和其他文明的成果,但在更多的方面,则是根据自身的需要创造了新的人类文明的成果。它的历史发展不是一种例外,但具有独特的个性。一些美国人甚至认为,它的独特性可以成为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类经验,其他美国人则反对这种看法,这是美国人对自己的“认知困境”。
我们也有自己的对美国认知的矛盾之处。我们有时会很不喜欢美国的做法,有些人甚至憎恨美国,但另一些时候,我们又不得不承认,美国在很多方面,走在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的前面。因为在某种意义上美国是在带头走一条无人走过的路,所以它遭遇的挑战一定更多,它更有可能遭遇决策的失误,它所遭遇的来自国内和国外的怨恨也一定更多。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将美国看成是一种人类政治的实验,我们也许会有另外一番研究心态和眼界,我们所关心的问题也许会超出为某一即刻的现实政治服务的局限。这是我想说的第一点。
如何重新认识美国,也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涉及美国研究的方法、问题和条件。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信息数据化、文献和资料电子化的时代,加上四通八达的互联网和人手一部的智能手机,研究美国的条件早已今非昔比。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这一段时间,美国国会众议院针对2021年1月6日暴力攻击国会山事件举行了7场听证会。这些听证会可以通过电视或网络同步观看,文字材料也可以从美国网站上免费获取,甚至不需要“翻墙”。这样的获取研究资料的便利在过去是无法想象的。20世纪90年代我写博士论文时,需要读19世纪70年代国会关于三K党暴力活动的听证会材料,当时我要在大学图书馆地下室的微缩胶片特藏部里埋头阅读数月,才能掌握材料。还有一个例子,几周前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公布了关于终止联邦政府对美国妇女堕胎权进行保护的多布斯案的判决意见,这是一桩关于终止联邦政府对妇女堕胎权进行保护的判例。要是在从前,外国研究者要获得判例意见的原件会很费事,但现在,不到24小时,判例的原件便在中国网站上出现,并且很快被翻译成准确的中文,在国内激发了一波难得一见的研习美国宪政和妇女公民权利的热潮。所以,研究美国的条件大大改善了。
对于美国问题的研究者来说,更大的挑战在于:提出什么样的研究问题,采用什么样的研究方式,如何从研究中得出中肯而有见地的认知。我觉得这些是问题的关键。
2018年,钱乘旦老师在邀请我们组织博雅工作坊时,只提出了一个要求,就是一定要请不同学科的学者来参加讨论。他认为,与其他的区域和国别研究一样,美国研究是一个跨学科的领域,需要多学科学者的共同努力,才能获得高水平的、有深度的研究结果。在编辑《重新认识美国》时,我们的体会也正是如此。就“特朗普现象”的研究而言,不同学科的学者选取了不同的视角、方法和材料,如刘瑜关注的是20世纪60年代“权利革命”以来美国左右政治文化的冲突,张大鹏梳理白人民族主义思潮的延续与变异,赵梅讨论媒体“中立”化现象的消失,赵蒙旸勾画新媒体时代都市右翼的构成与活动,它们从不同的角度来解释特朗普现象为何得以产生。在分析特朗普的政治与政策方面,张毅剖析了特朗普的个性、行为方式与执政的关系,达巍和张翔将特朗普执政放到新自由主义范式序列中来分析,张业亮则将特朗普的解构行政国家的政策视为一种反新政自由主义的动作,刁大明从政党政治的角度出发,描述共和党的特朗普化现象。所有这些研究,在我看来,都是不同学科的学者力图探求新的美国研究路径的一种努力。这些研究合在一起,便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完整、更复杂,我相信也是更准确的对特朗普现象的认知。单科学者往往无法做到这一点。
我们这本书的标题叫做《重新认识美国:来自当代的反思》,英文标题是“Rethinking the United States in a New Era: Contemporary Reflections”,我们意在强调“新时代”,所以,“New Era”是一个关键词。我们需要重新认识美国,是因为美国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美国的内部结构和外部环境在新的时代中都发生了迅猛的变化。这个变化之突然和剧烈,对美国的体制、美国思想、美国传统和美国人都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不光是美国人感到不适应,连美国之外的人也感到不适应,所以有了杨洁篪主任“我们过去把你们想得太好了”这样的反应。
我们看到很多最近出现的美国乱象,包括政党政治的极端化,分裂式政治的运作,宗教和文化价值观的冲突,以及来自左右两翼草根阶层的反抗运动,对权力精英和建制派极度的失望,以及围绕民权运动和权力革命的结果激烈的博弈,这些都反映出美国内部结构性冲突的加剧。特朗普在2016年当选当然不乏偶然的因素,但一定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他四年的执政进一步恶化了美国政治生态。在2020年大选中特朗普的失败透出一个信息,有相当一部分美国人企图利用现有的美国体制来阻止这个国家滑向更加失败的深渊。
然而,特朗普的下台并不意味着“特朗普现象”的消失,即便唐纳德·特朗普在2024年不出来参选,其他的特朗普也会跃跃欲试、取而代之。所以“特朗普现象”成为新时代美国的一种政治象征,我甚至认为会成为一种挥之不去的幽灵,将长期在美国政治上空盘桓。
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如何重新认识美国,这是摆在美国研究者面前的问题,回答这些问题是时代的要求,不只是为了中国找到应对之策,更重要的是探索人类政治文明的局限性和潜力,以及可能的方向,也就是说我们要跳出比较狭窄的范围来研究美国。
我的10分钟已经快到了,我就抓紧时间讲几个需要研究的具体问题。我最近看了美国国会众议院1月6日委员会关于暴力攻击国会的7场听证会,从中了解了国会山事件的许多细节。有些细节可谓触目惊心,将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古老的民主体制的脆弱之处暴露无遗;与此同时,也有很多细节展示了美国体制的内在力量和韧性——许多人,包括特朗普的支持者在内,在最关键的时刻将对美国宪法的忠诚置于对特朗普本人的忠诚之上,从而避免了美国民主的失败。这是所有美国人应该感到幸运的地方。听证会也促使我思考“如何重新认识美国”的问题。应该研究的问题很多,但我觉得在在未来的美国研究当中,应该更深入地研究以下四个问题。
第一,美国的选举制度。这个问题我在自己的文章有所讨论,但远远不够。选举制度在美国政治中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是所有国家和政府权力产生的体制程序。我们对美国选举体制知之甚少,尤其不了解各州的选举程序、选区的划分、选民资格的界定与管理,以及选举计票的复杂程序等。这是美国政治中最古老的程序,从建国开始便存在,同时也是使用最广泛、最频繁的体制,美国大大小小的政府官员、议员、甚至有些州的法官都是靠选举产生的。我们对这些细节了解多少?选举权的扩展曾经是美国民主演进历程中最伟大、同时也是最血腥的故事,我们对此有多深入的认知?与此同时,一些势力企图通过各种手段将选举权从选民手中夺走,也是最近的美国政治现实,我们对各州围绕选举程序、选民资格所展开的政治博弈了解多少?关于权力的争夺并不止是发生在高层,而更多地是发生在基层,我们对州和地方一级的选举制度是否了解?由此可以引申和展开研究的其他一系列问题,包括选民的构成、选民的区域分布与变化(与美国人口的变化和流动密切相关)、选举文化等。还有就是选举的政治运作,包括选区的划分、选民的动员、党派候选人的安插、主要政党的党纲写作、选民的意识形态的建构等,这些是我们过去对美国选举制度及其文化了解不深的地方。
第二,党派性政治。近期美国政治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分裂政治”(divisive politics)的加剧和政治博弈中党派妥协空间的消失。美国政治得以有效运作的前提是博弈各方有达成妥协的意愿,但在“党派性”(partisanship)主导了政党政治的时候,“民主的政治”就会可能演变成为“党”“政”不分的政治。目前国会内部的许多僵局正是因此而产生,而联邦最高法院内部的保守派与自由派之分也与此有密切关系。但什么是“党派性”?它如何产生,又如何不断增强?“党派性”与各级政府决策中的“公共性”(超越党派政策目标的政策)如何平衡,如何博弈?党派性的政治伤害极大,政治代价极高(在历史上有许多前例),但为何在政治博弈中反而愈演愈烈呢?目前出现的联邦政府的权力因为bipartisan legislation的缺乏基本失效、而地方权力(尤其是州权)的十分活跃的困境与党派性的关系何在?与此相关的其他问题包括:“共识制造”的失败,政党重组的历史与现实,政党内部不同利益势力的博弈与内部规则的建立,州一级的政党委员会的构成与运作,政党意识形态的建构,名人参政等,都值得深入和系统地研究。
第三,暴力与民主。暴力(violence)与民主(democracy)形影相随,两者的关系是美国历史和美国政治的经典题目,但我们对之知之甚少。首先是“暴力”的定义:什么是正当的暴力,谁能使用正当的暴力;此外,还有非法的暴力,谁又在使用非法的暴力等,这些问题需要研究。仔细阅读美国政治史,我们会看到,从美国建国开始,对暴力的使用与控制一直是美国政治(包括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美国独立是一场暴力革命,而后的美国内战——被称为是“第二次建国”——也是一场更加血腥的暴力革命。内战之后的重建事情白人至上主义者为了阻止获得解放的黑人公民行使选举权更是使用了“合法”的和“非法的”暴力。持枪的宪法权利与白人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合流,对少数族裔参与政治形成威胁,这种情形延续到20世纪60年代,直到联邦司法部根据《1965年选举权法》采用联邦执法后才被禁止。相关问题还包括:“显性暴力”与“隐性暴力”在国家制度中的建构与行使,执法部门(包括州与地方治安、警察队伍)对暴力使用的规范与尺度,联邦政府内部暴力实施机构的建构与协调等,都是国内的美国研究的空白。这些事实上是“国家制度建构”(state-building)的重要内容。需要明白一点:民主是美好的政治理想与愿望,但民主不是一张画饼,而是建立在“安全”基础上的;不同时代的“民主”,需要有不同内容的“安全”保障,而所谓“安全”与暴力的定义与使用密切相关。
第四,“法治”的力量和局限。这是我从国会听证会中受到的最大启发之一,也是对美国“法治”(rule of law)的最深感受。虽然特朗普认为他任命的官员应该按他的指示来行事,但在涉及宪政规范的问题上,许多他任命的官员(包括内阁成员、司法部高级官员)和州政府的官员,都遵循以宪法为上的政治操守,对特朗普提出的许多违反宪法常规的做法和“命令”予以劝诫、阻止、反对和公开的抵制,许多人在关键的时刻辞去官职,以示抗议等。这些官员曾经是特朗普的支持者,在意识形态上是分享共和党的价值观的,至今也是如此,但他们在涉及宪政问题(如大选是不是有舞弊现象,总统是不是可以单方面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就宣布大选无效,总统是否有权命令司法部宣布某州的选举结果无效,州立法机构是否可以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配合特朗普的需要、宣布本州大选无效等)时,却能够做到放弃“党派忠诚”、维护宪法程序的权威,他们如何做到这一点,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等,是需要研究的。因为这不是一个简单个人良心和政治素质的问题,这里面涉及许多的问题。特朗普推翻2020年大选结果的企图没有得逞,相当一部分原因在于他任命的司法部高级部门首长的抵制、关键州州议会共和党人议长的抵制。所以,美国政治中 “法治” 的内容、程序、文化值得深入研究。
与之相关的是“法治”的局限性。这也是一个大问题。我在讨论特朗普如何当选的文章中对此做了初步的讨论——一个选举经验丰富、选举制度规范、选举历史悠久的国家为何产生了特朗普这样的总统,是美国人值得深思的,也是所有外国的美国研究者值得深思的。如果美国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国家倒也罢了,但是美国的选举牵动许多国际问题和国际秩序,直接影响许多双边关系,不管我们是否承认,美国选举不再是一个美国的国内政治问题,而是一个具有国际影响和后果的美国问题。美国法治的局限性及其修正的可能非常值得研究。
传统的美国象征是自由女神像,给人一种美好的希望。现实中的美国则更像是古希腊传说中的“斯芬克斯”(Sphinx),它具有一种不断变换的奇特组合,令人捉摸不透,并不断地给人出难题。我们现在面对的,也许可以被称为是一种美国式的“斯芬克斯之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