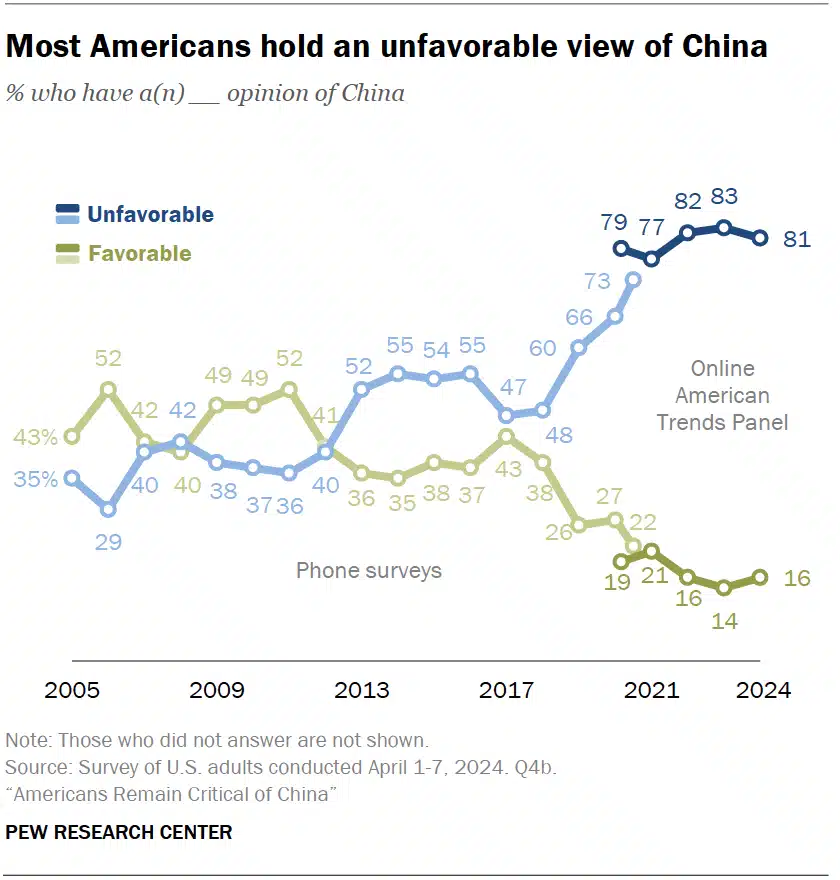中评智库:美式民主外交的三重谬误
作者:郑保国 来源:中评社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郑保国在中评智库基金会主办的《中国评论》月刊9月号发表专文《美式“民主外交”的三重透视——兼评“美国制度霸权论”和“美国民主霸权论”》。作者认为,美式“民主外交”的最大特性在于它深受美式民主的影响:根基于美式民主是其本质特征,扩展美式民主是其目标特征,藉鉴美式民主制度是其方式特征。祗强调美式“民主外交”之方式特征的“美国制度霸权论”隐盖了其实质;而认为美式民主决定了美国霸权的民主性质的所谓“美国民主霸权论”,则是对其实质的美化,具有三重谬误。文章内容如下:
引言
西方经典现实主义外交理论认为,外交取决于权力和利益,与国家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社会制度无多少关系。而体现西方自由主义外交理论的美式“民主外交”偏偏重视意识形态和价值观输出,强调制度规范和市场开放之积极作用。美式“民主外交”最独特之处在于它与美国国家特性和国家使命密切相关,其总体性成果是二战后美国主导构建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这个史无前例的“理想”国际秩序,却遭到以“美国优先”为原则的“特朗普外交”的严峻挑战。特朗普公开称自己是民族主义者而非全球主义者,且以其极端狭隘的“国家主权观”反对全球化和全球治理。2018年9月25日,他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说,“美国由美国人治理。美国拒绝全球主义,美国崇尚爱国主义。”〔1〕因此,约翰·伊肯伯里认为特朗普治下的美国在五个方面(国际主义、市场开放、多边规则与制度、美国社会多元文化与开放性、西方自由国家联合体及其独特合作能力)严重威胁着自由主义国际秩序。〔2〕
然而,“特朗普外交”并非“商人外交”和“武士外交”,而是这两者与“教士外交”的结合,即特朗普政府在极力追求商业利益和扩军好斗的同时,也大肆抨击敌国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大力宣扬美式自由民主价值观和推行美式“民主外交”。“特朗普外交”的“三合一”特点显着体现在其对华外交中。拜登政府对华外交大体上延续了这一特点。这两届美国政府都以“普世价值”的推行和捍卫者自居,以“保护人权、促进民主”为由肆意干涉中国内政,以致中美在涉台涉疆涉港涉藏问题上激烈交锋。可见,美国共和民主两党政府都搞美式“民主外交”,祗是手段、方式和力度有所不同。这是因为美式“民主外交”深受美式民主影响,任何美国政府都不可能不搞“民主外交”。 美式“民主外交”体现和维护的真是“普世价值”吗?美国对华“民主外交”真是在保护中国人权、促进中国民主吗?本文从根基与动因、目标与使命、方式与手段三个维度深度透视美式“民主外交”。
一、美式“民主外交”的民主根基与动因
从根本上讲,国家特性(意识形态、文化价值观、社会制度、国内政治等)对国家的外交政策具有重大、深远影响。美国国家特性集中表现为美式民主。所谓美式民主就是被美国宣扬为具有“普世价值”、代表人类社会最高形态的美式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包括其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自由民主价值观、民主共和制度、国内多元民主政治。自由民主是美式民主的标签,美式资本主义被称为典型的自由民主资本主义。美式民主对美国自身发展和外交政策的影响尤为重大和深远,是美式“民主外交”的根基与动因。
从宗教信仰、思想意识或价值观层面看,美式基督教和美式民主为美式“民主外交”奠定了思想基础。虽然美国形式上政教分离,但其浓厚的宗教意识对其外交潜移默化的影响很大。大多数美国人信仰崇尚发家致富的美式基督教新教,认为不信上帝是邪恶的,且相信通过自我奋斗获取财富才会成为上帝“选民”。“美利坚使命”思想认为,作为上帝“选民”,美国人被赋予一种特殊职责,即以他们的宗教信仰拯救邪恶的旧世界。受新教伦理洗脑的美利坚在成功开拓北美殖民地后又在反专制反殖民的独立战争中成功建国,树立了对资本主义自由民主的坚定信念。以个人主义、自由、民主、平等、宪政、市场经济等理念为内涵的“美国信条”(American Creed)和美国“独特、优越、至上、救世、无私、伟大”的“美国例外主义”(American Exceptionalism)信念是凝聚没有共同血缘关系和民族文化传统的美国社会的基本政治共识和“公民宗教”(civic religion)。美国天真地相信美式民主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救世良方,坚信输出美式民主有利于世界和平与繁荣,坚信自己有责任有能力使其“普世化”。换言之,清教主义的“救世”使命观和美式民主是“普世民主”的信念,共同导致了美国在宗教信仰和政治思想方面的对外扩张性,由此奠定了以输出美式民主为己任的美式“民主外交”的坚实思想基础。
从制度层面看,美国首创的资本主义民主共和制度是美国社会稳定和发展壮大的制度基础,也是美式“民主外交”的制度基础。美国的政教分离、宪政法治、代议制民主、三权制衡、文官控制军队、多党竞争、普选、舆论监督等制度设计能够避免美国民众最担心的权力集中对其宪法权利的侵犯,他们可通过许多渠道表达自己的各种诉求。美国没有阻止人们在社会各阶层和全国各地自由流动的制度障碍,人们普遍信奉人人平等,基本没有阶级意识,甚至不喜欢“阶级”一词,〔3〕且广袤的中西部曾经为源源不断的新移民提供发家致富的机会,因此美国基本没有激烈的阶级斗争使之陷入社会动乱。尽管自由市场经济使美国社会贫富差距不断拉大,但是美国人普遍相信机会平等、自由竞争,憧憬通过自身努力实现发家致富的人生理想,而不是把自己的贫穷归咎于美国社会制度和政治经济体制并试图推翻之,从而防止了神权政体、专制独裁、军事政变和暴力革命。而且,美国的橄榄型社会结构、自我反省意识、现实批判精神、强大社会舆论压力以及经常性选举等因素,共同构成所谓社会纠错机制,能够防止美国在错误道路上走得太远。美国通过渐进式政治改进和社会改良缓和社会政治矛盾,既避免了社会大动荡,又导致其繁荣昌盛、后来居上。随着美国国力和国际地位不断提升,自认为肩负“救世”使命的美国愈益坚信美式民主制度应成为普世性制度,从而强化了美式“民主外交”的制度驱动力。 总之,自认为担负上帝赋予的“救世”使命、笃信美式民主制度的美国,对无神论国家、非基督教国家、神权国家、非自由选举国家、一党制国家、军人当政国家等所有“非民主”国家有着本能的敌视和强烈的干涉冲动,由此生发了美式“民主外交”。
二、美式“民主外交”的美式民主扩展目标使命
由上可知,“美国立国的启蒙传统赋予美国一种认同,即把美国的政治原则视为具有普世的重要性和适用范围。”〔4〕基于这一政治文化传统,以民主的榜样和捍卫者自居的美国,自其霸权在二战后正式确立以来,尤其是冷战后它成为唯一超级大国以后,把美式民主宣扬为“普世民主”并大力对外扩展,其根本目标就是企图使其“普世化”,进而从思想和制度上控制世界,最终实现世界的“美国化”。美国经常打着维护自由、促进民主、保护人权的旗号违反国际法,或者以别国政府没有承担保护人权的责任为由对别国实施制裁,把它干涉别国内政、侵犯别国主权的霸权主义行为美化为扩展“普世民主”、保护“普世人权”的正义之举,极力扩展为它称霸全球服务的美式民主。按照美式“民主外交”逻辑,要成功遏制共产主义和各种反美主义,进而成为世界领袖并维持这一地位,祗有强大的经济、科技、军事实力和对国际制度的操控力远不够,还必须大力输出、扩展作为“普世价值”的美式民主,以使别国信奉美式民主价值观进而采用美式民主制度。美国自由国际主义认为,祗有美式民主实现了对整个世界的思想同化和制度主导时,它才能与世长存(即美式民主难以孤立地存在,这是它与美国传统孤立主义根本对立之处);因此扩展美式民主不仅是美国实现领导世界这个最高目标不可或缺的重要途径,而且本身也是与物质利益追求、国家安全维护并行的美国对外政策的重大目标,甚至是高于这两者的根本目标。1947年3月12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在标志美国对苏冷战正式开始的国会演说中公然宣称:“整个世界应该采用美国的制度,它祗有成为一种世界制度,才能存在下去。”〔5〕于是,在全世界扩展美式民主不仅是美式“民主外交”的核心内容和基本特征,而且被当作其首要目标甚至神圣使命。因此,二战结束以来,美国除了实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在国外驻军、组建军事同盟、构建并操控国际政治经济制度之外,还大力对外扩展美式民主价值观和民主制度。
冷战时期,美国与苏联开展全球性地缘政治争夺、军备竞赛并对社会主义阵营实施经济封锁,努力维护、扩展其安全和经济利益;与此同时,它打着捍卫自由民主的旗号,大力与苏联、中国进行激烈的意识形态、社会制度斗争,极力向外扩展美式民主,竭力遏制共产主义思想在世界的传播和社会主义阵营的扩大。美国把共产主义当作继法西斯主义之后又一个邪恶的极权主义,以基督教原教旨主义的思维方式认定它代表的自由民主主义与苏联代表的共产主义的较量是决定人类命运的善恶大决战。二战结束后不久,美国总统杜鲁门就抛出和实施旨在“保卫世界自由、遏制极权主义”的杜鲁门主义,正式展开意识形态色彩浓烈的对苏冷战,试图以扩展美式民主遏制共产主义发展。奉行自由国际主义的肯尼迪总统在就职演说中呼吁国民“不惜一切代价,顶住一切压力,克服一切艰辛,支持一切朋友,反对一切敌人,确保自由的存在与实现”。〔6〕为了遏制苏联和中国共产主义的发展壮大,美国竭力拉拢一切反共产主义力量,尤其是不惜把德、日这两个二战的死敌当作盟友大力扶植,强行向它们移植美式民主,甚至以旷日持久的大规模战争遏制共产主义在印度支那的发展。冷战结束前夕,美国藉海湾危机之机,打着“维护和平、制止侵略”的旗号,发动海湾战争,试图乘机实现中东“民主化”,进而建立美式民主统治下的“世界新秩序”。
冷战结束后,自以为赢得了“善恶大决战”的美国一度陶醉于“历史终结”的美梦中,冀望趁势实现美式民主的“普世化”。克林顿当局以“参与和扩展”战略取代冷战“遏制”战略,把促进全球“民主化”与美国的经济安全和军事安全并列,作为其对外战略三大目标之一,力图以美式民主一统天下。他的第二任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宣称,“今天,我们在每个大陆都有重要利益。……我们的利益是建立一个我们的价值观得到广泛认同、经济开放、军事冲突得到抑制、那些残暴对待其他人权利的人受到惩罚的全球环境。”〔7〕当时美国打着“人道主义干涉”的旗号,绕开联合国,率领一些北约国家先后干涉波黑内战和发动科索沃战争,强行向巴尔干地区扩展美式民主。
尽管冷战后美国大肆扩展美式民主在伊斯兰世界所引起的仇恨是美国遭受九一一恐怖袭击的重要原因,但是美国没有反思、收敛以美式民主扩展为目标的美式“民主外交”所激化的“文明冲突”,反而使其极端化,即力图通过武力扩展美式民主,以铲除恐怖主义、“邪恶轴心”、“流氓国家”等各种反美势力,最终实现中东伊斯兰世界乃至全球“自由民主化”。虽然美国共和党倾向于现实主义霸权外交,但是在以拯救天下为己任的美利坚民族主义因九一一事件而异常亢奋的形势下,由新保守主义主导的小布什当局悍然以战争向中东扩展美式民主。美国充分利用九一一事件,打着“铲除恐怖邪恶”、“保卫普世性自由民主”的旗号,先后发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力图把美式民主扩展到阿富汗、中亚和大中东地区。尽管美国陷入两场战争的泥潭,小布什当局仍一意孤行,认为美国的安全和自由与别国是否实现美式民主密切相关。小布什在连任的就职演说中声称,“自由在我们这块土地上的生存越来越取决于自由在其他土地上的成功。”〔8〕他说,“美国是一个有使命的国度,这一使命来自我们最基本的信念……美国的政策是在所有国家和文化中寻求和支持民主运动和民主体制的成长。”〔9〕与此同时,美国以俄罗斯等前苏联地区国家的民主不是真正的自由民主为由,通过煽动“颜色革命”,把美式民主扩展到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等国,并以此给俄罗斯施加强大的意识形态压力,企图在俄罗斯实现“颜色革命”,致使九一一后明显好转的美俄关系再趋恶化。小布什卸任后仍恋恋不忘推行美式“民主外交”对维护美国霸权的至关重要性。他说,“如果我们无法实践所宣扬的价值观,我们就无法领导这个自由世界,也无法吸引新的盟友加入到这项事业中来。”〔10〕为了重建美国的“世界领袖地位”,以自由国际主义为指导的奥巴马政府和拜登政府仍大力推行美式“民主外交”。
必须承认,美式“民主外交”曾取得了令美国自豪的成果。经过战后近30年的美式民主扩展与共产主义发展之间拉锯式的较量,到1974年“民主化第三波”开始时,基本符合美国标准的“民主国家”达到39个。到1995年“民主化第三波”达到高潮时,“民主国家”增加到117个,在191个国家中的占比达61.3%,这一比例在1974年是27.5%。〔11〕虽然亨廷顿从文明冲突的视角认为美式民主乃至整个西方民主并非普适性的,但他对美国推动的世界民主化赞赏有加,主张促使别国“认同民主、自由市场、有限政府、政教分离、人权、个人主义、法治等西方价值观,并把它们纳入自己的体制之中。”〔12〕美国学者戴蒙德曾经得意地写道:“共产主义溃亡,各地军人统治失去吸引力和合法性,一党制国家大量消失,民主制再无敌手,成为当今世界被广泛接受的唯一合法制度形式。全世界大约3/5的国家成为民主国家。”〔13〕
三、美式“民主外交”的民主制度方式
在双边外交中,美式“民主外交”往往以“保护人权、促进民主”为名,行干涉别国内政之实,而在多边外交中,它往往藉鉴美式民主的制度方式而非直接由实力说了算,尽量采用国际制度这种较民主较具合法性的文明方式。因此,美国霸权被新自由制度主义学派和新自由国际主义学派称为“制度霸权”,这被公认是美国霸权的一大特性。美国“制度霸权”不局限于其领导的西方阵营,其触角所及和影响是世界性的,也非纯自由主义性质,而是自由主义理念与现实主义联盟理论的结合,主要包括法理上以联合国为中心的世界政治规则、安全保障机制、人权保护规范和以布雷顿森林体制及其后续制度为代表的国际金融经贸体制以及以北约、美日同盟等基于共同价值观的多边、双边军事联盟为骨干的遍及全球的地区性军事同盟体系。二战后美国构建和主导的国际制度网络是美国霸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独特表现。“美国与以往霸权不同之处在于它不完全依靠军事实力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而是想建立一个由美国主导的制度化霸权体系。……制度化的霸权体系是通过建立多数国家接受的国际规范,使美国的霸权政策合法化,以便得到较多国家的政治支持,减少霸权政策对武力的过分依赖。”〔14〕伊肯伯里认为:美国霸权外交本质上是深受美式民主影响的自由主义霸权外交,即使美国现实主义霸权外交也具有多边主义和民主制度特性。他把美国“制度霸权”当作美国霸权外交是重视国际制度建设和多边主义合作的自由国际主义外交的证明,认为二战后美国在建立其霸权之时,采取了有别于其单边主义外交传统的多边主义模式,并以两笔现实主义交易为基础:第一笔交易即美国向自己的欧亚伙伴提供安全保护和在开放的世界经济中进入美国市场、获得美国技术和供应品的机会,作为回报,这些国家同意成为美国的稳定伙伴,向美国提供外交、经济和后勤支持,以确立以美国为核心的战后秩序;第二笔交易即欧亚国家同意美国发挥领导作用并在一个商定的政治经济体系内行使。〔15〕
“美国在一套规则和制度体系中行事,而这些规则和制度降低了它武断和歧视性地使用权力的能力。”〔16〕它通过建立、操控国际制度发挥国际主导作用和实现对西方国家的领导,对它认为的民主国家(主要是其盟国)比较讲民主协商,容忍不同意见。美国自由主义霸权外交的这种形式上的进步,既有利于缓和国际矛盾和合作解决国际问题,又在一定范围内有利于国际关系民主化,从而增强美国霸权的“合法性”和软权力。换言之,由于美国霸权外交不是如传统霸权国那样表现为直接的领土吞并、帝国统治、殖民奴役、军事占领或独断专行,而是尽量通过一系列全球性、区域性国际制度主导全球和地区事务,通过在一定范围内提供全球性、区域性国际“公共产品”,从而赢得了一些国家的追随、服从甚至赞誉,因此二战后美洲、西欧等完全在美国霸权治理下的地区总体上保持和平稳定与繁荣发展,尤其是北大西洋地区国际关系民主化程度比较高。
美国霸权采用“制度霸权”的方式,与美式民主有关。换言之,美式“民主外交”的民主制度方式源于美国政治价值观、社会制度和政治体制对美国外交的影响。很难想象一个国内没有民主价值观和民主共和制度的霸权国会采取“制度霸权”的方式。历史上的其他霸权国基本上都没有采取这一霸权方式。美国霸权一定程度上表现为“制度霸权”,显然有其国内的自由民主思想和民主制度做基础。美国对其国内政治秩序独特的自我理解,对美国领导人和公民如何考虑国际政治秩序是有影响的。〔17〕受国内自由民主价值观和民主共和制度的影响,美国在建立、维护霸权和对外交往时不再照搬传统霸权国的武力治理方式,而是藉鉴其国内民主制度,尽量采用国际规则、制度、规范,与盟国进行民主协商,有时也通过联合国处理国际问题。美国的自由民主思想与民主制度及反殖民帝国主义的外交传统使它总体上拒绝传统霸权的帝国治理模式,或者说美式民主很大程度上奠定了美式“民主外交”的国际制度基础。“美国是较早的成文宪法制国家,其长期的宪政主义政治思想对其外交政策的制定有着深刻的影响。”〔18〕“这种政治影响使美国的霸权政策十分重视国际组织及有形与无形的国际规范与机制。”〔19〕
四、“美国制度霸权论”的肤浅与“美国民主霸权论”的谬误
由上可知:没有美式“民主外交”的美式民主根基与动因,就没有其扩展美式民主的目标使命和美式民主的制度方式;而美式民主的制度方式根本上服务于美式民主扩展的目标使命。换言之,美式“民主外交”根基于美式民主这一本质特征从根本上决定了其目标特征和方式特征,三者构成美式“民主外交”的特征体系。因此,认识美式“民主外交”,必须透过其方式特征这个外在形式,认识其本质特征和目标特征及其危害。若祗强调其方式特征,就会相对忽视它根基于、服务于美式民主这一本质特征和它致力于扩展美式民主这一目标特征及其危害,以致陷入美国对外战略的制度陷阱。长期以来,在美国政治精英和学者的曲解和美化之下,美式“民主外交”的民主制度方式具有颇大迷惑性,成为美国霸权软权力的一个重要来源,而直接源于其方式特征的“美国制度霸权论”自然具有一定迷惑作用。
但是,无论美国的“制度霸权”多么具有“合法性”、多么吸引人,它总归是美式“民主外交”的形式和实现其基本目标(即扩展美式民主)乃至根本目标(即维护美国霸权)的一种手段与方式,无法改变其霸权实质。而且,正如以事物的非本质属性给该事物定性是对其误解一样,以民主制度性这一美式“民主外交”的非本质属性给它定性当然是错误的。由此可见“制度霸权”论之肤浅。
伊肯伯里认为,美国民主决定了美国霸权的民主性质,它是国际关系史上绝无仅有的“民主霸权”,称其为造福于世界的“民主和开放的霸权”。〔20〕他认为,美国霸权是“一个模糊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界限的延伸性体制”,即美国民主体制蔓延到其外交中,使它在对外关系中尤其是在与其欧洲盟国打交道时搞民主,通过制度彼此约束。〔21〕他把美国霸权定性为“自由主义霸权”(liberal hegemony),称之为“自由利维坦”(Liberal Leviathan),认为二战后美国把其超群的国际权力与自由主义国际规则结合,构建了史无前例的自由主义霸权秩序。〔22〕这就是所谓“美国民主霸权论”。
虽然美式民主从上述三个维度深刻影响美式“民主外交”,但其影响绝非是把美式民主的游戏规则照搬到美国外交中,因此不能得出“美国霸权是民主霸权”的结论。事实上,以美式“民主外交”的上述三大美式民主特征推导出“美国民主霸权论”,存在三重谬误。
第一,从概念本身看,“美国民主霸权论”在逻辑上自相矛盾。矛盾律告诉我们,在同一思维过程中或在同一论述层次上,不可使用两个含义完全相反的概念对同一对象或事物作出判断。如不能说“某某是君子和小人”。在国际关系或外交中,霸权与民主根本对立,不共戴天。霸权是国际体系中的一种主导权、支配权,意味着霸权国与其他国家关系的不平等,其本质违反国际关系民主化,而国际关系中的民主意味着无霸权,国际关系民主化就是要去霸权主义化。就美国与其霸权体系内别国关系而言,“霸权”表明它们之间是主导与追随、支配与被支配的不平等关系,而“民主”意味着它与别国平等相处,两者无法共存。虽然民主与霸权在美国自身独特地紧密结合在一起,但是两者的结合属于内外层次的结合(对内民主与对外称霸),不是也不可能在美国对外关系中结合在一起。事实上,似是而非的“美国民主霸权论”有意无意犯了偷换概念的错误,把美国的国内“民主”偷换成基本上不存在的美国对外关系中的所谓“民主”。因此,说美国霸权是“民主霸权”,就如说某人是“好坏人”一样不合逻辑。
第二,作为美式“民主外交”之国内政治基础和指导原则的美式民主,决定了其美式民主的扩展目标。这一目标使得美国经常违反国家主权平等和内政不容干涉的现代国际法基本原则,把自己的自由民主价值观和民主制度强加给别国,从而给国际关系造成严重消极影响,给地区稳定、国际安全和世界和平造成危害。美国努力实现美式民主扩展这一目标,在它看来是造福全世界的高尚追求和善举,但是实际上是要求甚至强迫它眼中的“非民主国家”违背国情地实施美式民主,这在国际关系中恰恰是不民主。为了成为世界领袖,美国在二战结束前夕一边构建基于大国合作但具有自由国际主义特征的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政治与安全制度体系和人权保护规范,一边构建基于自由市场主义的自由、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力图打造以自己为中心的战后世界新秩序。而在战后美苏分道扬镳和东西方冷战开始后,美国以自由世界领袖身份领导整个西方世界全面遏制和极力演变社会主义阵营,在社会主义阵营外构建起史无前例的自由主义霸权秩序。伊肯伯里自己认为这是以美国为中心的具有自由主义特征的新型等级体系,〔23〕或者说是“建立在美国实力支配地位和自由主义治理原则基础上的等级性秩序”〔24〕。既然是等级体系和秩序,成员间当然不平等,也就谈不上民主。事实上,美国在通过联合国操控国际政治与安全事务和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关贸总协定等全球性国际经济制度主导世界经济贸易的同时,通过北约、美洲国家组织、美日同盟等地区性多边国际制度和双边制度安排,与社会主义阵营以外的许多国家结成多个多边和双边政治、安全共同体,长期充当非社会主义世界的政治经济领袖和安全保卫者,在政治、经济、安全等领域谋取了十分巨大的霸权利益。虽然美国与盟国实行一定的民主协商,但美国远非与其势力范围内的其他国家平等相处。至于对其霸权控制之外的社会主义国家,美国曾长期采取完全不民主的全面敌对方式和隐蔽渗透方式。冷战结束以来,美国以世界领袖自居,仍在千方百计谋取霸权利益,更没有真正与别国平等相待。此外,民主的要义是重大决策由多数决定,但美国经常违背多数国家的主张、意愿和利益,最典型的事例就是不经联合国授权发动大多数国家反对的伊拉克战争。
第三,虽然美式“民主外交”的美式民主制度方式体现了美式民主对美式“民主外交”的积极影响,但由此推导出美国霸权是“民主霸权”的理论观点是错误的。即使美式“民主外交”的美式民主制度方式特征显示出一定的“民主性”,那也不过是成本较低的现代霸权治理形式,本质上仍是为美国构建、维护霸权地位和获取不公正霸权利益服务的。以手段或方式的文明进步性为目的的非公正性辩护,不合正义原则,从根本上讲站不住脚。霸权即便是基于民主政体建立起来,即使有时采用民主协商方式,仍然改变不了霸权的本质,它“在本质上仍是独断专行的”。〔25〕伊肯伯里在这里的错误是把事物的特征等同于其性质(特征是反映事物特点的标志,而性质指事物的根本属性),把事物的表象和形式当作其本质内涵。
五、结论
美式“民主外交”具有三大美式民主特征:根基于美式民主是本质特征,扩展美式民主是目标特征,藉鉴美式民主制度是方式特征。这三者共同构成美式“民主外交”的“三位一体”的美式民主特征体系:本质特征决定了目标特征和方式特征,目标特征体现本质特征并影响方式特征,方式特征服务于目标特征并美化本质特征。美式“民主外交”的民主特征体系反映了它在根基与动因、目标与使命、方式与手段三个维度都深受美式民主的影响。祗强调美式“民主外交”的方式特征的所谓“美国制度霸权论”是肤浅的。而概念上自相矛盾的所谓“美国民主霸权论”认为美式民主决定了美国霸权的民主性质,即美国霸权是“民主霸权”,这是对美式“民主外交”实质的误读和刻意美化。
注释:
〔1〕Remarks by president Trump to the 73rd sess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New York, available at:http://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remarks-president-trump-73rd-session-united-nations-general-assembly-new-york-ny/
〔2〕G. John Ikenberry, "The Plot Against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Can the Liberal Order Survive?" Foreign Affairs, May/June 2017.
〔3〕[美]威廉·霍姆多夫:《谁统治美国:权力、政治和社会变迁》,吕鹏、闻翔译,译林出版社,2009年,第12页。
〔4〕Samuel Huntington, American Politics:The Promise of Disharmony, 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3.
〔5〕Stephen E. Ambros, Rise to Globalism: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since 1938, Baltimore, 1971,p.19.
〔6〕转引自亨利·基辛格:《世界秩序》,中信出版集团,2015年8月第一版,第361页。
〔7〕Madeleine Korbel Albright, "Enduring Principles in an Era of Constant Change", September 20, 1997,Statement before 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New York City, US Department of State Dispatch, October 1997, pp7-8.
〔8〕President George W. Bush , Second Inaugural Address, 20 January 2005.
〔9〕同上。参见Thomas Carothers, U.S. Democracy Promotion During and After Bush, Washington, D.C.: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2007, pp.3-4.
〔10〕【美】乔治·沃克·布什:《抉择时刻》,北京:中信出版社,2011年8月版,第158页。
〔11〕Freedom House, Freedom in the World: the Annual Survey of Political Rights and Liberties, 1990-1991, 1991-1992, 1992-1993, 1993-1994, 1994-1995, New York: Freedom House, 1995. Freedom Review,Jan/Feb,1996.参见刘建华:《美国跨国公司与“民主促进”:一种国家—市场—社会关系分析视角》,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1月版,第81—82页。
〔12〕Samuel Huntington, "The West: Unique, Not Universal", Foreign Affairs, November/December, 1996, p.40.
〔13〕Larry Diamond, "Universal Democracy?" , Pollicy Review, June/July 2003, p.7.
〔14〕阎学通:《国际政治与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84页。
〔15〕G. John Ikenberry , "American Grand Strategy in the Age of Terror" , Survival ,Vol.43 , No.4 , Winter 2001-2002 ,pp.19-34. 转引自门洪华:《霸权之翼:美国国际制度战略》,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14页。
〔16〕[美]约翰·伊肯伯里:《自由主义利维坦:美利坚世界秩序的起源、危机和转型》,赵明昊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9月版,第258-259页。
〔17〕同上,第279页。
〔18〕金灿荣:《美国外交的国内政治制约及其在后冷战时期的特点》,牛军:《克林顿治下的美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99页。
〔19〕王缉思:《冷战后美国的世界地位与外交政策》,牛军:《克林顿治下的美国》,第33页。
〔20〕[美]约翰·伊肯伯里:《大战胜利之后:制度、战略约束与战后世界秩序重建》,门洪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87—193页。
〔21〕[美]约翰·伊肯伯里:《大战胜利之后:制度、战略约束与战后世界秩序重建》,第187-193页。
〔22〕John G. Ikenberry, Liberal Leviathan:The Origins, Crisis, and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World Order,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1.
〔23〕[美]约翰·伊肯伯里:《自由主义利维坦:美利坚世界秩序的起源、危机和转型》,赵明昊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9月版,第141-184页。
〔24〕同上,第6页。
〔25〕Lea Brilmayer, American Hegemony: Political Morality in a One-Superpower World, New Haven, CT: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4.
来源时间:2021/9/19 发布时间:2021/9/19
旧文章ID:26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