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毛学峰:中美关系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毛学峰(Andrew Mertha)是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保罗·尼采高级国际研究学院 (SAIS)教授,中国研究项目主任,中国全球研究中心主任。他是中美关系领域的著名学者。在这次访谈中,毛学峰教授探讨了中美两国领导人在两国关系中扮演的角色、中美关系与国内政治的互动、他对接触政策的看法、汉学在美国的发展前景、台湾问题以及柬埔寨在中美竞争中的作用等问题。
我听说您在中国生活了很多年。您能谈谈这些在中国生活的经历对您从事中美关系或中国研究的影响吗?
自 1988 年开始,我在中国度过了七年多的时光,尽管这段时间仍显得短暂。在这段时光里,我居住在中国的各个地方,特别是西南地区、长江下游地区以及广东/香港地区。这段经历给我带来了几方面的好处。首先,它让我更深入地了解了中国、中国人民、他们的生活方式,以及他们之间、他们与国家和与直接影响这一切的经济力量之间的互动方式。其次,长期在中国的生活对我的工作产生了重要影响。我的研究问题和议程通常需要我走出大学或者图书馆,亲临中国进行实地考察,这种亲身经历对我的工作至关重要,因为我的研究不仅局限于北京,而是希望它能代表中国更广泛的范围,并融入一些地方因素,这些因素是中国治理、国家与社会关系以及中央与地方互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政治的引擎。因此,长期且广泛的在中国的经历对我的工作至关重要。
另一个需要牢记的问题是,在研究中国时,即使处于最佳情况下,你可能也只能获得所需信息的 20%。正因为如此,很多关于中国的学术研究都是—也必须是—归纳式的;你必须根据极少的信息不断进行推断。最终,你只能依靠直觉,而对一个地方产生强烈直觉的唯一方法就是在那里生活一段时间。这并不意味着我不系统地思考问题。然而,有时你必须做出判断。至少就我而言,判断的依据是在该国待过相当长一段时间后才能获得的经验。由于这种接触的机会越来越少,这让我对双方处理这种关系所需的分析的质量感到担忧。
您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讲授有关当代中国政治和中国领导人的课程。您认为改革开放后中国领导人处理中美关系的理念是什么?美国领导人是如何应对的?
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我认为,自19世纪末以来,中国的领导人,不论是共产党领导人,国民党领导人,还是清朝皇室成员,至少是晚清宫廷中的改革派,都有一个始终不变的目标,那就是让中国变得富强。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们采取了各种不同的战略。今天许多美国人对中国变得如此强大感到惊讶。我的反应是,我们不应该感到惊讶。这一直是中国想要做到的。我们应该少花点时间在惊讶之中,多花点时间在客观、成熟地处理两国关系上。当然,与哪位领导人打交道对如何做到这一点有很大影响。
在改革开放前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和中国还没有什么联系。1972年,这种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地缘政治的考虑,目的是平衡苏联的实力,并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中美之间的安全。邓小平处理中美关系的理念是非常自信的:中国是一个弱国,需要西方,尤其是美国的资金、专业知识和资本。站在这个等式的另一方也符合美国的利益。因此,虽然两国的国内政治使得处理这种关系变得困难重重,尤其是在20世纪90年代,但是中美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相互支持的。
在江泽民时代的早期,中国一直在努力寻找自己在中美关系中的的政治立足点,而在克林顿总统的第一个任期内,美国也确实没有什么对华政策可言。直到1997年和1998年,两国领导人才得以在以经济为基础的语言中找到彼此的共鸣,从而建立起交往的逻辑。不幸的是,9-11事件让这一切努力付诸流水。在小布什政府时期,美国没有一个连贯的对华政策。奥巴马政府曾试图制定对华政策,但我认为双方都没有足够的决心和力量将其作为优先事项。
时间来到现在,情况变得非常具有挑战性,这不仅仅是因为–但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特朗普总统对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就摆在桌面上的美国对中国的一系列不满做出了反应,至少在他的支持者看来是这样。然而,对于微妙而复杂的中美贸易政策大动干戈,在经济和政治上对整个双边关系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而特朗普在COVID-19疫情期间针对亚裔的种族主义让情况让情况更加恶化。我认为,拜登总统上台后,他和国务卿布林肯并没有真正致力于废除特朗普采取的一些关键措施,这让人感到有些失望。这可能是美国国内的政治局势使然。目前的美中双边关系是我有生以来所见过的最糟糕的局势,甚至比1968年时更加糟糕。
中美关系一直是一种困难的关系。我认为处理这一关系最成功的总统有两位半。一位是尼克松总统。另一位是卡特总统,他们对两国关系的巧妙处理没有得到足够的赞誉。而“半位”指的是克林顿总统的第二任期,我认为他意识到了如何推进两国关系。在上述每一届政府中,都有改善和建立双边关系的真正连贯的承诺,这是其他政府所没有的。
您刚刚指出了您认为在处理中美关系方面比较成功的美国总统。那您如何评价邓小平之后的中国领导人为中美关系所做的工作?
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我认为,在邓小平之后的三位中国领导人中,在促进中美关系上做的最好的可能是江泽民。我认为胡锦涛时期中国更加关注自身,当时中国国内有很多批评,认为他在处理中美关系方面不够强势。在那一时期,中美关系开始有些偏离正轨。我认为现在的中国领导人从现实的地缘政治的角度看待中美关系。遗憾的是,即使中国领导人的态度有所缓和,我们两国的领导人也没有足够的意愿将两国关系与国内政治问题隔离开来,提升到更高的层次。
您能否详细谈谈您对将两国关系与国内政治问题隔离开来的看法?为什么这样做很重要?
我认为,中美关系一直受制于彼此国内政治的影响,而这也让处理两国关系变得非常困难。中国正变得比以往强大得多,在外交政策和投资战略方面也变得更加外向。这正是我们最应该相互接触的时候。但事实上,两国国内政治正在越来越多地干扰双边关系的稳定,为原本应该保持独立的双边关系带来了更多限制和挑战。
当然,我是一名学者,不是政策制定者,所以我明白在政策领域工作有多么困难。尽管如此,我并没有看到任何一方真正做出持续的努力来避免两国关系受到国内政治牵连。我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与美国政策制定者及其幕僚与中国同行之间庞大的专业网络的解体有关。特朗普总统在执政期间不再使用美国政府内部的中国事务专家,这让两国关系失去了这个由专业人士组成的减震器,任何纠纷都更有可能演变成危机。虽然现在政府中与中国打交道的大多是一些聪明人,但他们并不具备必要的深厚的中国经验,很难有效地管理两国关系。不鼓励希望在美国政府工作的人去中国,哪怕只是去学习语言,只会助长这种缺乏深入相互理解的情况。这不是追求我们共同利益的前瞻性方式。
了解中国政治在双边关系中的作用对美国决策者有何意义?
比我更聪明的人说过,美国政策制定者不理解中国国际行为的原因之一就是我们认为中国的国际行为和我们一样,是基于对国际事件的反应。而事实上,中国的国际行为大部分是基于其在国内的安全关切。我认为许多政策制定者都误解了这一点,导致他们对中国领导人的优先考虑缺乏了解,从而制定出次优的对华政策。一直以来,我们更倾向于从国际关系的角度来思考问题,而不是从中国国内政治的重要性角度来思考问题。因此,这并不是一种意识形态,而是一种先入为主的态度,是一种政策的优先排序。一旦我们理解了这一点,我认为我们在如何处理两国关系方面就有了一个更好的路线图。
在阅读了您写的章节:《半个世纪的交往: 中国研究与中国学术团体的作用》,我相信您是接触政策的支持者。您为什么支持这一政策?您认为接触政策的目的应该是什么?
我曾读过一本由(前《华盛顿邮报》驻中国)记者潘文(John Pomfret)撰写的关于中美关系的书(The Beautiful Country and the Middle Kingdom, American and China, 1776 to the Present),讲述了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中美关系是如何经历循环起落的。我不认为中美关系有什么新鲜之处。我们现在正处于这个周期的低点,但我仍然相信这是周期性的,两国关系最终会走出低迷。尽管如此,还是有很多人批评接触战略,说那些一直主张两国进行接触的人是错误的,而现在中美关系的破裂就是证明。
我非常不同意这种评价。一些人首先假定接触的目的是为了改变中国,我认为这在当前的中国研究者群体中是不真实的。研究中国的群体已经存在了五六十年,现在的研究者从他们的前辈身上学到了教训,他们的前辈曾试图改变中国,但却惨遭失败。我认为有两个原因可以解释为什么改变中国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首先,从历史上看,这样的企图几乎总是失败的。其次,从另一方面,中国自身也一直在变化,只是变化的方向不一定是我们所希望或预期的。我认为当代中国学者认识到了这一点,对他们来说,接触的目的不是改变中国,而是了解中国,同时也让中国了解我们。
如今,在华盛顿特区,有很多人说支持接触政策的人在中国问题上十分软弱。这种逻辑表明,对华强硬意味着与中国脱离关系,意味着剥夺我们关于中国的信息,也剥夺中国关于美国的信息。不论是作为一名学者还是作为政策制定者,我都认为我们应该追求更多而不是更少的信息。我认为对接触政策的支持与否与一个人是对华鹰派还是对华鸽派关系不大,它只与是否愿意获取信息相关。我支持接触战略,因为它为我们带来了大量关于中国的知识,并在处理两国关系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能够最有效地处理两国关系的人,至少在美国,是那些了解中国的人。
您是否觉得支持接触政策的学者正在被边缘化?您认为汉学将来有可能在美国消失吗?
当然,我们感到自己被边缘化了。然而,这也让我们的工作变得更加重要,更加有价值。作为一名学者的好处之一是,我并不觊觎任何政治地位。我希望我的贡献在于我的学术、教学和对中国的观察。因此,无论如何,到目前为止,我的贡献基本不受政治氛围的影响。
我不认为中国研究在未来会消失。美国的汉学传统根深蒂固,不可能消失。话虽如此,但中国研究已经变得越来越具有挑战性,尤其是对年轻学者而言。他们获得终身教职、晋升以及在各学科领域扬名立万的所有动力,都取决于他们是否有能力进行实地考察或数据分析,而现在这一切变得越来越困难。因此,人们一直在尝试一些变通的办法。一种是从中国以外的地方研究中国。另一种方法是专注于那些更容易收集到所需数据的学科领域。当然,这样做的问题在于,会扭曲我们对中国的理解。就像观察一只大象,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只是大象的一条腿或一只耳朵,而不是整只大象。
尽管如此,在我最近的中国之行中,我发现中国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同事们非常热情。我能够坦率地与他们谈论我所面临的一些挑战,他们也非常积极地分享了他们面临的许多挑战。他们也对现状感到沮丧,但我们的确在努力寻找向前迈进的解决方案。这是我四年来第一次来中国,但感觉一切都很熟悉。我在那里只待了两周,所以了解得还不够深入,但我确实强烈地感觉到,事情并不像我们这些学者想象的那么糟糕。我想说的最后一点是,尽管面临这些挑战,我们和中国学者都做了一些了不起的工作,比如对于中国国家结构和进程的研究,这不亚于过去的任何成果。如今的研究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需要更多的创新,中美之间的学术合作可能比任何时候都要少,但并没有完全消失。这也是一个充满希望的信号。
您上个月前往台湾观察选举。您认为赖清德当局会对中美关系产生什么影响?
这个问题问得好。我认为要听到赖清德的就职演说才能做出判断。尽管如此,我们看到的一件事是,鉴于中国大陆近几个月对台湾采取的行动,再加上美国对两岸关系潜在的危险的暧昧态度,台湾问题可能会变得越发棘手。我认为,如果中美双方都退一步看看实际情况,同时相互保证不会采取任何偏离现状的行动,都将对目前的局势有益。对我而言,最大的担忧来自 2024 年的美国总统大选。我认为新政府可能会对大陆与台湾交往的动机造成非常不同的影响。我不是在这里显示我的政治立场,但鉴于特朗普最近对北约的评论,以及对美国支持乌克兰政策的持续批评,他的上台可能对台海局势带来变数。
您认为美国国内政治将如何影响台湾问题?
可以想象,台湾在美国国内的政治讨论中会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在美国大力援助乌克兰和以色列时,许多人也将台湾纳入了讨论。很明显,台湾的地位在国内政治的讨论中被抬高,这一点令人担忧。此外,我不确定,如果众议院不是处于目前这种糟糕的状态,是否会有更多的国会代表团前往台湾。我认为,议员们正在将此作为批评政府的国内政治工具,同时也是在向北京挑衅的工具。这些动机是不负责任的。我认为选举后两党代表团与台湾的交流是恰当的,但佩洛西前往台湾,以及麦卡锡在担任众议院议长时调侃要做同样事情的言论,似乎标志着国会过深介入敏感事务这一危险趋势的开端。
您对柬埔寨政治和中柬关系做了大量研究。您认为像柬埔寨这样的东南亚小国在中美竞争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认为柬埔寨作为一个东南亚小国,如果不是因为它的地理位置,它将无足轻重。这也是美国和中国真正的分歧所在。我认为,中国认识到了在东南亚大陆拥有一个可靠伙伴的战略重要性,这将为中国提供通往泰国湾及其他地区的通道。此外,虽然与越南的实力并不对称,柬埔寨也有可能成为中国与越南抗衡的筹码。
遗憾的是,美国并没有东南亚放在优先位置。引用一句老话,“战争是上帝教美国人地理的方式”。 就像我们 50 年前看到的那样,恐怕这种忽视最终会让美国付出相当高的代价。而中国正在我们甚至不选择竞争的地方取得巨大成功。我不会为柬埔寨政权的人权记录,以及他们自 1997 年以来朝着不自由的方向发展的方式辩护,但我们不应放弃与他们打交道。我觉得有点讽刺的是,在东南亚,美国似乎缺乏地缘政治的基因。这正是中国正在利用的东西,任何崛起的大国都会这样做。
作者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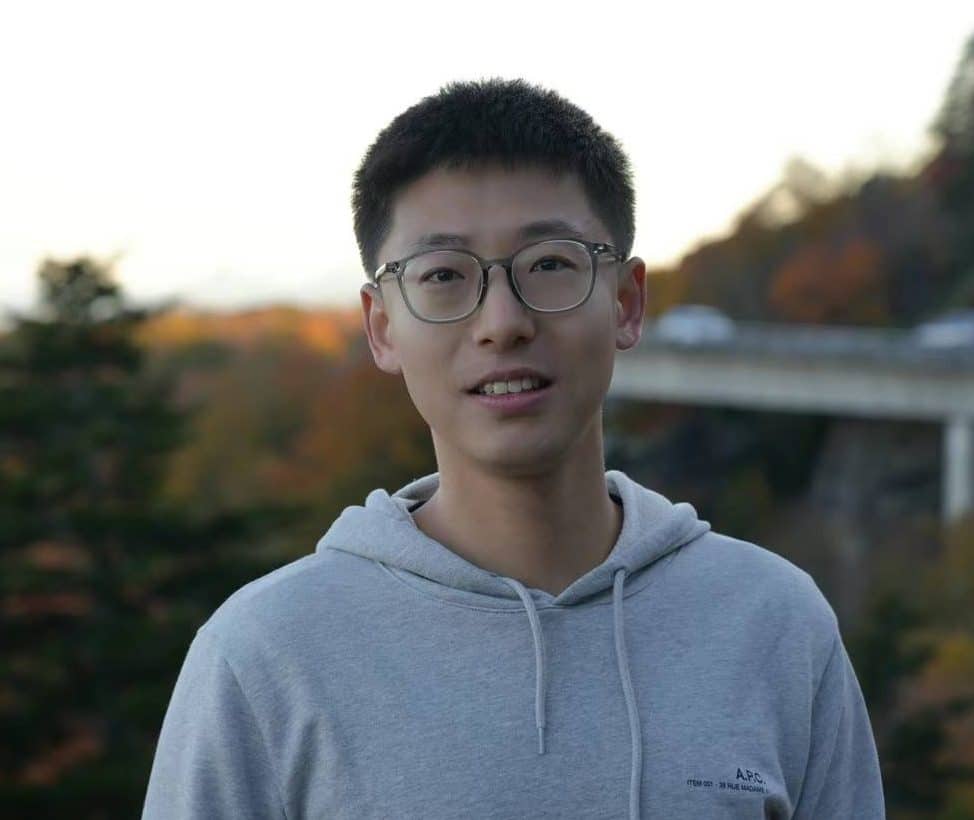
陈必凯 (Bikai Chen) 是卡特中心 China Focus项目助理,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保罗·尼采高级国际研究学院 (SAIS)国际关系硕士。







1 Comment
[…] 阅读全文,请点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