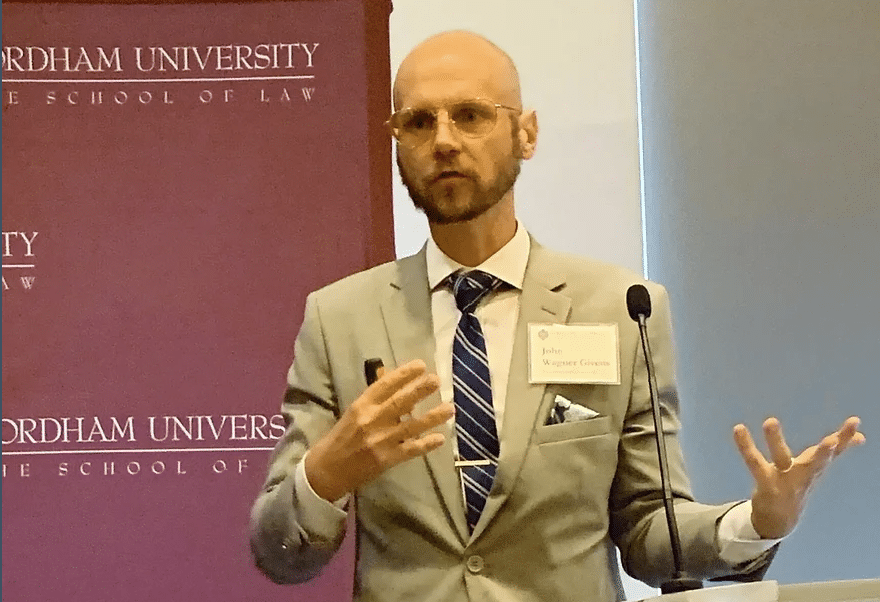杨大巍、薛倩倩:基辛格和他的政治遗产
编者按:本文2023年12月11日由《经济观察报》发表。作者授权本站转载。
延伸阅读:

麦克阿瑟在他的告别演说中引用了军营中流行的一首民谣,作为其演说的结语:老兵永远不死,他们只是悄然隐退(Old soldiers never die. They just fade away)。麦克阿瑟以这种充满了不平凡的平凡语气告别他的职业生涯,为世人留下一个顽强而又有些悲怆的军人形象,将这感人的一幕变成时代的一个定格。
11月29日,在其100周岁之后离世的基辛格,从某种角度来说,正是世界外交领域中永远不死的一位老兵。这位精力充沛,办事果决,决不言败的外交家,离开度过了八年政治生涯的白宫以后,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里,顽强而勤勉,直到生命的尽头仍然穿梭在世界舞台上:在度过百岁生日后的两个月、离世前的四个月,飞跃太平洋,进行了对中国的最后一次访问。
在美国所有的政治家中,基辛格在政治尤其是在外交事务中的影响力之大、之久、之活跃,也许是唯一的一位。美国从第一任总统华盛顿起,离职的总统都渐渐地远离权力,走向归隐的路途。与美国政治家的传统相去甚远,基辛格在离开政坛之后,从未真正退出世界的舞台,在他离世后的短短几天之内,世人对他的生平迅速就了如指掌,媒体争相报导,如水如潮的评论纪念文章,将基辛格的功过毁誉再一次呈现在众人面前。
犹太人基辛格
基辛格是他那个时代在政治上走得最高最远的犹太人,并且还是一位非美国本土出生的、归化入籍的犹太人。1923年在德国巴伐利亚出生的基辛格,在德国度过了算不上是太过悲惨的童年,因为在纳粹执政并且开始疯狂迫害犹太人后不久,由于其母亲的决定,基辛格举家迁至了纽约。基辛格认为,母亲对他来说是最为重要、也是他最为感激的家人。因为她的坚持,基辛格一家才免于惨遭屠杀的命运,而基辛格也得以在这个广阔而充满机遇的新大陆一展身手。
尽管基辛格的家族里有13个亲属被纳粹杀害,给外界的印象却是,基辛格并没有过多地沉浸在那一段痛苦的历史中不能自拔。在回忆他在德国的经历时,基辛格的描述甚至有些轻描淡写。他自幼喜爱足球运动,而这一爱好也伴随其一生。在他开始疯狂爱上这一运动时,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迫害已经开始,而那时的基辛格却仍是经常混入各处观看足球比赛,遭人发现而被痛打,然后遭到驱逐。但第二天他又混了进去,然后是第三天、第四天……如此而往返不已。在叙述这些经历的时候,基辛格并未显得痛苦,而是颇为平和。我们听到更多的是对足球的热爱,而非对生活不幸的陈述。
到达纽约后的基辛格,在22岁那年应征入伍,并被派往德国。当被问及前往德国之时是否带有一种复仇感的时候,基辛格坦承并没有。在德国两年的军队经历,为他赢得了一枚铜星勋章。
对于身世及身份的平和感,或许是因为基辛格早年离开德国之时尚属年幼,而未真正经历随后而至的可怕灾难,又或许是由于他个性强势而试图隐藏内心的痛苦。基辛格的母亲说服其父逃离德国有着一种先见卓识,她的坚定执着和理智个性,大概遗传给了基辛格,并在其职业生涯中起到不可低估的作用。基辛格是那种具有坚强人格、永远往前看的人,他不会扮演弱者或者向外界展示伤痛以博取同情之心。
在一段曝光的录音中,基辛格对尼克松说:“让犹太人从苏联移民到以色列不是美国的外交政策目标,而如果他们在苏联把犹太人关进毒气室,也不是美国关心的问题。它或许是个人道主义问题。”录音令人感到震惊,基辛格被指责为卑鄙和冷酷无情。但是卡利尔(Carllill)博士认为,基辛格是一个非常骄傲的犹太人,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他绝对地把美国利益放在首位,这超越了他的犹太身份,超越了以色列。
犹太人的身份和犹太人的遭遇,在基辛格的生涯中仍然具有影响。基辛格很少谈论过去的不幸,但是那段历史在他的成长之际应该是塑造了他的世界观。希特勒的上台使他目睹了世界如何陷入野蛮和大规模屠杀,这种疯狂对世界造成的混乱和巨大的灾难,成为一种永久的警示,促使基辛格在一生都力求去追求某种秩序与和平。
基辛格是属于特别具有哲学思辩能力的人,他的谈话,他的著述,他的对于世界局势的分析看法和处理,都显示出他的缜密严谨和极富理性。在他感到孤独的时候,他会重新阅读斯宾诺莎(Baruchde Spinoza),在这个17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崇尚理性主义的犹太作家的作品之中,基辛格不仅找到了令其自豪的归属感,也找到了指导其一生认识世界和进行决策的理性基础。
学者基辛格
受益于退役军人权利法案(GIBILL),结束在德国服役、回到美国的基辛格得以进入哈佛大学学习,并在七年间获得了哈佛大学的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就学期间,基辛格对国际事务产生了巨大兴趣,他的分析评判展示了他在国际事务研究方面的惊人才华。他在这一时期发表的博士论文《重建的世界——梅涅特、卡苏尔与和平问题,1812-1822年》,以及稍后发表的《核武器与对外政策》,更是为他赢得了令人艳羡的学术声誉和后来进入政界的入场券。前者塑造了基辛格处理国际事务的基本风格,而后者则成为基辛格对国际局势的看法和处理问题的基础。
基辛格在《重建的世界》中研究了1815年拿破仑战败之后,维也纳体系的建立与维持,对19世纪欧洲的均势学说进行了有见地的评述。基辛格认为维也纳会议之后,欧洲通过协调国际秩序而维持了百年和平,这一难能可贵的和平局势则主要归功于奥地利的外交家梅特涅。由于梅特涅在各国之间的斡旋和努力,使得战胜的欧洲列强并没有对战败的拿破仑法国采取过多的报复,从而达到了国际体系中欧洲各国力量的均衡。基辛格在对梅特涅的研究中建立起了自己的价值观,而梅特涅也成为他日后努力仿照的榜样。在他的外交生涯中,无论是打开中国的大门,遏制前苏联的军事强势,还是停止越战,平息印尼及南美各国的动荡,穿梭斡旋期间的基辛格的身影中,始终都可以看到梅特涅当年的印记。
《核武器与对外政策》研究讨论了美国战略以及对外关系,一经发表,基辛格很快作为核及地缘政治战略家而享有盛誉,成为政治家们手中炙手可热的人物。他首先引起了尼克松的竞争对手、著名共和党政治家纳尔逊·洛克菲勒的注意,并受邀成为其竞选顾问。尼克松赢得大选之后,邀请基辛格加入其内阁,任命他为国家安全委员会顾问。1973年,尼克松又任命基辛格为国务卿。
基辛格具有学者气质。他的一生都在不间断地阅读、思考和写作,直到生命的最后几天,而他的关注点则始终在于人类的命运。上个世纪的50年代,基辛格首先看到了核武器在战争中的作用和对人类的毁灭性打击,在这个世纪,则关注和担虑人工智能对人类命运的影响。他在2023年与埃利森(Graham Allison)合作出版了《通往AI军备控制之路》一书,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还在思考着AI的崛起对人类意味着什么。
外交家基辛格
尼克松入主白宫之际,世界正在目睹美国的节节败退。其时,美国陷于越战已经十年,而战争尽头却仍然是遥不可及。与此同时,苏联正处于进攻状态,建立了庞大的核武器库,并在亚洲、中东和南美各个地区赢得盟友。在国内,美国仍需要从长期的内乱中恢复过来,在这之前,马丁·路德·金和罗伯特·肯尼迪先后被暗杀,100多个城市发生了骚乱。
这种局势之下,基辛格协助尼克松主持了冷战的关键时刻。在执政的第五年,尼克松因水门事件而下台,基辛格则继续担任尼克松后继者福特总统的国务卿。基辛格八年任期结束的时候,世界格局因其努力而发生了变化:越南战争结束了;苏联的军事政治势头因尼克松和基辛格的破冰外交而受挫;北京向华盛顿打开了门户。
在缓和与苏联的军备竞赛方面,基辛格促使美苏达成重要的军备控制协议。在中东,基辛格说服莫斯科的长期盟友埃及驱逐了俄罗斯顾问,转而投向美国。1973年阿拉伯与以色列的战争爆发,基辛格在1974年1月至5月间,频繁穿梭于埃及、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进行调解谈判。这一著名的史称“穿梭外交”,终于促成阿以停火,使得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达成了第一个和平条约,建立了以色列与阿拉伯邻国之间相对和平的关系。
1973年,基辛格最终促使北越和南越之间签署《巴黎和平协定》,为美国从越南的撤军挽回了面子。基辛格由于这一协议的签订获得了1973年的诺贝尔和平奖,与北越领导人黎德寿共同获奖,但黎德寿因基辛格而拒绝了该奖项。在此之前,基辛格被人们谴责为战犯,因为他秘密授意轰炸柬埔寨以断北越供给而造成了数以万计平民的伤亡。
基辛格在许多方面都遭到了谴责。人们谴责他将越战拖得太久,而在1973年签署的协议与他在1969年就可以接受的协议之间没有太大区别;如果不是等到1973年,数以万计的美国人和数十万的越南人、柬埔寨人和老挝人的生命,就能得到挽救。
人们还谴责他在巴基斯坦试图残酷镇压后来成为孟加拉国的叛乱时,对巴基斯坦的支持;他还支持智利军政府的政变推翻民选总统,给美国的声誉留下了很长的阴影。当时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在智利进行了秘密行动,试图帮助反对派团体推翻这个新政府,基辛格主持了授权该行动的委员会。基辛格解释了行动的初衷,“我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要袖手旁观,看着一个国家因为对人民不负责而变成和苏联一样的国家”。他说“这些问题对智利选民来说太重要了,不能由了他们自己去决定”。
基辛格所作的一切当然更是出于美国利益的考虑。在道德与国家利益之间,基辛格永远会选择美国的国家利益。
历史往往需要经过时间的沉淀才能看清其轨迹。智利最终成为一个自由市场的成功国家,在南美经济大规模崩溃之后,智利第一个从经济衰退中走出,至今还是南美经济最为成功的国家。
卸任许久以后,基辛格仍然被视为苏联问题的专家。他以一种更为广阔的和更具历史观的视角看待欧洲的局势,并且始终秉承着均势原则处理苏联和欧洲事务。2015年,当西方试图让乌克兰加入北约的时候,基辛格在《华盛顿邮报》上撰文警告:“西方必须明白,对于俄罗斯来说,乌克兰永远不能只是一个外国。”基辛格指出:“俄罗斯历史始于所谓的基辅罗斯……即使是像索尔仁尼琴和布罗茨基这样著名的异见人士也坚持认为,乌克兰是俄罗斯历史乃至俄罗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基辛格对俄乌关系的评价值得人们的反思。九年多过去了,由于西方对俄乌关系缺乏深刻的了解和谨慎处理,致使巨大的历史性悲剧在俄乌之间发生;而俄乌之间看似无休无止的战争更可能会破坏全球事务的稳定。当然,基辛格认为普京对这场悲剧负有主要责任,但是如果西方决策者具有历史意识和国家利益意识,他们很可能能够避免乌克兰战争。
哈以冲突也使得基辛格担心以色列的长期生存能力。这仍然出于均衡势力的考虑,因为战争越过一定的界限,就可能导致伊朗和俄国的介入,而后果则可能是毁灭性的。一个多世纪以来,基辛格一直都在担心,“破坏性力量一旦启动,很容易撕掉文明和稳定的薄薄外表,将世界推入深渊”。
从1971年秘密访华,并在1972年陪同尼克松完成对中国的破冰之旅开始,基辛格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里访问中国达100多次。这一数字让人惊叹且印象深刻,它成就了基辛格外交生涯中最为醒目、也最为重要的成就。基辛格见证了两个国家之间的协作与发展,更见证了中国在半个世纪里一跃而成世界第二大经济大国。基辛格一生中的大部分成就与中国有关,而中国更是成就了作为外交家的基辛格。
基辛格逝世的消息,在中国引起的反响,比在除美国而外的世界上其它任何地方都要巨大。中国人称赞基辛格为世界著名战略家,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和好朋友。中国官方媒体指出,半个世纪前,基辛格以卓越的战略眼光,为中美关系正常化作出了历史性贡献,既造福了两国,也改变了世界。
基辛格与尼克松
许多时候,尼克松和基辛格的名字往往同时出现,以至于人们很难说清在两个人的政治生涯中,谁对谁起到更大的作用。尼克松和基辛格都极具个性,自我意识强烈。不过两人在许多问题上的看法和主张是一致的,这使得两个同样个性强势的政治家能够成就彼此。历史学家罗伯特·达莱克 (Robert Dallek)在一次接受采访时指出,基辛格的标志性成就是他与尼克松的合作,两个人一起创造了“和平文化”。他们创造了一系列措施,降低了核战争爆发的可能性。
至少是在公开的场合,基辛格总是表现得对尼克松极其尊重。在白宫里,基辛格会用赞誉之词讨尼克松的欢心,而当尼克松沮丧之际,他又能给予安慰和承诺。但是一个极其自负的基辛格对尼克松到底怀有多大的敬意?这多少让人怀疑。水门事件之后,基辛格召集记者泄露了不少内幕,他将尼克松描绘成一个喝醉了的疯子,形容尼克松如何怒火冲天地冲着他大喊大叫:炸了那儿,炸了那儿!基辛格在描述这些情形时,有记者回忆道,带着一种滑稽的、假装悲剧的微笑看着记者说道:“如果我们轰炸了尼克松让我们轰炸的每个国家,那么世界将会是一片光秃秃的土地!”他接着狡黠地说道:“我就说,‘好的,总统先生’,然后就回去睡觉了。”在这里,基辛格不仅略有得意,而且还不无暗示:他是白宫里的那个成年人,是他阻止了疯狂的尼克松做出“炸毁世界”这样的事,以此来彰显自己的角色。
尼克松具有政治洁癖,是个虔诚的基督徒。他的洁癖和自我崇高,致使他在白宫的所有地方都装上了录音装置,以确保日后的政治透明。不过这一措施最终吞噬了尼克松,水门事件发生以后,民主党在录音里找到指证,将尼克松拉下了总统宝座。
正像基辛格在内心里嘲笑尼克松一样,尼克松毕竟也谈不上尊重基辛格。他轻飘飘地称基辛格为我的犹太男孩(My Jew boy),甚至并不信任他。但是尼克松需要借助基辛格的能力去执行白宫的政策。所以从某种角度来说,离开了彼此,尼克松和基辛格都将会是一事无成。
历史对尼克松的不公之处在于,水门事件让尼克松从生涯顶端跌入谷底,而基辛格却因此走向了事业的巅峰。尼克松的使命仿佛就是将基辛格放置于那个聚焦点,成就他的外交功名。基辛格在他与尼克松两个人共同成就的事业中获取了太多的光环。今日提及中美关系的开放和苏联军政势力的受挫,仿佛皆是基辛格一人之所为。但是回顾历史,我们会发现对中国的融冰之旅实际始于尼克松,是尼克松首先看到了打开中国大门的必要性,虽然在意识形态上他曾长期坚定地反对中苏。而在越战停战这一历史事件中,尼克松和基辛格均反对战争,希望尽早能够带领美国走出东南亚的战争泥淖,但是出于同样的好胜心和体面意识,使得越战的结束拖延了三年。
基辛格的政治遗产
基辛格是一个注重实干的思想家,用思想和行动塑造着世界。他固然并不注重讲求道德,但他对全球事务有着当今政治家们所缺乏的深刻理解,他也明白美国力量的投射是有限的,而他的责任则是以有利于美国利益的方式解决全球冲突。
随着基辛格和他的时代的远去,具有他那种严肃性和清晰性的政治家也越来越少。年轻的外交家和政治家们,在这个道德观和世界主义泛滥的时代,完全脱离了自己的国家。许多人倾向于认为地缘政治的观念已经过时,国家利益的概念是一种民粹主义的概念;相比于道德,国家已经变得无关紧要;与维护国家的利益相比,这个时代更愿意对抗全球贫困以及防止全球变暖。
基辛格受到来自全球的赞誉和敬重,同时也受到同样多的指责和抨击。基辛格的支持者们认为他继承了梅特涅的传统,是现实政治的实践者:利用外交来实现实际目标,而不是推进崇高理想。他们认为基辛格促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军事力量和政治力量之间的均势,将随时可能发生的热战变成为冷战,给世界带来一定时间的和平,这种务实倾向符合美国的利益;而基辛格的批评者们则认为,基辛格的做法与民主理想背道而驰,他的外交实践造成了柬埔寨、老挝、智利、孟加拉等国无数平民的伤亡,是一名沾满了受害者鲜血的战犯…… 确实,基辛格将实用主义与对美国国家利益的追求结合起来,在这一追求中,做出了许多道德上令人反感的行为,比如为了消除当时苏联在南美的影响,基辛格宁愿支持一个军政府,所以他在1970年与中央情报局合作破坏智利民选社会党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并最终推翻他;又在1976年热情支持阿根廷1976年的血腥政变,敦促阿根廷武装部队在西方对侵犯人权行为的强烈抗议之前迅速消灭对手。许多人包括希拉里,在年轻的时候都曾走上街头抗议过尼克松和基辛格,但希拉里在成为国务卿之后就转变了看法,开始认可基辛格的外交思想和实践。
基辛格的一生都在为捍卫美国的最大利益而努力着。美国不仅为他提供躲避纳粹德国的庇护,而且宽容地将他推至权力的最高层,为他提供了成为伟大政治家的机会。基辛格少年时期在纳粹德国的经历,使他对秩序与和平充满了渴望。他曾多次表示,如果必须在正义与混乱和不公正与秩序之间做出选择,他总是会选择后者;因为一旦混乱,正义就不可能实现。
基辛格对在复杂的世界中追求国家利益有着极其清晰的认识。他将自己描述成一个孤独的牛仔,引领着一群坐在马车上的、对路程茫然无知的旅人,走进城镇,走进村庄,走进西部。他认为这种孤独感正是他自己最形象的写照。“一位伟大的领导者能够带领一个国家到达它需要到达的地方,即使其人民没有意识到他们需要到达那里”。
基辛格的好友兰斯·莫罗(Lance Morrow)注意到基辛格有时会现出短暂的、令人惊讶的表情:焦虑、困惑、惊慌甚至是恐惧。他关于基辛格和他的朋友巴克利的一段描写与感受让人怅然却若有所悟:“那天晚上,在长岛岸边,船上的灯在逐渐变暗的夜色中闪闪发光……就像约瑟夫·康拉德 (Joseph Conrad)《黑暗之心》(Heart of Darkness)的开场场景。巴克利和基辛格让我想起康拉德笔下经验丰富的航海家,他们是老朋友,曾以某种方式‘沿着大海航行’。黄昏时分了,一艘停泊在泰晤士河上的巡航小艇,他们聚在那里谈了一个晚上的话。‘一条通向大海的水道’,正如康拉德所写,‘到达地球的尽头’”。
兰斯让我们隐约窥见到,在世界的中心有一种人类无法看清的黑暗,正如康拉德所描述的非洲的腹地,这其中有着鲜血、贪婪、屠戮和毁灭,但也产生出崇高与和平。这一窥见是令人不安的,尤其是对于那些对这个世界有着清晰认识、同时又有着明确而坚定的人生信念的人来说,更是如此。基辛格其实对此有过类似的陈述,他在回忆录中谈论尼克松时写道:“在内心深处,人们永远无法确定尼克松身上令人不安的事情是否也反映了自己内心某些被压抑的缺陷。”
基辛格所成就的一切,他的一生闪闪发光的履历和他冷静沉着的行为背后,似乎有一种幽暗而深不见底的惶惑、羞耻和痛苦,一种属于人类的惶惑、羞耻和痛苦。
作者
-

杨大巍是旅美政治评论家,中国《经济观察报》专栏作家,《中美印象》特约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