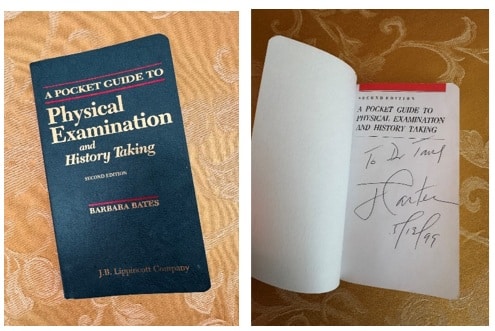人口递减:中国不可避免的挑战
作者:明克胜-文|徐宇深-编译
2023-01-27
【编者按】明克胜 (Carl Minzner)是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中国研究高级研究员 ,福德汉姆大学(Fordham University)法学院教授,著有《改革时代后的中国》等研究中国政治的专著。他曾担任美国国会与行政部门中国委员会的务高级顾问,并曾在中国西北政法大学担任 “耶鲁-中国” 法律教育研究员 。本文“中国遏制人口递减的努力是徒劳的”(China’s Doomed Fight Against Demographic Decline)2022年5月发表于美国外交学会的杂志《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2023年中国公布2022年人口统计数字后,文章又一次引起中国问题学者的关注。
中国社会的人口危机是一个值得研究与思考的问题,它呈现了追求现代化转型的传统社会解决社会和经济问题的一个侧面。 除此之外,作为发展中人口大国,中国的人口发展模式更是集约化全球生产下产业转型升级的缩影。劳动力与住房价格上涨、教育时长增加、高校总体水平的下降,都无疑都加重了中国 “未富先老” 的结构性问题。中美对抗和经济脱钩的局势更对中国人口现状造成前所未有的挑战。而在后现代视域下,中国和世界各国都面临一个问题:生育是否完全属于个人意志领域? 如何解决个人自由与社会国家-人类繁衍义务之间的矛盾与冲突? 这是一个事关文明延续的重大问题。
中国迅速老龄化的社会和急剧下降的出生率为其领导人带来了一系列困扰,包括劳动力的减少和日益不稳定的养老金体系。为了减轻这些风险,北京正在稳步转向支持生育主义政策,以此作为减轻这些风险的战略。 2016年,中国政府取消了严厉的独生子女政策,并于2021年开始出台旨在积极鼓励生育的政策。 然而,中国东亚邻国的经验表明,此类措施对于提高生育率并无帮助。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主张重新接受传统的性别规范,它出台的政策可能使中国妇女的权利倒退几十年。这一变化将使导致中国出生率下降的情势进一步恶化。
中国政府目前应该改变自己的政策走向:消除歧视妇女的意识形态,接受人口递减的冷酷现实,并通过提高退休年龄、削减不可持续的养老金承诺以及为老年人,特别是中国贫困农村人口中的老年人设计更好的护理体系来解决老龄化的后果。如果中国现在不采取这些措施,不仅它的人口问题会更加严重,它还将面临巨大的政治和社会风险。
以下是为明克胜文章的中文编译。
破灭的中国婴儿潮
1949 年后,中国人口迅速增长。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在公共卫生、预期寿命和婴儿死亡率方面取得了快速改善,人口在三十年间几乎翻了一番,从1949年的 5亿4千万人增加到 1949 年的9亿6千9百万。20 世纪 70 年代,中国当局开始担心人口过剩会阻碍经济增长。 他们起动了一项旨在敦促夫妇少生孩子的人口计划(晚、稀、少 )。之后, 生育率急剧下降,从 1970 年每名妇女生育 5.8 胎到 1978 年的 2.7 胎。
1979 年,官员们将上述努力强化为一项全国性的强制性计划生育制度,即独生子女政策。 中央计划制定者设定了生育配额,这些配额与经济增长的目标一样,是中国官员政绩评估的主要标准。 实现配额为当局控制其管辖范围内的生育创造了强大的动力, 一些官员为了政绩达标甚至诉诸强制绝育或强制堕胎。 更常见的是对违反计划生育的违规行为严厉罚款,罚款数额有时相当于普通公民多年的工资。

从 2000 年开始,中国学者开始表达对这些政策导致的长期人口影响的担忧,包括作为选择性堕胎的结果的男女性别比失衡。 正如人口学家王峰指出的那样,“中国对低于更替生育率和人口快速老龄化的政策反应异常缓慢。 中国官僚体制的惰性和特殊利益集团的反对使得中国政府的领导人在2013年前对这些警告充耳不闻:最高权力机构的政治共识与核心政策转变直至2013年才出现,以至于从 “单独二孩” 到“全面放开生育”,再到”鼓励生育三胎”的转变耗费了整整八年时间。
中国官员最初认为仅仅终止长期的计划生育政策就能提升妇女的生育率,然而,事与愿违,中国的出生率持续下降,并在2021 年跌至大饥荒年份以来的最低水平。 中国官方的总和生育率(TFR)已经下降到 1.3。 专家测算真实的数字更接近 1.1,与东亚其他快速老龄化社会的统计相当。这些数据不仅远低于北京的乐观假设,甚至低于最保守的联合国低生育率模型。 人口下降的速度之快迫使官方大幅修改了对于中国老龄化速度的估算。 2016年中国政府预计中国总人口要到2030年才会开始下降,但现在这个转折点可能最早在今年到来。
冗长的学术论证与缓慢的政府反应都使北京采取的应对措施为时已晚。伴随着2021年夏季实施的鼓励三胎政策,北京取缔了整个营利性教辅产业,它们被认为是增加生育成本并导致生育率下降的原因之一。除此之外,数十个省份积极推广带薪产假、延长产假时间、减免个人税收、发放生育奖金和其他财政激励等方式,希望以此鼓励生育。
生育率暴跌
其他东亚国家已经尝试过中国目前正在推行的许多相同政策,但这些国家的出生率一直再世界的最低水平徘徊。
1989年,日本妇女的生育率降至1. 67胎,大惊失色的日本政府随后出台了最为慷慨的育幼政策。本世纪初,台湾和韩国妇女的生育率也掉至同一水平,双方政府也马上推出育儿优惠政策。为了促进人口增长,新加坡政府推出的激进手段不仅包括政府组织的相亲活动,还有专门优待已婚夫妇的公共住房政策。
这些雄心勃勃的措施都无关紧要。 在普遍缩减的全球生育率下,东亚社会的出生率降低程度很容易受到忽略。 它们不仅远低于每名妇女生育 2.1 胎的更替水平,俄罗斯等其他老龄化国家也是如此(1.8),德国 (1.6),或意大利 (1.3) 。 香港、澳门、新加坡、韩国和台湾是全球最低的,徘徊在 1.0 左右。 韩国的生育率低得惊人,妇女平均生育率为 0.81 胎。 相比之下,即使是老龄化的日本在 1.37 时也显得非常多产。
高昂的住房成本和对额外教育年限的需求促使全球年轻人推迟结婚和生育,或者干脆放弃。然而,正如台湾学者 Yen-hsin Alice Cheng 指出的那样,保守的社会价值观在东亚扮演着特殊的角色。 冰岛和美国分别拥有70%和40%的非婚生新生儿,而台湾、日本和韩国的非婚生新生儿占比为 4%、2% 和1.5%。中国与其邻国一样严苛的非婚生育禁忌,与其不断下降的结婚率一道,导致东亚的生育率跻身世界最低之列。

东亚结婚率和生育率下降的背后体现出了性别角色期待、传统婚育伦理的影响:它们使许多国家提高生育率的努力步履蹒跚。 瑞士和日本都拥有最好的带薪陪产制:在2019年,休产假的瑞士父亲有90%,而在日本,仅有 7.5% 父亲休产假。这一事实说明,如果人们不接受,鼓励生育政策就毫无价值;如果生育奖金不能解决人们对于婚姻和生育的根本顾虑,那它就毫无意义。 尽管社会主义国家一直提倡两性平等,但性别期待继续影响着中国女性的生活。
【译者评论: 除了性别角色期待与婚姻伦理,对同性恋的歧视也是东亚国家出生率大幅度下降的原因之一。不容忽视的是,在东亚地区,只有台湾宣布同性婚姻与同性伴侣家庭受法律保护。对同性婚姻与同性恋家庭的拒斥限制了同性伴侣的生育意愿,进一步限制了东亚各国的人口增长潜力。】
阻止人口滑坡
北京目前的计划类似于台北和首尔大约 15 年前的修补计划——这些政府当时认为促进生育的刺激举措可能会扭转本国的人口增长颓势,但事与愿违。中国同样面临阻碍东亚其他国家政府采取的那些措施的挑战。 2021 年,中国的婚姻数量跌至 36 年来的最低点 。大约44%的年轻城市女性和 25% 的男性不打算结婚。 性别角色期待更是女性恐婚恐育的重要原因。
奇怪的是,中国应该是最有能力解决性别问题的国家,这一问题是导致东亚超低生育率的核心。中国共产党正是通过拥护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而上台执政的。执政者颁布的第一个法律《婚姻法》就规定结合自愿并允许妇女自由离婚。因此,从理论上看,人们可以模糊地设想20世纪的中国走上类似于北欧的道路。在北欧,包括单亲家庭、未婚伴侣、同性关系、平等的性别规范以及针对母亲和父亲的灵活休假政策都为生育率做出了贡献,使其达到了发达国家中最高的生育率水平。然而,中国并未成为本应最有能力解决人口问题的国家;与之相反,一系列以牺牲女性权利为目的的政策正在恶化中国的人口危机。
中国正在背离其社会主义遗产:Leta Hong Fincher等学者详述了 1978 年后的市场改革和北京对维护社会稳定的关注造成了巨大的性别歧视,妇女权利受到严重侵蚀。传统性别范式,污名化非婚生育行为的社会观念,司法和制度性不公,都加剧了中国的低生育率。一方面,将家庭责任归于女性的传统性别角色观念,驱使女性被迫在个人发展和家庭义务之间做出选择。另一方面,未婚伴侣和非婚生家庭为传统价值所不容。比如,一些地市至今都限制未婚母亲享受生育保障。
自2012年开始,中国近年来在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复古倾向,推崇生育自然主义,神圣化婚姻与家庭价值,并试图恢复父权文化道统。与此同时,执政叙事同样高度弘扬女性的家庭属性,优先强调女性的婚育责任。2021年,根据当局发布的讲话汇编,中国领导人援引中华帝国的早先论调,强调 “女性的特殊职责” 是 “(作为)贤妻良母,相夫教子” 。执政党的言辞经常呼吁将中国特色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进行结合,中国古典哲学家语录成了官方辞令。
上述意识形态倾斜也体现在具有决定性的政策转变方面: 中国通过增加个人的离婚难度和成本,稳步转向反对离婚。 Xin He、Ke Li和Ethan Michelson等学者记录了中国法官面对女性离婚请求时减少的批准意愿 。本世纪初,中国法院批准了 60% 的离婚申请, 批准率目前已经下降到大约 40%。申请人撤回离婚申请的撤回率也从从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的 5% 上升到今天的 25% 以上。

执政党强调家庭和谐与社会秩序的严厉要求也促使法官在判决中牺牲妇女权益。在离婚和子女抚养权这类案件中,男方的暴力抗诉手段也使法官更容易实施上述判决。对法官而言,迫使妇女撤销离婚请求,放弃子女抚养权,放弃离婚,被迫忍受家庭暴力要更为容易。国家法律也在变化:出于对离婚率上升的担忧, 长达30天的 “离婚冷静期” 于2020年正式生效。作为结果,离婚总数急剧下降,从 370 万(2020 年)下降到210万(2021 年)——在一年内就下跌了43%。
中国的治理模式可能会导致中国政府把人口的增长作为一项政治要求,甚至提出明确的生育目标,并将其纳入地方官员的绩效评估体系,并追踪那些在其辖区内实现达到1.5的年度TFR的官员的职业生涯。 这些举措远非假设:在过去的独生子女政策期间,北京就是这样管理反生育主义的人口计划的。
如果中国继续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它很可能会经历与独生子女政策相称的政策滥用。 2021年政府十年计划中对于 “限制非流产”的措辞”可能演变成对女性身体自主权的新限制(美国的平行趋势)——但这一次,是为了诱导她们生育孩子,而不是禁止她们这样做。 2022年,一名鼓励研究生一毕业就生育的人大代表引发了中国网民的“群嘲”——但这可能逐渐演变为降低法定结婚年龄和限制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阴谋。
更好的方法
人口急剧递减,中国何去何从?
现在,北京陷入窘境:一方面,像东亚国家一样,将大量社会资源投入以扭转生育率难以扭转中国的人口前景;更糟糕的是,在“振兴中华”的愿景下,迅速恶化的人口状况加剧了政策错误的风险,将家庭、婚姻和生育进一步重新政治化。 前者会浪费宝贵的资源;后者会使性别问题倒退好几代人,使政府与中国年轻人,尤其是女性对立,并最终加剧导致中国生育率进一步下降的潜在因素。
因此,提高退休年龄、完善养老系统、放弃无法实现的养老金承诺,吸纳移民并允许外国劳工协助养老——尤其是针对中国农村贫困人口,才是北京应当考虑的举措。然而,这样的改革困难重重。中国试图提高退休年龄的方案一直没有被通过,减少退休福利的计划更因为担心激怒退休干部和城市精英而寸步难行。
尽管如此,如果中国政府把目前的困难交给未来的政府去解决,结果只能是积重难返,引发更大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