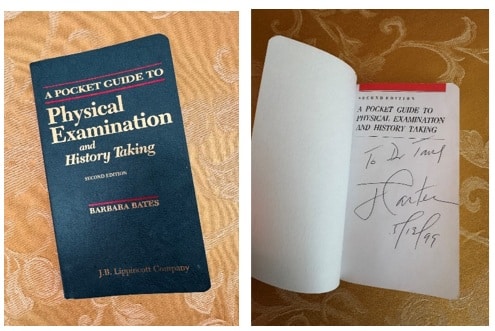佩蒂斯:中国经济模式令其发展陷入僵局
作者:vera
2022-10-10
编者按: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金融学教授Michael Pettis(迈克尔•佩蒂斯)于《外交事务》(Foreign Affaris)杂志发表了题为“中国经济模式令其发展陷入僵局”(How China Trapped Itself: The CCP’s Economic Model Has Left It With Only Bad Choices)的文章(点击阅读全文),提出中国的高投资发展模式使中国承受了高额负债,面临艰难的转型选择。佩蒂斯认为在振兴房地产市场以刺激经济增长和增加基础设施支出之间,中国政府选择了后者。他预测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模式难以长久维持,中国不得不接受减少投资后经济增长放缓的结果。
随着至关重要的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于本月召开,中国领导层将不得不面对几十年来最艰难的一系列经济选择。中国目前面临着令其进退维谷的经济僵局:一方面,中国可以选择摆脱其已施行愈四十年的、为其创造大量财富的经济增长模式,尽管这一模式在过去十年间令中国社会付出了不平等加剧、债务激增、投资浪费上升的代价。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可以选择在未来几年内维持现状,继续推行目前的经济模式,直到现行的经济模式所要付出的代价令其不堪重负,届时中国政府将面临更加艰难的经济转型。
德裔美国经济学家阿尔伯特·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曾在几十年前预测中国如今面临的问题。赫希曼指出,所有快速增长都是不平衡增长,一个成功的发展模式是不平衡增长解决并扭转经济中现有的不平衡。但随着这些情况的逆转和经济的发展,这种模式与最初的一系列失衡越来越不相干,最终开始产生一系列截然不同的问题。
这就是今天的中国。中国的高投资发展模式旨在解决中国巨大的投资不足,但在近半个世纪之后,这种发展模式使中国面临投资率过高的问题。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投资通常占全球GDP的25%左右,较成熟经济体的投资占17% – 23%,处于高增长阶段的发展中经济体的投资占28% – 32%。但是,在过去的十年里,中国每年的投资额相当于其国内生产总值(GDP)的40% ~ 50%。中国必须大幅降低这一异常高的水平,但由于其经济增长已高度依赖投资,在不大幅放缓整体经济活动的情况下,这一目标恐怕难以实现。

债务危机
对中国来说,高投资率并不总是坏事。20世纪70年代末,在经历了内忧外患的五十年之后,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时代。当时中国在基础设施、物流和制造能力方面的投资严重不足,它最需要的是一个将快速投资放在首位的发展模式。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中国采取的高投资模式令经济蓬勃发展。首先,中国政府强制提高了为投资提供资金所需的国内储蓄占GDP的比例。在任何经济体中,储蓄指的是所有生产出来但未被消费的资产。因此,提高储蓄占GDP的比例意味着降低消费占GDP的比例。中国政府通过系统性地限制家庭收入占GDP的比重来做到这一点。家庭收入是一个国家除企业和政府收入外的收入途径。但与企业和政府不同的是,家庭消费占据了家庭收入的大部分,因此家庭收入在GDP中所占的份额越小,消费所占的份额就越低,储蓄所占的份额就越高。
到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国内储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达到50%,达到了有史以来任何国家的最高水平。银行系统是中国储蓄的主要中介,它以政府设定的人为低利率为中国企业、房地产开发商和地方政府提供了巨额储蓄。其结果是高水平投资推动的快速增长,这令中国投资不足的问题得到了有效解决。但是,与其他遵循类似模式的国家一样,中国也面临着一个隐藏的陷阱:一旦中国缩小了其资本存量水平与工人和企业能够有效吸收的水平之间的差距,它需要转向一种不同的增长战略,不再强调投资,转而关注消费。投资不足的差距可能在至少15年前就已经消除了,但与此同时中国的债务负担开始迅速上升。
这一债务危机并非“一日之寒”。通常情况下,当一个经济体将大量债务用于生产性投资时,其GDP的增长很可能超过债务的增长,该国的债务负担就会保持在较低水平。但是,当债务被用来为经济效益低于劳动力和资源成本的投资(被称为“非生产性投资”)提供资金时,债务开始比GDP增长更快。中国的债务负担在2006年至2008年前后开始激增,从那时起,中国的官方负债率已经从GDP的150%上升到近280%——这是任何一个国家都经历过的最快增长之一。债务负担上升的主要来源是中国房地产行业的私人投资,包括出于投机目的购买的满是空置公寓的大楼,以及地方政府对过剩基础设施的投资,如过于雄心勃勃的铁路系统、未充分利用的公路和高速公路,以及大型体育场和会议中心。
尽管房地产和基础设施行业对中国经济活动的贡献如此之大,以至于对地方精英来说,它们在政治上变得非常重要,但经济政策制定者越来越担心,他们要重新控制债务的唯一途径是限制这两个行业的非生产性投资。但由于近年来这些支出占了中国GDP增长的一半以上——在经济特别困难的时期,这一比例远远超过了一半——要在不导致经济活动大幅下降的情况下限制这些支出几乎是不可能的。
泡沫破裂
去年,监管机构终于在解决债务激增问题上迈出了重要的第一步——他们决定通过提高负债最重的房地产开发商的借款难度,来打击杠杆率。但是,由于房地产部门占所有经济活动的20%到30%,房地产的任何急剧收缩都将不可避免地迅速自我强化,并导致整个经济活动大幅放缓。在去年对房地产业借贷的打压之后,金融危机蔓延到其他经济领域的程度出乎人意料。对地方政府来说尤其如此,土地出让是地方政府收入的最大单一来源;因为土地销售是其最大的单一收入来源;对家庭来说,他们突然开始担心房价不会无止境地上涨;对直接和间接受到房地产行业破产影响的企业来说也是如此。
随着人们对中国经济放缓速度的担忧日益增加,中国政府将不得不以有限的方式作出回应。一个选择是回到由债务推动的快速增长时代,要么试图恢复房地产行业,要么通过大幅增加基础设施支出来弥补其下降。地方政府一直渴望,几乎是不顾一切地振兴房地产市场,但如果购房者对中国房价可以持续上涨的预期被破灭,那么这一振兴计划也将付诸流水。更重要的是,中国地方官员似乎非常不愿意回到过去的经营方式,即开发商承担巨额债务,为投机性的新项目融资。由于中国住宅房地产的价格大约是美国可比水平的三倍,而且房地产行业在整个经济活动中所占的份额如此之高,大多数经济政策制定者长期以来一直希望看到市场降温。更有可能的情况是,中国政府将通过增加基础设施支出,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房地产市场放缓和收缩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北京方面似乎已经愿意走这条路,并已告知地方政府,它们必须加快或增加基础设施支出计划,或者两者兼而有之。
中国政府的第二个选择是,通过经济再平衡,越来越多地向消费倾斜,以保持高速增长。至少从2007年以来,中国政府一直在努力做到这一点,但要增加消费支出,就必须提高家庭收入占GDP的比重。换句话说,普通民众将不得不以更高的工资、更高的养老金、更多的福利等形式从经济产出中获得更大的份额,而这意味着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将不得不牺牲其部分GDP份额。这样的调整在政治上极其困难。与任何国家一样,中国的政治权力分配在一定程度上是经济权力分配的结果,两者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牵一发而动全身,收入分配再平衡也许会发生,但从其他国家的历史经验看,这一转型的实现极为困难。 最后,如果中国政府决心现在就采取行动,控制不可持续的债务增长,而又无法实现经济再平衡,那么第三个选择就是允许GDP增速大幅下降,即可能降至3%(甚至2%)以下。如果处理得当,这种下降的大部分成本将落在部门而不是家庭,所以这对普通人来说不会有太大影响,但它确实意味着中国经济整体增长放缓,特别是国家机器的增长。近三十年来,中国的投资在GDP中所占的比重一直处于历史最高水平,但太多的投资流向了那些创造经济活动(和债务)、但不能创造真正经济价值的项目,而如今这一现状难以为续。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唯一的选择是迅速减少投资,并接受增长大幅放缓的后果,或者通过强制持续的高投资率来维持高水平的增长,直到由此导致的债务负担激增,使其难以或不可能保持在这条道路上。换句话说,无论如何,中国的经济增长都将大幅放缓,而这种放缓的方式将对中国、中国政府和全球经济产生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