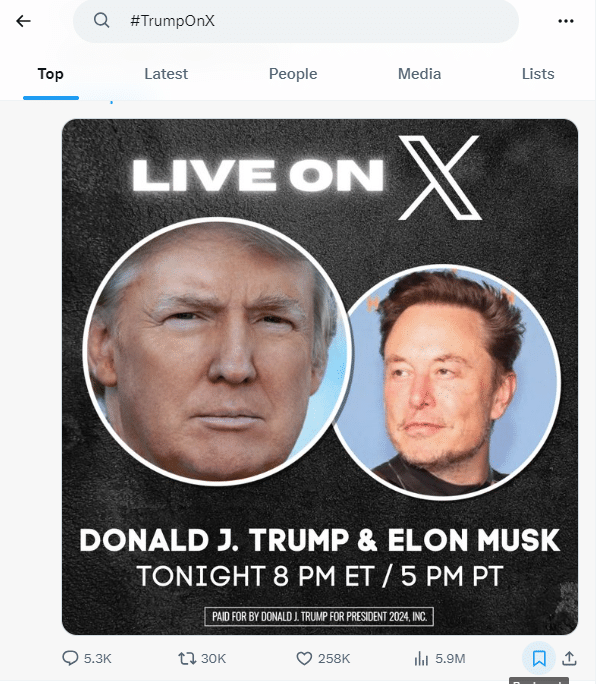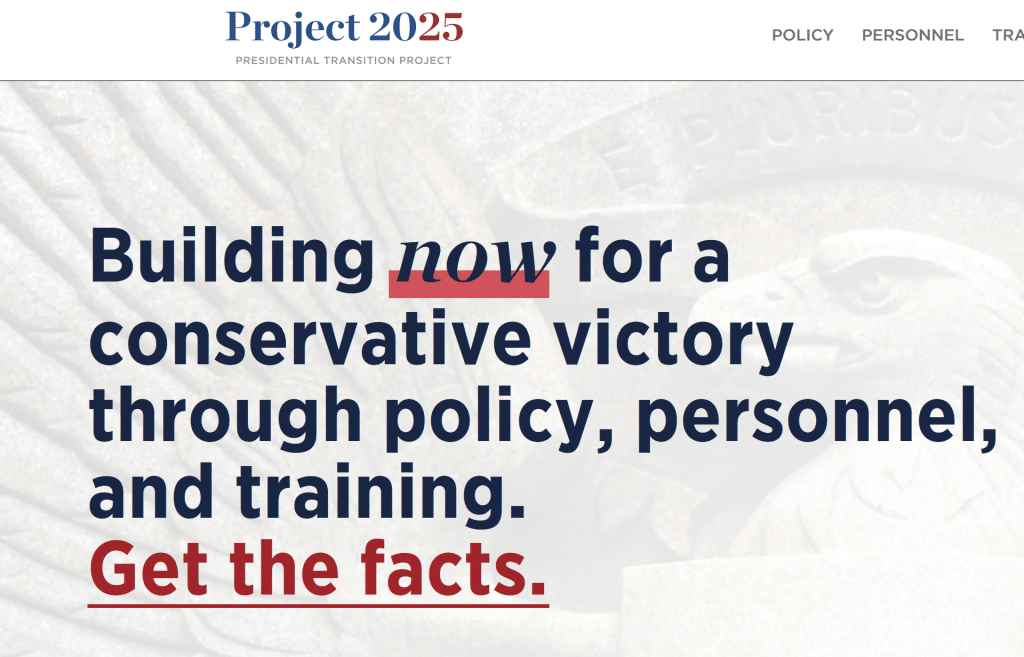王希:民权运动如何改变了美国?
作者:王希 来源:作者赐稿
民权运动如何改变了美国?
How did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Change the United States?
王希
Indian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大家好。感谢刘亚伟教授、王开元博士的邀请,有机会再次来到大学沙龙的线上讲座,我感到很高兴。尤其感谢李洪山教授来做点评。我们是多年的老朋友,曾在留美历史学会共事多年,我相信他的点评一定会像上次洪朝辉教授的点评那样精彩,发人深省。7月24日讲座之后,有听众来信,与我分享看法,并提供资料,在此我向他们表示感谢。
我上次讲的时候(王希:最新的联邦假日与美国的两次“重建”(上)),企图覆盖的内容过多,时间没有把握好,“第二次重建”的题目未能展开,应听众的要求,再讲一次。今天我就以民权运动作为讲座的重点,主要讨论如下几个问题:(1)民权运动为何发生?(2)民权运动是如何进行的?它的参与者、领导者是谁?(3)民权运动的结果是什么,如何改变了美国公民权利的享有以及美国本身?如果时间允许,我会结合《1965年移民和国籍法》——这也是民权运动的成果之一——讨论亚裔美国人与非裔美国人的“相同的和不相同的历史”。
民权运动的概念
“民权运动”(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指的是什么?简单地说,它指的是20世纪50、60年代由非裔美国人发起和领导的一系列争取平等权利、平等法律待遇的群体性公民抗争运动的总称。在这场运动中,抗议者采用大规模的、由普通黑人参与的、非暴力的直接抗争方式,挑战南部各州的种族歧视法律法规,迫使联邦政府出面干预,从司法、执法和立法三个方面采取行动,废除美国公民和公共生活中的种族歧视。民权运动的最初目标是为非裔美国人争取平等权利,但运动得到了白人主流社会和其他族裔群体的同情、支持与参与,最终转化成为了一场为所有美国人争取权利的运动,给20世纪的美国带来了一场“权利革命”(rights revolution),不仅激活了“沉睡的”宪法权利,恢复了非裔美国人被剥夺的权利,而且还创造了为所有美国公民享有的新权利。
我想先与大家分享的两个观点:第一,没有民权运动,就没有今天所有美国公民和在美国生活的外国移民所享有的权利和法律待遇的平等,而非裔美国人是这场运动的先驱和主力,是主要的组织者、参加者和领导者;第二,民权运动虽然发生在20世纪中叶,但在它发生之前已经有无数的美国人——尤其是非裔美国人——为之做了大量的准备和铺垫工作,在组织动员、意识形态建构、抗争战术测试、运动骨干培养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所以民权运动的发生并不是偶然的或一蹴而就的。那么,为什么会发生民权运动?为什么民权运动会在20世纪中期的美国发生?早期有何铺垫?国内和国际形势起了什么促进作用?更重要的是,民权运动为什么最终能够获得成功?这是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问题。
种族隔离时代的希望与抗争
许多历史学家把“民权运动”称作“第二次重建”,为什么?最主要的原因是,民权运动在宪政思想与实践上与内战后的重建(“第一次重建”)是一脉相承的。重建(1863-1877)是美国历史上的一次“伟大的宪政革命”,是美国国家建构和民族建构进程中的一次关键的转折,也为后来的美国历史发展设定了至今尚未完成的政治议程。第十三(1865)、十四(1868)和十五条(1870)宪法修正案分别废除了美国境内的奴隶制,为美国公民建立在法律上平等的公民资格和公民权利,禁止各州剥夺美国公民的权利,禁止各州拒绝给予美国公民以“平等法律保护”(equal protection of the laws)的待遇,还将选举权赋予给黑人男性公民,开创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跨种族民主”的实践。我在《原则与妥协:美国宪法的精神与实践(增订版)》(2014)中曾经指出,贯穿于美国历史的两大政治主题是“权力宪政”(constitutionalism of power)与“权利宪政”(constitutionalism of rights)。内战前的美国政治主要围绕联邦与州政府的“权力”的界定与分享而展开,内战后的政治史则主要围绕“权利”——谁享有权利,以及谁应该享有什么权利——而展开。民权运动既是关于权力的,也是关于权利的,起点都始于重建。
重建虽然是一次宪政革命,但它未能进行到底。1877年 “激进重建”结束之后,南部白人重新掌握了州政府的权力,通过公开和变相的手段,推翻了许多重建建树,在南部的公共生活中实施种族隔离、将黑人选民排除在选民队伍之外。到19世纪末,南部黑人的大多数处于经济上贫困、政治上无权、公共生活中无尊严的地位。什么原因导致了重建的失败?历史学家有许多讨论,总结出多种原因,包括经济重建的缺失,共和党内部的分裂,联邦政府的软弱无能,南部白人的“白色恐怖”(white terror),联邦最高法院的保守主义以及黑人内部缺乏有效、稳固和独立的领导力等。
并非所有的重建建树都被推翻。在救赎(redemption)时代,经济上,大部分南部黑人并不拥有土地,但许多人利用内战后劳动制度的改革,成为了分成租佃农(sharecroppers),部分地控制了自己的劳动时间,获得了某种独立性。有的人(尤其是居住在佛罗里达州的黑人)还获得了土地。在教育方面,州公立教育体系虽然受制于种族隔离制度,但仍然在运行。内战后建立的一批黑人院校(Historically Black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在北部慈善机构和教会的资助下得以保存,培养出第一代黑人专业人才,包括律师、牧师、教师和大学教授等。1900年,黑人中小学教师人数已经达到将近3万人,黑人院校达到了34所,有2000多名黑人获得了大学学位,他们成为了第一批黑人中产阶级的成员。
南部黑人也没有放弃对尊严、正义和权利的追求,他们内心深处仍然燃烧着重新获得失去的权利的强烈愿望。但他们的愿望需要被点燃,黑人大众需要被组织起来,形成一种改变自己命运的洪流。争取重获权利,需要建立基层组织,需要拥有意志坚定、具有感召力的领袖人物,还需要有白人社会的合作,而且抗争必须是在美国宪政体制的框架下进行,并且得到国际社会的同情与支持。所以,重获权利的任务艰巨而负责,参与抗争的人——无论是领袖人物还是普通大众——都需要有足够的信心、耐心、智慧和牺牲精神。换言之,民权运动的发生是在20世纪中叶,但其力量的培育、思想和经验的创造与积累却是在半个多世纪前就已经开始。黑人大迁徙、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成立、哈莱姆文艺复兴等为此做了早期的铺垫。
黑人大迁徙、NAACP的成立与哈莱姆文艺复兴
从重建结束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之前,美国用40年的时间完成了从农业国家向工业化国家的转型,站在了世界工业强国的前列。高速的工业化带来了美国国内在经济结构、人口分布和区域政治力量等方面的重组。黑人人口分布的改变便是这一进程的结果之一。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南部乡村地带的黑人——尤其内战之后出生的一代人——为北部的工业化所吸引,开始移居到北部、中西部和西部的新兴工业城市,更多的人则从乡村地带移居南部城市之中。这场被称为“大迁徙”(Great Migration)的黑人人口转移进程一直持续到20世纪中叶。仅1900年至1920年间,就有约50万南部黑人移居北部和西部城市。1890年,美国黑人的90%居住在南部乡村地带,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全国约三分之一的黑人已经居住在北部和南部的大城市里。1980年,五分之四的黑人人口居住在城市,而且大多集中在大城市里。黑人人口的城市化对改变20世纪美国黑人的命运、种族关系和美国政治发展都有重大影响。与我们讲题相关的是,“黑人大迁徙”为民权运动在20世纪中叶的发生奠定了人力资源的基础。民权运动是一场以都市人口为基础的群体抗争运动,黑人人口的城市化是运动发生和得以持续展开的前提条件。
如同内战前的“国内贩奴贸易”(internal slave trade)对“棉花王国”的兴起产生了巨大影响的情形一样,“黑人大迁徙”也将黑白种族关系的紧张与对立带出了南部,带到了北部、中西部、西部的城市之中。大量黑人移民的到来,不仅扩大了城市中的黑人社区,而且对白人劳工的就业形成了竞争的压力,也导致地方和城市政府、社区等在住房与公立教育方面制定出针对黑人(和有色人种)的种族歧视规定,歧视程度甚至超过了南部。随着种族歧视与种族隔离蔓延到南部以外,黑白社区的冲突在全国不同城市的频繁发生。在20世纪初美国城市发生的种族骚乱中,1908年发生在伊利诺伊州的斯普林菲尔德(Springfield)的骚乱最为严重。骚乱发生在“伟大解放者”林肯的故乡,它带来的震撼因而特别大。1909年,为了回应这些令人震惊的针对黑人的种族冲突,一群黑白改革者共同发起组建了“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the Colored People,简称NAACP),呼吁开展一场新的废奴运动以废除美国生活中的种族歧视。NAACP的宗旨就是,恢复重建宪法修正案的活力,开展合法斗争,为黑人争取宪法保障下的平等权利。它的早期策略是法庭斗争,即借助联邦法院对各州和地方的种族歧视法进行挑战。协进会的成员吸引了相当一批普通黑人,但它的成员多为黑人和白人人口中的中产阶级成员、知识分子、律师、教师等。著名的黑人学者杜波伊斯担任NAACP官方杂志《危机》(Crisis)的主编。杜波伊斯也是最早提出利用重建宪法修正案来合法争取民权的黑人知识分子,他的社论在黑人读者中有广泛的影响力,《危机》也成为早期民权运动的宣传阵地,NAACP则是最早的全国性民权运动组织。
黑人大迁徙和NAACP的建立带来了另外一个结果,即将一批黑人知识分子、艺术家、作家、教育家等从美国各地和海外带到了纽约,催生了“哈莱姆文艺复兴”(Harlem Renaissance)运动。在此之前,一些黑人知识分子和精英已经开始组织起来,如在19世纪末杜波伊斯等人建立了“美国黑人学院”(American Negro Academy)和“尼亚加拉运动”(Niagara Movement),布克·华盛顿(Booker T. Washington)等建立了“黑人商业联盟”(Negro Business League),但这些组织多为专业性较强的组织,其影响力在普通黑人人口中十分有限。哈莱姆文艺复兴虽然也是带有“精英”色彩,但它却具有更为强大和宽广的传播力量。20世纪初,来自各地的黑人艺术家和作家聚首纽约曼哈顿的哈莱姆区,通过自己的文学和艺术创作,表现黑人的内心世界,展示“新一代黑人”(New Negro)的思想,讲述黑人的历史,创造黑人的艺术,为后来非裔美国人文学和艺术的兴起起到了重要的奠基作用。“新一代黑人”深知,一个没有历史和传统的民族,无法在内部建立认同感,也无法得到外部的认同。他们将黑人文化的重建视为自己的使命,他们的文学和学术创作为培育黑人的“文化意识形态”和身份认同产生了重要的作用。我们也可以将哈莱姆文艺复兴视为一种黑人内部的“精神重建”运动。我在这里与大家分享由原籍牙买加的黑人诗人克劳德·麦凯(Claude McKay)在1919年创作的一首诗,从中感受一下“新黑人”的精神气质——绝不接受任人宰割的命运。
“If We Must Die” (1919)
By Claude MaKey
If we must die—let it not be like hogs
Hunted and penned in an inglorious spot,
While round us bark the mad and hungry dogs,
Making their mock at our accursed lot.
If we must die—oh, let us nobly die,
So that our precious blood may not be shed
In vain; then even the monsters we defy
Shall be constrained to honor us though dead!
Oh, Kinsmen! We must meet the common foe;
Though far outnumbered, let us show us brave,
And for their thousand blows deal one deathblow!
What though before us lies the open grave?
Like men we’ll face the murderous, cowardly pack,
Pressed to the wall, dying, but fighting back!
黑人领袖关于抗争策略的早期探索与辩论
即便在种族压迫最残酷的时代,黑人领袖也没有放弃对重获平等权利的途径的探讨,并在内部进行过激烈的争论。1895年,19世纪最著名的黑人领袖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去世,在亚拉巴马州塔斯基吉学院担任校长的黑人领袖布克·华盛顿被视为新的黑人领袖,受邀在亚特兰大世界博览会会上讲话。华盛顿主张南部黑人的当务之急不是挑战种族歧视制度、争取享有平等民权和社会权利,而应该是致力于学习基本的工业和商业技能,与南部白人和谐相处,用诚实劳动赢得白人社会的尊重。他认为,经济上的独立自主比起争取民权更重要。他的这种“迁就”和“顺从”(accommodating)南部种族隔离现实的立场遭到了杜波依斯等人的反对。杜波依斯认为,黑人受歧视的根源在于政治权利被剥夺,无法平等参与公民生活,因此也得不到尊重。他认为,黑人不应忍气吞声,接受二等公民的地位,更不能放弃争取权利和接受与白人同等的高等教育的努力,否则黑人将永远处于美国社会的最低端,无法获得真正的解放。
其他的黑人领袖则在不同的方面探索抗争的方式。黑人女记者艾达·威尔斯(Ida B. Wells)单枪匹马地在20世纪初发起了一场反对南部私刑的活动。当时私刑是南部白人时常使用的一种非法手段,私刑案件在南部频繁发生,受害者多为黑人。威尔斯冒着生命危险,四处收集事实,记录私刑的发生,并将骇人听闻的私刑事实公之于众,要求国会立法禁止私刑。另一位黑人女性安那·库珀尔(Anna Julie Cooper)则强调教育对于改变黑人命运的重要性。她指出,黑人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光靠外界的“阳光和雨露”远远不够,必须在黑人的内心播下改变自身命运的愿望的种子。黑人历史学家卡特·伍德森(Carter G. Woodson)在20世纪初开启了整理和研究黑人历史与文化传统的工作,创办了《黑人史期刊》(Journal of Negro History),反击主流学界认为黑人无历史的说法。来自牙买加的黑人移民马库斯·加维(Marcus Garvey)1916年移居纽约后,组建了黑人组织(Universal Negro Improvement Association, UNIA),提出“黑人民族主义”(black nationalism)的口号,主张在黑人内部建立一种世界性的互助经济网络,争取经济自立。社会主义者菲利普·伦道夫(A Philip Randolph)是早期黑人工运的领袖,组织了第一个全国性的黑人工会。瑟古德·马歇尔(Thurgood Marshall)在1930年代中期从霍华德大学法学院毕业,随后加入NAACP的律师团队,他在后来的法庭斗争中将扮演最重要的角色(并在1967年成为第一名在联邦最高法院担任大法官的非裔美国人)。
这一部分内容是经过大大压缩的。我的目的是想说明,上述这些代表了黑人领袖们在不同时期和不同环境下对斗争策略的探索。需要指出的是,在早期,黑人领袖内部始终未能建立起一个统一的领导核心力量,他们与主流政治接触的渠道也是非常有限的。但20世纪上半叶国际形势将改变美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重新界定美国的国际地位,而这些将为黑人争取重获权利带来新的机会。
20世纪上半叶的国际战争与美国国际地位的改变
从1898年到1945年,美国经历了几次重要的外部战争——包括美西战争(1898),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和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45)——这些战争对美国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转型意义。美西战争时间不长,但它标志着美国放弃了奉行一个世纪之久的孤立主义外交,加入到帝国主义扩张的潮流之中。美国卷入一战的时间不长(1917年才参战),但却在战后获得了帮助制定战后国际秩序的强国位置。真正将美国变成世界性强国的是二战和二战之后的冷战。二战结束之际的一系列涉及国际政治(联合国)和经济秩序(世贸总协定、世界银行和布雷顿森林体系)是美国成为西方世界领袖的标志。美国的商业利益也随之成为了一种与世界经济进程密切相连的利益。美国利益的“世界化”带来的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是,种族问题不再是一个“国内问题”,而演变成一个“国际问题”。在冷战初期,黑人领袖很快意识到,在美国与共产主义阵营在国际上争夺人心的竞争中,美国国内的种族问题成为了美国对外关系的一种“负资产”。
国际战争在另一方面也对国内的种族关系带来了冲击。一战期间有40万黑人公民应征入伍,参加美国军队,前往欧洲作战。他们在欧洲领略了新的国际主义。参加二战的黑人军人的人数更是高达100万人,其中有50万人前往欧洲和亚洲和作战。如同内战一样,战争为非裔美国人的抗争带来了机会,一方面黑人士兵希望通过参战表示对国家的忠诚,希望以此换取白人主流社会对他们的尊重;另一方面,从军和在海外作战的经历也使一些老兵具有了“国际意识”,其中一些人后来也成为基层民权运动的参加者和领袖人物。1942年,在匹兹堡出版的黑人报纸《匹兹堡信使报》(Pittsburg Courier)曾发表一封读者来信,信中提出黑人应该力求在二战中同时争取“双重胜利”(double-v):在国外战胜法西斯主义,在国内战胜种族主义。由此可见,国际形势也激发普通黑人的政治自觉意识,推动他们将国内与国际政治联系起来。
罗斯福、杜鲁门执政时代的“权力”与“权利”的博弈
自重建起直至20世纪30年代,非裔美国人在政党政治中长期站在共和党一边,因为在当时的南部民主党扮演的是一个保守的、代表白人至上主义思想的角色。当南部黑人被剥夺了选举权之后,南部几乎成了白人民主党的“一党制”天下。然而,当南部黑人移居北部和中西部城市成为当地选民之后,全国的政治版图也相应发生变化。共和党本身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也发生了转型,逐渐成为与大资本、职业工会结盟的政党,而北部民主党则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转型过程中逐渐成为与都市中下层、移民和都市黑人结盟的政党。20世纪上半叶,因为黑人都市力量逐渐增强,黑人政治家开始在北部城市参加竞选,并获得了一定的成功。早期的民权运动组织,如城市联盟(Urban League)等也在北部得以建立,开始培训运动骨干,尝试不同方式的抗议活动——从法庭斗争到拒乘种族隔离的公车等。这些活动不能不引起民主党领袖的重视。
1933年民主党人罗斯福在就任总统后,为应对经济大萧条带来的空前危机,利用总统权力,实施新政,力图挽救美国资本主义。他任用了一批黑人知识分子和领袖担任联邦政府的高级官员,并时常在种族问题上听取他们的意见,故有“黑人内阁”(black cabinet)之说。联邦政府也雇佣了大量黑人。这些举动赢得了黑人对罗斯福的好感,而新政所表现出来的政府干预经济、保护和调节人民权利的做法更让黑人记忆起重建时期自由民局所发挥的作用。1936年总统大选中,北部的黑人选民集体转向支持民主党,推动了当时美国的政党重组(realignment)。显然,黑人领袖开始认识到,经济危机和二战极大地扩大了总统的权力,而这种权力是可以被利用起来挑战盛行于各地的种族歧视法律的。他们同时意识到,二战和美国国际地位的改变也提供了给总统直接施加压力的机会。
1941年,黑人领袖菲利普·伦道夫进行了第一次尝试。他计划发起一场“为争取工作进军华盛顿”(March on Washington for Jobs)的示威活动,声称要组织10万黑人到华盛顿示威,要求改变美国工业就业中的种族歧视状况。虽然此刻美国还没有直接卷入二战,但罗斯福不愿看到这场示威活动的发生。他希望伦道夫取消示威计划,但伦道夫拒不让步。最终罗斯福签署了《第8802号总统行政命令》,要求所有接受联邦政府国防合同和经费的工业、企业将其就业机会平等地向所有人开放,禁止这些企业以肤色、种族或民族血统为由对有色人种进行歧视。伦道夫的施压取得了成功,也为后来的民权运动提供了一种可行的抗争模式——利用执法部门的权力渠道。对于许多黑人来说,罗斯福的行政命令他们带来了希望,并让他们记忆起内战时代林肯颁布的《解放奴隶宣言》。
二战和冷战的意识形态也为后来民权运动的发生提供了思想资源。二战期间,罗斯福提出了著名的“四大自由”(Four Freedoms)的口号——强调美国人拥有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以作为美国与专制、极权国家的区别。当联合国于1945年成立时,美国“全国黑人委员会”不失时机递交声明,要求联合国关注黑人在美国受到的歧视,在“黑人问题”国际化方面迈出重要一步。事实上,瑞典经济学家贡纳尔·米尔达尔(Gunnar Myrdal)在1944年出版的著名的关于美国种族关系的调查报告《美国的困境》(An American Dilemma)中就已经发出警告——如果美国不能解决国内的“黑人问题”(即黑人公民没有享受到平等的公民待遇),它就无法成为具有道德感召力的“民主”世界的领袖。
1946年,杜鲁门总统任命的民权状况调查委员会在其报告中列举了种族隔离给美国在政治、经济和国际形象方面造成一系列的伤害,并提出这一现象令美国难以向亚非拉有色人种盟友国家说明“我们思想和体制的长处”。1948年,杜鲁门建议国会及早建立一个永久性的民权管理机构,保证所有美国公民的宪法权利都得到保护,因为“美国目前在世界上的地位要求联邦政府承担这样的责任”,也因为“世界人民目前正面临着对自由或奴役制(两种制度)的选择”,“如果我们希望激发那些自由遭到了危险的人民,如果我们希望恢复那些已经失去了自由的人民对自由的期盼,如果我们希望实现自己的承诺,我们必须改正我们现行的民主中的不完美之处”。同年,杜鲁门签署了《第9981号总统行政命令》,宣布废除美国军队中的种族隔离制度。当然,他这样做也是有选举政治的考量——他希望争取北部黑人的选票,但他的行动为民权运动的到来创造了有利的政治气氛。
由此我们看到,在20世纪中叶民权运动开始之前,已经有大量的铺垫、探索和积累。虽然这些活动与后来的民权运动没有组织和体制上的直接联系,但它们提供了思想、组织和战术资源。国际形势的变化、总统权力的扩大以及种族问题的国际化也都营造了有力的抗争环境。正是在这种背景下,NAACP从30年代起加速推动法庭斗争。
NAACP的法庭斗争
自1910年正式建立之后,NAACP一直锲而不舍地涉及投票权、住房种族限制和使用公用设施方面的种族歧视案例带入州和联邦法院,对种族歧视州法提出挑战。在NAACP的压力之下,最高法院也有限度地做出了有利于黑人权利的判决。在1915年吉恩诉美国案(Guinn v. United States)的判决中,最高法院宣布俄克拉荷马州一项限制黑人选举权的州法中的“祖父条款”违反了第十五条宪法修正案。1917年,最高法院在布坎南诉沃雷案(Buchanan v. Warley)的判决中,将肯塔基州路易斯威尔市的一项居住隔离法宣布为违宪。1948年,在居住区种族隔离的问题上,最高法院通过哈德诉霍吉案(Hard v. Hodge)和谢利诉克莱默案(Shelley v. Kraemer)的判决表示,虽然居民盟约属于个体公民之间的行为,不受州法管制,但不能借助州的法律机器去实施,州也不能从司法程序上予以支持,如果州介入了这种盟约的实施和执行,该盟约就变成了州的行为,就必须受到第十四条宪法修正案的制约。1941年的米切尔诉美国案(Mitchell v. United States)涉及到一个黑人乘客乘坐火车时遭到拒绝的事件,最高法院认为州制定的隔离乘车法是对联邦州际商务管理权的侵犯。1946年,在摩根诉弗吉尼亚州案(Morgan v. Virginia)的判决中,最高法院宣布弗吉尼亚州种族隔离乘车法为非法。 但这些判决的影响甚小,未能触动南部种族歧视法律体系的根基。
从1930年代起,NAACP开始选择高等教育领域作为突破口,采用的策略是“以毒攻毒”,即启用第十四条宪法修正案,用“平等法律保护”的原则来挑战奉行“隔离但平等”(separate but equal)原则的州法,要求州在实施种族隔离时做到在提供隔离设施时的“绝对平等”(absolute equality),从而增加州的财政负担,让其无法承受实施种族隔离的经济成本,最终被迫放弃种族隔离的实践。从1936年到1950年,NAACP分别通过1938年盖恩斯诉卡纳达(Missouri ex rel. Gaines v. Canada)案,1948年赛普尔诉俄克拉荷马大学董事会(Sipuel v. Board of Regents of University of Oklahoma)案,1950年斯韦特诉佩因特(Sweatt v. Painter)案和麦克洛林诉俄克拉荷马州(McLaurin v. Oklahoma State Regents)案,迫使联邦最高法院推翻了南部高等院校对黑人学生的种族歧视政策。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展开讲每一个案例的故事,只是略为总结一下它们的要点。在盖恩斯案中,最高法院宣布,州不能以为黑人学生到外州法学院去上学而支付学费的方式来解决种族隔离造成的“不平等”;在赛普尔一案中,黑人女学生赛普尔拒绝到临时拼凑的黑人法学院就学,因为提供的条件不平等,最高法院表示赞成。在斯威特案中,NAACP的律师认为黑人法学院与白人法学院的“无形因素”(intangible factors)不平等——要做到“绝对平等”,必须让两个种族的学生上同样的法学院,最高法院支持了这一立场。
在这些案例中,最有后续影响力的是1950年的麦克洛林案。该案的主角是一位黑人教师,他到俄克拉荷马大学学教育学博士学位,因为前车之鉴,大学录取了他,但当进入学校之后,他去遭遇了在校内的种族隔离——即他的所有行动(包括听课)都是在与白人学生隔离的状态下进行。最高法院将大学的做法宣布为违宪,理由是:
我们的社会正在变得日益复杂起来,我们对于经过良好训练的、未来的领袖的需要也将更为迫切。这个案件正是充分表现了这种需要,因为他(原告麦克洛林)是在争取获得一个更高的、能够指导和教育他人的学位;他本人接受的教育必然要影响那些将来要成为他的学生的人;如果麦克洛林与他的同学所接受的教育是不平等的话,那他的未来的学生在教育与发展上也将不可避免地受到伤害。由州强制实施的这种〔对麦克洛林在校内实行种族隔离教育〕的政策将产生这种不平等,最高法院对此不能容忍。
这份判决提到的两个观点——教育在现代美国的重要性,种族隔离教育给受歧视者带来的伤害——给NAACP的律师们带来了极大的启示。应该说,这是他们在自己的起诉文献中首先提出的观点,现在得到了最高法院的承认。NAACP做出了一个大胆决定,将反种族隔离教育的斗争推向涉及千家万户的中小学公共教育领域。1954年的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 of Topeka)成为理想的案例。
布朗案的判决及其意义
布朗案也非常有意思,我也没有机会展开讲。该案实际上一共包括5个案件,分别选自南卡罗来纳、弗吉尼亚、堪萨斯、特拉华等州和哥伦比亚特区,都涉及黑人中小学生在就学、学校设施等方面因肤色不同而遭受的不平等待遇。当这些案件在联邦低等法院和州法院审理时,NAACP的首席律师瑟古德·马歇尔(Thurgood Marshall)和他的同事大胆使用了当时一些黑人和白人教学心理学家对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后果所作的社会调查结果。这些调查资料显示,强制性的种族隔离教育对黑人学生的自尊心造成了极大伤害,致使黑人学生感到自卑,不喜欢自己的肤色和长相,甚至产生了下意识的“自憎”(self-hatred)感。在每个案件的审理中,马歇尔和他的同事们都邀请心理学家或教育学家出庭作证,说明隔离教育给黑人学生造成的难以修复的心理伤害。马歇尔的这一策略非常成功,NAACP在法庭使用的调查资料最终将成为最高法院判决书的一部分内容。
第二次法庭辩论之后,最高法院新任首席大法官厄尔·沃伦(Earl Warren)深为马歇尔的雄辩所打动。为了保证最高法院的判决有足够的分量,沃伦运用了他极为擅长的斡旋技巧,耐心地说服几位对取消隔离教育持反对态度或犹豫不决的大法官。最后,最高法院终于以9-0票的一致意见作出决定:宣布种族隔离教育违宪,推翻了1896年普莱西案(Plessy v. Ferguson)建立的“隔离但平等”的原则。沃伦在布朗案的判词中几乎直接借用了麦克洛林案判决关于教育与公民素质培养的说法。他宣布说:
当今,教育可能是州和地方政府最重要的功能之一。强制性的就学法律和巨额的教育花费都说明我们充分认识到了教育对我们民主社会的重要性。教育是我们履行基本公民职责(包括服兵役时)的基本条件,是(培养)优秀的公民品质的最重要的基础(the very foundation of good citizenship),是唤醒一个孩子对文化价值的认知、辅佐他为以后的职业训练作好准备以及帮助他正常地适应他所面临的环境的一种主要工具。在当代,我们怀疑,当一个孩子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机会时,他还能有机会(在社会中)获取成功。(所以)接受教育的机会是一种权利,这种由州负责提供的机会必须平等地向(本州内)所有的公民提供。
他接着说,如果因为“仅仅基于种族和肤色的原因,将少数民族的学生从与他们年龄和资格相同的其他学生隔离开来,将使被隔离的学生对自己在社区中的地位产生一种自卑感,这种自卑感将对他们的心灵和心智造成一种不可修复的伤害”,而这种伤害得到了现代社会科学研究的证明,因此“隔离但平等”的原则不能在公共教育中实施,因为“隔离的教育设施本身就是不平等的”。
布朗案的判决具有深远的影响,可以说是直接发出了启动民权运动的邀请——虽然这完全不是最高法院或沃伦大法官的最初意愿。判决推翻了最高法院在1896年做出的决定。最高法院大法官之所以最终能作出这样的决定,是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没有基层黑人群众的勇气,没有有色人种协进会的黑人和白人律师的精心策划和在法庭上有理有节的斗争,没有众多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和他们的研究成果的支持,没有类似沃伦对政治问题的敏感和对美国社会前途的关切,布朗案不可能获得成功。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布朗案本来是宣布中小学教育中的种族隔离是违宪的,但它却宣示了一项新的公民权利——平等接受州立教育的权利,这是以前不曾有的一项公民权利。
民权运动的第一阶段
布朗案判决对民权运动的来临无疑是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两者在形式上非常不同——一个是联邦司法部门的行动,一个来自南部基层的群体运动——并不存在体制上的逻辑联系,但在政治目标和原则上是相交的。布朗案判决,与它之前最高法院的一系列相关判决,与罗斯福、杜鲁门的总统行政命令和类如城市同盟等早期组织的抗争活动等,都是民权运动的铺垫和基础。虽然这些早期的事件与民权运动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体制联系,但它们为民权运动的发生做了思想、组织、意识形态和人员的积累和准备。换言之,民权运动的发生不是偶然的,它与NAACP在目标、策略、战术和意识形态上是有密切关系的,而NAACP后来也都深深卷入民权运动之中。
如果以1955年蒙哥马利市的“拒乘公车”(Montgomery bus boycott)为起点,以1968年马丁路德金的遇刺为重点,在13年的时间里,美国出现了数十次甚至上百次的群体抗议和示威活动,我们将这些活动总称为“民权运动”。关于民权运动,我觉得有几点观察值得注意。一是民权运动绝非只是“街头抗议”,还有发生在立法、司法、政治选举和“社会正义”(social justice)等领域的一系列改革;二是民权运动最初所要求的不是新的公民权利,而是第十四条宪法修正案所建立的“受平等法律保护”的权利,但最终民权运动的结果远远超出了最初的目标;三是民权运动的发生的确有些突如其来,但在起步之后,群体抗议迅速蔓延开来,在不同的南部城市展开,新战术、新参加者、新领袖人物和新民权组织连续涌现,并在最终由各个组织构成了一种协调式的、资源共享的领导者同盟,前期发生的运动为后来的运动提供了经验、战术和组织力,后面的运动吸引了和培养了不同背景的参与者,所以整个运动呈现一种动态之中。为说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一下一些标志性的抗议运动以及他们之间的某种联系,从而理解整个民权运动所包含的多样性、复杂性、艰苦性和创造性。
1955年12月黑人妇女罗莎·帕克斯(Rosa Parks)在亚拉巴马州蒙哥马利的公交汽车上拒绝给白人乘客让座——按当地种族隔离乘车法,当公车上人满为患时,坐在后排隔离位置上的黑人乘客必须给白人乘客让座绝让座——遭到逮捕。在年轻牧师马丁路德金的组织与动员下,蒙市的黑人群众举行了一场长达380天的拒乘公车抗议活动。他们采用的抗议方式是非暴力抵制,拒绝乘坐公车,改用步行。因该市公车乘客的70%是黑人,他们拒乘公共汽车,使公车系统面临瘫痪,经济损失严重,最终最高法院宣判该市的隔离乘车法违反了第十四条宪法修正案,必须废除,抗议取得了胜利。
从表面上看,这场抗议活动是因为帕克斯的偶然行动引发的,但其实不然。在帕克斯拒绝让座之前,蒙市的妇女民权组织早已在准备挑战种族隔离乘车法,而帕克斯本人也曾经担任过当地NAACP分部领导人的秘书,参加过非暴力抵抗的训练。年轻的牧师马丁路德金虽然刚到蒙哥马利市,但他拥有教会的黑人成员,并熟悉公民不服从的思想与策略,能够很快担任起领袖的角色。金在运动之后,提出了“非暴力的大规模直接行动抗议”的思想,随后成立的南部基督教领导同盟(Southern Christian Leadership Conference, SCLC)由南部城市的教会领袖组成,一个新的运动模式因此而诞生:运动有了新的参加者——普通黑人群众,新的抗争方式——大规模的和非暴力的群体抵制,新的领袖人物——马丁路德金等,新的政治语言——争取作为一个美国公民的权利,还有新的组织——SCLC等。运动的结果是联邦最高法院寻求法律裁决,而最高法院所依据的是第十四条宪法修正案的“平等法律保护”原则。一个旧的宪法原则通过一个新的抗争方式得以启用。
这样,蒙市运动提供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抗议活动的逻辑和程序——从抗议理由、抗议方式、参加者、领导者和最终的法庭诉讼——都得以建立,并能作为一种可以操作的规范用于其它城市和环境。后来的标志性运动——包括1957年的小石城高中(Little Rock Central High School)黑白学生合校运动、1960年北卡州格拉斯伯勒的“入座抗议”(Glassboro sit-in)、1961年的自由乘车(Freedom rides)和1963年的伯明翰儿童十字军抗议等,基本上都是沿用这一运动模式和逻辑,但具体实施的规模和力度不一。而这些后来的运动,也都加入了自己的特色。譬如,在小石城合校抗争中,地方民权运动的组织者挑选9名黑人男女高中学生进入白人学校,遭到州长派遣的州国民警卫队的阻止。9名黑人学生遭到白人群众的围攻与谩骂,联邦法院发出的合校命令被州政府忽视,艾森豪威尔总统不得不下令,调遣美国军队空降兵101师(这支部队二战期间曾率先在法国诺曼底登陆)前往小石城,履行护送黑人学生入校上课的责任。艾森豪威尔曾经有些后悔任命沃伦担任首席大法官,但作为总统, 他不能无视地方和州政府无视联邦法律。他的行动延续了他的两位民主党前任(罗斯福、杜鲁门)开创的总统介入的做法。北卡州的“入座抗议”活动则将黑人大学生带入到运动中了,催生了学生非暴力联络委员会(Student Nonviolent Coordinating Committee, SNCC)的诞生,这是一个主要由大学生参与的民权运动组织,在运动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1961年的“自由乘车”运动则启用20世纪40年代由城市联盟(Urban League)发起的跨州乘车战术,选用勇敢的黑人和白人积极分子一起行动,要求联邦司法部介入,以管理“州际商务”为由,挑战南部地方的种族隔离乘车法。
在1963年的伯明翰“儿童十字军”示威中,马丁路德金通过黑人教会,组织起数百名黑人儿童参加反种族隔离的公共行动,当城市警察动用高压水龙头冲击游行者时,各大电视网中断了正常节目,实况转播警察对黑人抗议者施暴的场面。警察狼犬扑向孤立无援的黑人儿童的画面产生了巨大的震撼效果,完全印证了金的预想:北部各地的白人纷纷行动起来,举行呼应性的抗议活动,要求联邦政府出面干涉,采取有力行动,废除南部的种族隔离制度。这些事件也由国际媒体广为报道,产生了极强烈的国际效应,当时的苏联和中国报刊也都对此作了大量报道。最后,肯尼迪政府不得不出面干预,迫使伯明翰取消种族隔离制度。
《1964年民权法》
1957年和1960年,在艾森豪威尔执政期间,国会通过了两部民权法,都是以保护公民的选举权为目标,并没有涉及公共生活中普遍存在的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问题。而南部黑人因被其他的方式(如人头税,文化水平测试,白人预选)剥夺了选举权,无法参与州和地方政府的决策,而白人主导的政府在排除黑人参与的情况下不可能主动废除种族歧视的法律。所以,联邦干预的力度成为一个立法障碍。1963年6月,肯尼迪总统向国会提出了一份新的民权法草案。他将民权问题看成是一个道德问题,敦促国会立即采取行动,以免让解决民权问题危机的机会从“理性的和负责任的人民手中错失,而使危机转到施用仇恨和暴力的人手中”。肯尼迪此话不是没有道理,当时南部的三K党死灰复燃,攻击和暗杀民权领袖的事件时有发生,黑人内部也出现了主张以暴力对暴力来反对种族歧视的倾向和组织。1963年11月,肯尼迪在达拉斯的遇刺显然帮助扫除了国会内对肯尼迪提议的新民权法的阻挠。1964年6月,新的民权法由继任总统林登·约翰逊签字后生效。
《1964年民权法》是一个内容广泛的旨在全面禁止种族歧视的法律。此法共有7个部分,主要内容包括:(1)全面禁止在包括旅馆、饭店、戏院以及所有从事州际商业的公用设施里实行以种族、肤色、宗教和民族血统为理由的歧视行为(第二部分),禁止州和地方政府以上述理由拒绝给予任何人使用上述公用设施的权利(第三部分);(2)继续强调废除公立教育中的种族隔离(第四部分);(3)扩大和增强依据《1957年民权法》建立的民权委员会(Civil Rights Commission)的权责范围(第五部分),(4)禁止任何接受联邦资助的项目、机构和企业实施种族歧视(第六部分),禁止任何从事州际商务和接受联邦资助的企业、商业和项目以种族、肤色、宗教、性别和民族血统和性别为理由对雇员进行歧视(discrimination based on race, color, religion, sex and national origin)(第七部分)。这里我们看到这部民权法覆盖的范围非常宽泛,使用了“经济制裁”的手段来禁止各种歧视行为,不光是种族和肤色歧视,也包括性别、宗教和血统歧视,不光是在使用公用设施,而且在就职、就业、就学和接受联邦政府的资助等方面。所以这是一个力度非常大的民权法,不仅巩固了前期运动的成功(废除公立教育中的种族隔离),也实现了民权运动的主要目标(废除公共设施使用中的种族隔离和歧视),而且还创造了新的民权(在就业和接受政府资助时不因种族、性别、宗教和民族血统而遭受歧视)。
民权法实施后刚四个月,最高法院便接到对民权法质疑的上诉案件。在1964年的亚特兰大之心汽车旅馆诉美国(Heart of the Atlanta Motel v. United States)案的判决中,最高法院所有大法官无一例外地对《1964年民权法》表示了支持。最高法院称,国会有权在州际商务中禁止种族歧视,为过往旅客服务的汽车旅馆(如亚特兰大这家汽车旅馆)自然在此之列,应受到管制。从而宣布民权法合宪。由此也可看出,第十四条宪法修正案和州际商业(interstate commerce)管理权仍是联邦政府制定和实施民权法的宪政基础。
争取重获选举权的运动与《1965年选举权法》
在《1964年民权法》成为法律之前,许多民权运动领袖已经意识到恢复南部黑人公民选举权的重要。政治权是获得平等民权、捍卫平等民权的保障。1963年,联邦民权事务局指出在南部至少有100个县的黑人选民的登记率在10%以下。1964年,第二十四条宪法修正案得以批准生效。该修正案规定在所有联邦官员(总统和副总统)和国会议员的选举中,州或联邦政府不得因公民未缴纳人头税或其他税收而拒绝选民的投票权。这是一个重要的进步,但仍然未能超越对联邦选举权的管理,没有突破旧有联邦制的羁绊——即州政府拥有规范本州公民选举权及其行使程序的权力。1964年,包括SCLC、SNCC和NAACP在内的民权运动组织都开始将下一阶段的运动目标锁定在为南部黑人争取选举权的问题上,但首先需要打破的是南部各州白人民主党人对州政权的把持。
1964年夏天,在联盟组织委员会(Council of Federated Organizations, COFO)的领导下,来自北部的数百名白人和黑人学生联合发起了密西西比州“自由夏天”项目(Mississippi Freedom Summer Project),目标是打破白人民主党人对密西西比州政治的封锁和垄断,动员黑人公民行动起来,参加选美登记,组织新的政治力量,重新进入州政治,与白人民主党抗衡。因为长期被剥夺了选举权,同时在经济上又依赖当地白人雇主,许多黑人选民不敢参加选民登记。大学生志愿者冒着危险,深入密西西比州的乡村,走村串户,对黑人选民进行选举知识的宣传,帮助登记黑人选民,建立和组织起一个“密西西比州自由民主党”(Mississippi Freedom Democratic Party,MFDP),从中选举代表参加民主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与该州的白人民主党形成对抗,要求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将对黑人选举权的支持纳入当年的总统大选的竞选纲领中。黑人民主党最终只是获得了象征性的承认,但自由夏天的活动对民主党和约翰逊总统施加了很大的压力。
1965年3月,SNCC和其他组织在亚拉巴马的塞尔玛组织和发起了为争取选举权的进军运动,目的是通过向该州首府蒙哥马利的进军活动,来营造声势,给国会施加压力,要求通过联邦选举权法。组织和领导这场运动的是后来著名的黑人国会议员约翰·刘易斯(John Lewis),当时他还只是一名20岁的大学生积极分子。1965年3月7日,在第一次进军举行时,非暴力的抗议者们遭遇了州警的暴力镇压,酿成著名的“血腥的星期日”(Bloody Sunday)流血事件,州警的暴力震惊全国。马丁路德金等组织了第二次进军,仍然未能成功。在联邦政府的干预下,第三次进军终于在3月21日开始,抗议者最终抵达了蒙哥马利。约翰逊也利用来自基层的压力敦促国会通过新的选举权法,并喊出了民权运动的口号“我们将排除万难”(We shall overcome)。
国会最终在1965年8月通过了《1965年选举权法》(Voting Rights Act of 1965)。该法的目的是彻底消除南部各州对黑人选民设置的种种歧视性选举资格限制,尤其是文化水平测试的规定。根据这项法律,任何州和地方实行的文化水平测试将自动停止,任何州合格选民的登记率在50%以下的也不能使用这种限制。只要联邦司法部发现任何州违反了第十五条宪法修正案,政府就有权任命联邦选举监察官到该州或地方监视选举,并有权准备新的选民登记表,并在选举日观察选举的全过程;同时严禁使用人头税来剥夺选民的选举权。
《1965年选举权法》带来的政治效果十分明显,南部黑人选民登记率迅速提高,最终达到与白人选民相等的程度。在1965年至1975年间,许多黑人担任了南部的地方官员,进入国会的黑人议员也增加了。1964年,有150万黑人在南部的11个州登记参加选举。1969年,黑人选民的人数达到310万。1963年,南部的黑人官员不过100人,到1973年时,仅密西西比一州的黑人官员就有近200人。最高法院也在一系列案件中支持了《1965年选举权法》的合宪性。我们看到,黑人公民选举权的恢复和使用逐渐改变了南部州政府的权力构成。
民权运动(“第二次重建”)的立法分析
民权运动对美国的“权力宪政”和“权利宪政”的改革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先来简短总结一下民权运动时期的相关民权立法。
1957年9月,在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建议下,国会通过了《1957年民权法》(Civil Rights Act of 1957)。该法建立了联邦政府确保民权享有的一些机构和权力,包括在司法部下建立民权局(Civil Rights Section),授权联邦官员对干扰选举权行使的行为进行调查和发出禁令。最重要的机制建设是建立联邦民权委员会(Commission on Civil Rights),负责调查权利歧视的情况并提出政策建议。这是自重建时期《1875年民权法》以来,联邦政府第一次就公民权利立法,两部法律相隔整整82年。来自纽约的黑人国会议员亚当·克莱顿·鲍威尔(Adam Clayton Powell)当时将这部法律成为黑人的“第二次解放”(the second emancipation)。但因为缺乏民主党人的支持,该法赋予执法部门的权力有限(譬如将民权委员会的任期限制在两年之内),执法力度也远远不够。1960年3月,国会通过了《1960年民权法》(Civil Rights Act of 1960),对1957年法律进行补充和增强。1960年法律延长了民权委员会的任期,扩大了联邦政府监管选举的权力,要求地方和州保存所有与选举相关的文献与记录(不得随意销毁),重申不得因种族和肤色对选民行使选举权进行歧视。该法还建立了对全国所有儿童和美国军队成员提供免费教育的规定。这两部民权法通过的时候,民权运动已经在南部展开,但两部法律都有一个明显的漏洞——缺乏对民权(civil rights)享有中的歧视性法律的禁止和纠正,而只是关注选举权问题。即便在选举权问题上,两部法律的监管力度也是十分有限的,虽然赋予了联邦政府调查、收集证据和提出法庭诉讼的权限,但没有触动州政府制定歧视性法律的权力。正是在这个背景之下,《1964年民权法》和《1965年选举权法》的重要性才得以凸显出来。
如我们在前面提到的,1964年民权法是一个内容广泛的旨在全面禁止种族歧视的法律,它的核心是直接面对弥漫于南部各州公共生活和公民生活中的、由州法支持的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法律与实践,它启用第十四条宪法修正案的原则将这些州法和实践宣布为非法和违宪,回应了民权运动的要求。需要指出的是,从蒙哥马利拒乘公车的抗议到伯明翰示威,还有发生在南部许多城市的示威,最初获得的成果都是局部的、有限的,属于个案性质的(case by case),而1964年民权法以联邦法的形式将反种族隔离和反种族歧视的原则联邦化(federalized)和国家化(nationalized)了,从而限制了州在管理公民权利方面的权力,这是对重建时期建立的新联邦制的使用,非常不容易,也非常重要,是联邦权力与州权力在另外一个层面博弈的结果。更重要的是,1964年民权法还重申了受教育的平等权利,就业、就职和接受联邦合同的平等权利,并将反歧视的内容扩大到种族和肤色之外,将宗教、性别和民族血统等因素包括进来,覆盖了几乎所有的美国公民和在美国居住的外国移民。这部法律(以及随后以此为基础的数部修订法)可以说是20世纪美国宪政的《权利法案》,也是对第十四条宪法修正案“平等法律保护”原则最有力度的诠释。
与此同时,《1965年选举权法》也直接面对了南部黑人公民无法自由、平等地行使选举权的问题,从联邦的角度,提出对选举权的全面保护。该法直接否定了地方和州政府针对有色人种的歧视性选举法规定(包括各地为阻止有色人种参与选举而设置的选民登记、语言要求、文化能力测试等规定),对歧视行为特别严重的地区建立针对性立法,赋予联邦司法部长期监管这些地区选举情况的权力,并要求个别选区或州提供双语选票以帮助双语选民有效地参加选举,行使投票权。与1957、1960年的民权法相比,《1965年选举权》执法的力度得到空前的加强,前所未有地扩大了联邦司法机构在实施第十五条宪法修正案方面的力度。可以说,没有这一条法律,便没有今天美国选举政治的格局和结果。2021年,在117届国会的535名国会议员中,有124人是少数族裔(非裔、拉美裔、亚裔等),占了国会议员人数的五分之一多。这个结果与1965年选举法有直接的关系。重申一遍,行使选举权规则的改革带来了政府权力构成的改革。
这一时代还有其他的法律,如《1968年民权法》(Civil Rights Act of 1968),该法旨在废除住房歧视和居住方面的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实践。1961年生效的第二十一条宪法修正案赋予首都华盛顿的公民参加总统选举的权利,1964年生效的第二十四条宪法修正案废除了人头税的选民登记规定,197年生效的第二十六条宪法修正案将行使投票权的年龄统一规定为18岁,即服兵役的起码年龄。
民权运动如何改变了美国?
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一种崭新的民权概念建立起来了。第十四条宪法修正案的内容得到了极大的充实,“平等法律保护”的原则得到了充分的运用,在公共生活中的对黑人和其他有色人种的法律歧视被禁止了,长期阻挠黑人公民参与政治的州法障碍被排除了。民权运动最具永久意义的贡献是,它把美国人争取权利的斗争变成了一种以群体为基础的斗争,它将一个以“种族”为整体的概念介绍到宪法中,把原来分散、孤立的个人权利的概念变成一种集体的群体权利,要求联邦政府对这些权利进行保护。在某种意义上,这种转变也是对美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体制性种族主义”的一种纠正——针对有色人种的种族主义思想曾经一直建构在美国南部的州法和一部分联邦法中。民权运动的立法建树也扩大了联邦政府的功能,限制了州权。将联邦政府逐步变成保护社会中受歧视的少数群体的工具,这是重建时代提出的重要宪政思想,但直到将近一个世纪之后才通过民权运动部分地得以实现。
同时需要指出的是,民权运动带来了美国公民权利的扩展。从权利宪政的角度,我们可以将1791年生效的《权利法案》(第一到第十条宪法修正案)看成是美国公民权利的第一次“革命”——通过宪法的制定将传统的个人自由和普通法权利变成了受宪法保护的“权利”,第十四条宪法修正案建立了联邦公民权利的原则,但没有细化这些权利。民权运动不仅将联邦公民的权利具体化了(如公民有不受歧视的权利),而且还为创造新的权利奠定了基础。今天美国公民享有的许多权利,如接受教育的权利、享受良好生活品质的权利、隐私权、接受联邦福利的权利、同性恋者的婚姻权,过去并不存在,甚至也不敢想象。
两次“重建”的比较、“权利革命”及民权运动时代的结束
现在让我们回到这两次讲座的主题——“美国历史上的两次重建”。我们看到,20世纪中叶的民权运动与19世纪中叶的重建之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联系——民权运动力图争取的是实现重建提出的、但未能实现的对获得解放的黑人的政治承诺。这两个历史进程在政治原则上是一脉相承的。两者之前当然有许多的不同,尤其是在参与者、领导者、联邦政府的立场与支持力度、黑白美国人之间的配合以及国际环境等方面。重建时代,北部共和党和联邦政府的即时目标是在前邦联州内建立亲共和党的州政府,虽然有一定程度的黑人和白人共和党人的配合,但效果并不理想,而且也未能持续下去。当时美国刚从血腥的内战中走出来,联邦国家的转型刚刚开始,没有建立起足够强大的、能够贯彻自己立法意志的国家机器,再加上重建时期总统领导力的相对软弱,共和党内部并为形成坚定的共识,国会内的多数党经常变换,实施重建宪法修正案非常困难。
而在从二战到民权运动时期,黑人人口的都市化和社交网络(通过教会、社团等机制)的出现,帮助建构了一个巨大的潜在的抗议人群;参与者有许多是受过教育、参加过二战的黑人积极分子,还有深受二战时期美国自由意识形态激励的新一代美国政治人物(在某种意义上包括了从罗斯福、杜鲁门、艾森豪威尔、肯尼迪和约翰逊在内的总统)也认为种族歧视变成了美国成为世界和西方领袖的一种政治负资产。艾森豪威尔在做出干预小石城高中合校事件时,他将捍卫联邦权威和顾及美国的国际形象作为一个重要因素来考虑。他之后的肯尼迪和约翰逊两任民主党人总统则更是将民权立法作为自己的执政标志来重视。
民权运动还在另外一个方面深刻地改变了美国——它激发了一场新的“权利革命”——这个题目需要另外一次讲座来展开讲。在民权运动的激发下,其他族裔和群体的权利抗争运动也在20世纪60年代得以发生和扩展,并延续到70年代甚至80年代。这些运动包括第二次妇女解放运动、墨西哥裔美国人和印第安人的争取权利运动、同性恋者的权益要求运动、大学校园的言论自由运动以及公民要求获得政府信息的运动等。这些运动与同代的反战运动、反正统文化运动等合在一起,极大地冲击了美国社会的传统秩序,也激发了强烈的来自保守势力的反弹。
早期的民权运动注重解决黑人遭受的民权不平等的问题,并没有触及经济权利不平等的问题。对于南部黑人来说,《1964年民权法》和《1965年选举权法》是非常重要的,但对于许多生活在贫困线下的都市黑人来说,它们更多的是一种政治上的奢侈品。黑人和有色人种在经济上的贫困导致他们继续在公共生活中遭受歧视。而一些黑人因经济上得不到保障因而对联邦政府感到失望,城市骚乱时有发生。《1965年选举权法》通过后不久,洛杉矶便爆发了都市种族骚乱。民权运动内部从一开始就存在“非暴力抵抗”和“以暴抗暴”的路线之争,此刻要求“以暴力抵抗暴力”压迫的“黑权” (Black Power)运动在都市黑人人口中开始获得更多的支持,一些早期支持民权运动的白人力量开始逐渐与黑人组织疏远,金的非暴力抵抗运动思想渐渐失去了感召力,民权运动的联合阵线开始瓦解。
1967年后,金等民权运动领导人开始将注意力转到黑人面临的经济不平等的问题上来。但是,对于这个触及资本主义社会中枢神经的问题,联邦政府和白人社会的大部分并不热心。约翰逊提出的“伟大社会”项目在实施中遭遇很大的阻力。主流社会只崇尚人人有均等的机会,相信凭个人的能力去争取经济上的成功,拒绝考虑由于历史原因造成的巨大的经济不平等。约翰逊政府忙于越战,更无暇顾及黑人的经济要求。1968年,马丁路德金和支持民权运动的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相继遇刺,民权运动开始进入低潮。同年总统大选中,共和党人尼克松以恢复“法律与秩序”为口号,在“沉默大多数”的支持下当选总统,民权革命的运动阶段落下帷幕。
结语:亚裔美国人与非裔美国人——共同和不同的美国经历
民权运动带来的另外一个成果是《1965年移民和国籍法》(The Immigration and Nationality Act of 1965)。从2021年的角度看,这是民权运动对美国人口结构、公民权利的享有和政党政治带来的最具有戏剧性、最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成果。我想,不少听众都注意到昨天公布的2020年美国人口统计结果,其中提到在新移民中,墨西哥裔和亚裔移民增幅最大,白人人口的比例在下降,而移民人口目前在美国人口中已经占到了14%左右的比例。人口学家估计,这个数字还会上升在2060年达到18%左右,而这也意味着白人人口的比例届时也将进一步降低,有色人种人口的比例将进一步升高。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从种族和肤色的角度来看,美国将会有一个更多元化的人口结构。这对于美国人的身份界定、美国公民权利的享有、美国人价值观的重新界定,以及不同族裔之间的相互和共同认同的塑造都会带来新的挑战。
我在这里没有时间展开讨论《1965年移民和国籍法》的立法背景,但希望指出这部法律应该被视为是民权运动的结果。美国从一开始就一个移民国家,殖民地时期的人口是多元化的,除美洲印第安人之外,其他人都是移民,先后来到北美的时间和方式不同,最早的是英国移民,随后是被强行贩卖而来的非洲奴隶,然后是不同欧洲国家的移民。19世纪上半叶,爱尔兰的大饥荒和欧洲革命将爱尔兰和德意志移民带入美国。1846-48年美墨战争后,美国兼并了墨西哥北部(今美国西南部),将大量墨西哥居民变成了美国人。随之开始的1849年淘金热,将华人带到了美国,开启了华裔劳工移民美国的历史。美国内战之后,日裔和印度裔也进入美国。1898年美西战争之后,美国占领了菲律宾,开启了菲律宾人移民美国的历史。这是19世纪美国移民史的主要篇章。
讲这些历史细节是什么意思呢?我是想说,从表面上看,美国的移民史一开始是“自由”和“开放”的,但实际上这并不完全真实。移民只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是“归化”(naturalization)——即来到美国的移民需要通过法律程序获得美国国籍、成为美国人。早期的移民也许是开放的,在十九世纪基本如此,但归化则是有限制的,正是在联邦归化法的制定和实施中,“种族”和“肤色”成为了一开始就建立起来的限制。《1790年归化法》明确规定,只有“自由的白人”(a free, white person)移民才能通过归化成为美国人。这是美国的第一部归化法,在美国宪法生效后一年开始实施。所以,建国者对于美国应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有一个清楚的认识——美国需要成为一个追求自由的国家,但自由只限于白人所享有。种族意识(racial consciousness)和种族主义(racism)与追求个人自由和国家独立是美国建国时并行的并同生共长的两个事实。这是一个悖论,但也是现实:自由不是所有人的自由,平等也不是所有人的平等,早期的美国自由与平等是建立在肤色、种族、性别等生理区别之上的,而支持和强化这些区别的法律。当第一批华人在1849年进入美国时,他们不是进入了“金山”,而是进入了一个具有强烈种族意识的国度,他们自动地被看成是“有色人种”(people of color),低人一等。你如果看美国联邦政府的人口普查资料,你会发现,从1790年到1870年,人口分类中只列出了两个种类:白人(white)和黑人(black) 。到1880年时,增加了华人(Chinese),大概认为华人既不是白人也不是黑人,那就单列一类。大概也考虑到文化、宗教和地域的因素。但在地方和联邦法律上,华人与后来的其他亚裔移民都被视为是“有色人种”,在法律待遇上与黑人是同类的。
但19世纪70、80年代排华浪潮兴起的时候,华人劳工在经济上对白人劳工形成竞争威胁是一个重要的动因,但种族主义也很方便地被利用起来,作为一种非经济手段的武器来压制、排斥和歧视华工。推动《1882年排华法案》制定的理由之一是种族主义——华人在人种上是低贱的、文化上是落后的、政治上是自私和保守的,与美国民族的气质与精神不符合。这种论点并不是针对华人而发明的,它早已经是一种成熟的思想,用来为支持奴隶制、在奴隶获得解放后继续歧视黑人的做法而正名。换言之,种族主义的思想与实践具有一种内在的交叉性,可以在必要时为白人用来捍卫自己的利益、优势和经济特权。
1868年第十四条宪法修正案生效之后,法律上不能再将出生在美国的非裔人后代视为“非美国人”,也不能以种族和肤色为由来拒绝来自外部的黑人通过归化成为美国人,但也不能将1790年归化法中的“白人”限制删除——这等于实施真正的“自由归化”政策。怎么办呢?国会在制定《1870年归化法》时绞尽脑汁,最终决定保留“白人”作为外国移民归化成为美国公民的条件,但同时附加说明非洲人后裔不受此限制。这个非常奇葩的法律规定完全是应西部国会议员的要求设置的,目的是防止已经在美国的华裔劳工通过归化程序成为美国人,避免将西部各州置于“黄祸”泛滥的威胁之下。所以,我们看到重建宪政改革的一个新的悖论——在赋予一部分美国有色人种(非裔美国人)以平等待遇的时候,又拒绝考虑给予另一部分在美国的有色人种(如华人)以平等的待遇。在这种背景下,10年后国会制定《1882年排华法案》实际上已经不足为奇了。
《1882年排华法案》在经过两次延长之后,最终在1917年演变成为对几乎所有亚洲移民进行全面禁止的法律。1924年移民法建立起按原国籍移民在美国的人口数(national origin quota)来配发新移民名额的实践,将欧洲移民视为最值期望的移民来源,继续全面禁止亚洲移民,而已经移民美国的亚裔移民的绝大多数也无法通过归化成为美国公民(只有他们出生在美国领土上的后裔才可根据第十四条宪法修正案成为美国公民)。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43年美国废除排华法案时为止。即便如此,美国也没有开放无限制的华裔移民,这也就是为什么华裔和亚裔移民人口在美国人口中的比例一直处于很低状态的原因——因为在1882-1965年没有大量的新移民人口的加入。
直到20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的发生,在非裔美国人运动的带动和鼓舞下,亚裔美国人第一次开始组织起来,与其他族裔一样,喊出了要求“平等”的口号,加入到民权运动的洪流中,推动移民法的改革。1965年移民法废除了按原国籍和民族血统来分配移民名额的做法,改用家庭团聚和美国“国家需要”作为移民标准,才使大量亚裔移民获得了进入美国、成为美国公民的机会。没有民权运动的推动,1965年的移民法改革是不可想象的。我希望强调的是,今天亚裔美国人在美国享有的种族平等和种族正义并不是美国宪法最初的自然生成,而是民权运动的结果,是依循第一次重建所建立起来的平等原则,并通过第二次重建中无数非裔美国人的艰苦斗争才取得的。我们要非常清楚地认识这一点。
谢谢大家。
2021年8月14日
来源时间:2021/8/25 发布时间:2021/8/25
旧文章ID:258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