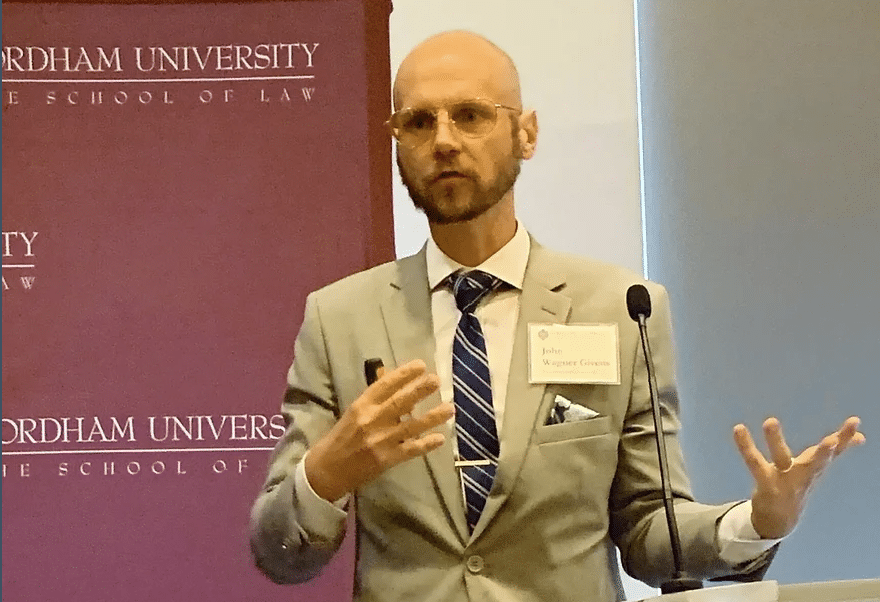杨原:对抗还是让步? ——大国崛起进程中的鹰鸽策略取舍逻辑
作者:杨原 来源:《当代亚太》2020年第5期
一、问题的提出
本文的研究问题是:崛起国在面对来自霸权国的遏制和打压时,什么条件下会倾向于选择对抗性 (鹰/强硬)策略,什么条件下倾向于选择让步性(鸽/合作)策略?
(一)理论层面的 “对抗—让步”两难
国家如何在对抗性策略和让步性策略之间做出选择,涉及国际关系理论中威慑 和螺旋两种模型的经典争论。威慑模型认为,强硬立场和有力的威胁有助于一国展示捍卫自身利益的决心,从而防止冲突的发生;让步和妥协性策略则会释放软弱信号,招致对方更多的挑战。螺旋模型则针锋相对地认为,让步能释放善意从而避免或缓解安全困境,强硬策略则会塑造和强化对方对自己的敌对认知,从而引发冲突螺旋,导致冲突升级。对抗和让步策略的优缺点恰好互补,造成了这两类策略在实践中的取舍两难。
根据现有研究,国家间互动是否符合威慑模型的预期取决于防御者发出的威胁是否足够可信。但如何既能让威胁可信到让对方认为一旦进攻则一定会招致报复,同时又使对方相信己方一定不会首先进攻,这在理论和实践中都是难题。同时,学者们对于冲突螺旋产生的原因也缺乏共识,一些学者认为,冲突螺旋源于错误认知等心理因素,另一些则认为源于特定的情境结构。冲突螺旋产生的根源不明确,进一步增加了决策者在对抗和让步两类策略中做出选择的难度。这种对抗—让步的理论两难甚至成为宏观理论争论的核心议题。进攻性现实主义主张以权力最大化求安全,防御性现实主义则强调权力扩张对安全的负效应。这两种宏观理论可以分别近似地被视为威慑和螺旋这两种中观理论模型的广义化,它们之间经久不息的争论反映出这个两难问题在国际政治中的普遍性以及解决这个问题的挑战性。
在复杂的大国政治中,保持有效的威慑非常重要,为此,需要让潜在对手相信其破坏现状的行为一定会给其自身带来巨大损失。但同时,通过自我克制、主动示善等方式增进互信、避免不必要的冲突或冲突升级同样非常重要。在霸权国的战略压力下,崛起国的策略选择不仅直接关系自身利益,而且会极大地影响两个大国的互动进程和体系的安全状态,这意味着从对抗—让步视角研究崛起国的行为规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政策层面的对抗—让步两难
冷战结束后,中国长期坚持韬光养晦的外交战略,表现出明显的现状偏好。但是,随着来自美国的战略压力的不断加大,中国战略界开始出现对既有外交战略的反思。一些学者指出,过分低调和示善,有可能限制中国应有的国家利益的拓展空间,使中国在与美国的 “讨价还价”过程中陷入被动,诱发美国更大胆的挑战。
自 2018 年美国发动对华贸易战以来,中国仍然坚持了以斗争求合作的总体方针,对美国提出的平衡贸易逆差、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诉求总体持合作立场。这些政策在战略界也引起了一定程度的争论。在学者们讨论合作性政策是否对中国有利时,另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也随之浮现———如果中国的对美政策增加 “强硬”和 “对抗”的比重,是否会强化两国的对立情绪,导致冲突螺旋,甚至由此引发一场 “新冷战”?现在的中国显然正处在一个战略取舍的十字路口,面对美国不断升级的战略打压,究竟是选择强硬反击还是缓和退让,正日益成为中国对美战略的焦点问题。
(三)研究发现和结构安排
本文在甄别威慑和螺旋模型理论前提的基础上指出,崛起国和霸权国在权力转移过程中的实际动机通常不符合螺旋模型的假定,这是导致现有许多实证研究不支持该模型预期的潜在原因。以地位动机为主要驱动力的崛起国与霸权国的战略互动,更加近似于 “消耗战”博弈所刻画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崛起国在对抗—让步策略光谱中的偏好由可支配的物质实力对比、决心对比以及实力变化趋势三个因素共同塑造。如果霸权国的遏制没有逆转崛起国对自身未来物质实力发展前景的原有乐观预期,则崛起国倾向于选择让步和合作性政策;如果霸权国的遏制逆转了上述预期,或者霸权国挑战了崛起国捍卫自身重大利益的决心,则崛起国倾向于选择强硬和对抗性政策。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主要是着眼于事实层面的经验性研究,即研究在特定条件下崛起国会怎么做以及它们为什么会这么做;而不是规范性研究,不讨论崛起国应当怎么做,不评价崛起国所选策略的对错优劣。当然,从理性和演化的视角看,倘若某种具有规律性的行为模式与崛起国的战略利益存在根本或重大抵触,那么这种行为模式本身也不可能真正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讲,本文对崛起国策略选择规律的探讨也具有一定的政策参考意义。
本文以下分为四个部分。第二部分回顾学界在对抗 (鹰/强硬)—让步(鸽/合作)策略取舍问题上的现有争论,第三部分提出崛起国鹰鸽策略的取舍逻辑,第四部分考察德国、苏联和北宋三个案例以检验第三部分提出的理论假设,最后是结论。
二、现有理论争论
(一)威慑与螺旋模型的分歧
对抗和让步策略各有优劣且彼此互补是导致这两种策略难以取舍的重要原因。让步 (鸽/合作)策略的一个核心优势是通过一定程度的让步能够释放善意,使双方避免因误解彼此意图而陷入安全困境或使冲突升级。如果双方能够通 过 长 时 间 的 互 惠 逐 步 建 立 起 互 信,就 会 进 而 形 成 积 极 的 合 作 螺 旋,在这种螺旋下,双方会不断强化稳定的合作与互信。让步策略的这种优势恰是对抗 (鹰/强硬)策略的劣势,从螺旋模型的角度看,后者无疑会加剧不信任和安全困境,增加冲突升级的风险。即使从更一般的角度看,“非理性”的强硬尽管会带来更好的讨价还价,但也会带来更缺乏效率的冲突。
但是,让步策略同样存在不可忽视的劣势。最首要的风险就是,如果对方有侵略意图,让步和释放善意的举动可能会使国家面临被攻击或被胁迫的危险。在对方胁迫下主动让步,还将破坏本国捍卫自身利益的声誉,从而增加未来遭遇他国挑战的概率。还有研究指出,螺旋模型提出的避免强硬对抗的建议在实际操作层面存在难点:一是决策者有时难以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维护本国安全的行动存在增加对方敌意和不信任的负面效应;二是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双方都有可能高估自己的实力或低估对方的实力,从而都坚持对抗。而让步策略的上述劣势同样也是对抗策略的优势。
对抗和让步策略难以取舍的另一个原因是学者们对于如何取舍存在很大的分歧。一般认为,这两类策略的效果和适用性取决于对手的类型。以罗伯特·杰维斯为代表的主流观点认为,如果对手的意图是扩张,则适用于威慑模型,己方应当选择对抗;如果对手的意图是保持现状,则适用于螺旋模型,应当选择让步。按照这种观点,国家决策的关键在于甄别对方的意图。但问题是,在一些学者看来,准确判断他国意图几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同时,螺旋模型所强调的示善策略要想有效地向对方展示善意,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条件是必须能够区分对方的进攻能力和防御能力,并且其进攻和防御能力与己方相比均不占优势。
使问题更加复杂的是,即使能够准确地判断他国意图,可能也无助于国家在对抗和让步策略中做出选择。首先,查尔斯·格拉泽认为,决定威慑和螺旋两种模型哪一种更适合于指导决策的不是对手的意图,而是对手的动机,即其是否愿意进行非安全目的的扩张。其次,罗恩·古兰兹等提出的博弈模型显示,对于防御者而言,其对挑战者的意图感到恐惧比了解到挑战者的意图是善意的,更有助于维护自己的安全。对挑战者意图的恐惧会提升防御者威慑的可信度和成功率。最后,理查德·赫尔曼等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提出,从对对手的不同印象(敌人或者盟友)出发而不是从对手的意图出发将决定己方的战略选择 (对抗还是合作)。
从上述梳理来看,很难从理论上对威慑模型和螺旋模型分出对错优劣;对于决策者如何在对抗和让步策略中做出选择,目前也缺乏理论共识。然而,与理论研究情况不同的是,实证研究几乎一边倒地支持威慑模型。卡斯滕·德勒的统计研究显示,谈判过程中一方强制性力量的增加会降低而不是增加另一方的要价水平;实力均衡更不容易引发权力竞争。贝尔·布劳莫勒的实证研究也显示,大国间的冲突最容易发生在它们与安全相关的活动不均衡时,这一发现同样符合威慑模型的预期。其他学科的实证研究同样提示个体行为模式与威慑模型的预期更为吻合。例如,市场营销领域的统计研究总体上更支持威慑模型。社会心理学的实证研究也显示,更多的强制性力量会降低而不是增加对方未来使用惩罚性策略的概率,相比较于实力均衡,实力不均衡更容易招致惩罚性策略。威慑模型在实证研究中明显胜出,其内在原因有待揭示。
(二)对绥靖政策的争论
与对抗—让步问题密切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关于绥靖政策的争论。受二战前英法绥靖政策失败的影响, “绥靖政策对国家安全有害”曾是学界的主流看法。较近的一些研究开始关注绥靖政策合理性的一面。关于国家为什么会选择绥靖政策,学界的看法同样莫衷一是。斯蒂芬·沃克认为, 20 世纪 30 年代英国之所以会选择对德绥靖,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经济受大萧条影响而无力支撑大规模的军备建设,而当时英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国际承诺又在不断增加,这使其在客观上难以采取有效的强硬手段抵制德国的扩张。诺宁·利普斯曼等则认为,英国采取绥靖政策是为了争取时间,在德国的军事实力已明显占优的情况下,英国只能通过这种缓兵之计争取更多的时间发展军备。
也有学者从更一般的角度探讨了绥靖政策的使用条件。罗伯特·鲍威尔指出,衰落大国不确定崛起国的目标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这种不确定性使得绥靖在很多情况下成为博弈的均衡选择。丹尼尔·特雷斯曼认为,抗争有助于增加自己决心的声誉,但同时也会消耗未来抗争或者威慑所需的资源。当资源是约束条件时,国家更有可能选择绥 靖 保 存 资 源 以 应 对 未 来 的 挑 战。彼 得 · 特 鲁 波 维 兹等指出,当决策者同时面临外部安全威胁和国内政治压力时,为了保证自己有足够的资源用于应对国内的挑战,决策者将更有可能对外采取绥靖政策。
(三)时间视野
时间视野是影响国家选择对抗还是合作策略的另一个重要变量。然而,学者们对于时间视野与国家策略选择之间的关系同样未能形成共识。以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的研究为代表的传统观点认为,国家越看重长期利益,即时间视野越长,则越倾向于采取合作政策。罗纳德·克雷布斯等借鉴心理学的解释水平理论指出,国家的时间视野越长,其对未来收益的估计会越乐观,同时会越不关心追求未来收益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风险和成本,从而有助于国家在当下做出互惠性让步。
然而,另一些学者却认为,时间视野越长,国家的行为会越趋于强硬和不合作。詹姆斯·费伦指出,时间视野的延长,固然有助于协议达成后被长期执行,但正因如此,谈判双方会愈发关注协议规定的己方获益的大小,这会增加双方达成协议的难度,降低双方在谈判中做出妥协的意愿。约书亚·科尔泽也认为,越看重未来利益的国家决心越大,越不情愿首先做出让步。米歇尔·加芬克尔等指出,合作和让步固然可以节省冲突成本,但也会因此失去通过战争削弱对手从而在未来冲突中获得更大收益的机会,因此国家越重视未来收益,越倾向于在当下采取强硬策略。莫妮卡·达菲·托夫特同样认为,看重未来收益会增加冲突的可能性,当互动双方都看重未来收益时尤其如此。
考虑到决策的互动性,对方的时间视野应该也会对己方的策略选择产生影响。根据凯尔·海恩斯的研究,己方时间视野越短,对方时间视野越长,己方越难以采取合作行为。但大卫·埃德尔斯坦的研究则提示,己方时间视野越短,对方时间视野越长,己方越容易采取合作行为。
上述争论充分反映出对抗—让步两难问题的复杂性,同时提示我们,对抗 (鹰/强硬)和让步 (鸽/合作)策略可能存在各自的适用边界和触发条件,本文的任务就是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探寻崛起进程中面对霸权国的挑战时,崛起国在这两类策略中做出取舍的原因和条件。
三、崛起国鹰鸽策略的取舍逻辑
(一)大国竞争的动因问题
受以新现实主义为代表的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和美国对外政策话语的影响,许多研究都认为,安全是大国对外行为的最主要动机,引发大国间冲突的最主要机制是安全困境。如果大国的目标函数真的只是确保自身安全,冲突真的只是源于无政府状态下的恐惧和错误知觉,那么螺旋模型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强硬反击和对抗会损害自身利益 (安全),适当的让步和安抚有助于缓和和规避冲突。
安全困境包括了猎鹿博弈和囚徒困境两种可能的支付结构。 如果是猎鹿博弈,即当对方选择合作时己方选择合作的偏好大于选择背叛的偏好,则这种情况下的 “安全困境”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 “困境”,只需要简单地建立信心措施即可实现合作。相对而言,囚徒困境下实现合作的难度要大很多,它也是国际关系学者用以分析大国冲突的一种常用模型。但即使是在囚徒困境状态下,由于相互合作是相互背叛的帕累托改善,因此,国家间仍然可以通过适当的策略选择和长期的互动形成互惠式的合作关系。这也是螺旋模型和防御性现实主义乃至制度主义核心政策建议的理论基础所在。
但问题是,安全困境并不是导致国家间军事和战略竞争的唯一机制,真实的利益冲突同样会引发类似的进程和结果。在与霸权国的互动中,崛起国的策略选择是否符合 (遵循)螺旋模型的预期 (建议),取决于双方的战略互动是否真的受安全困境机制的驱动。根据现有理论,安全困境的存在至少要具备以下两个条件中的一个:互动双方的动机都只是确保自身安全而不是寻求增量利益;互动双方的意图都不包括损害或削减对方的利益。遗憾的是,在崛起国和霸权国的战略互动中,这两个条件都很难满足。
首先,大国间战略竞争的主要动机是荣誉和地位 (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狭义上的权力)而不是安全。演化生物学和演化心理学的大量实验显示,对支配地位的渴望是动物的一种自然本性。近年来,国际关系学界逐渐意识到将国家动机纯粹简化为追求安全的错误,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地位动机的普遍性和重要性,指出以追求地位为主要动机的位置竞争是大国战略竞争的主要类型。在位置竞争下,崛起国和霸权国的冲突源于真实的利益冲突而不是无政府状态下的恐惧。霸权国会担心崛起国的崛起导致自己的地位下降,由此产生的地位焦虑会促使霸权国阻挠崛起国地位的提升。
对崛起国来说,尽管由于其实力处于增长轨道,因而在多数时候只寻求改变实力分布而不寻求改变现有秩序和规则,但随着实力对比的持续变化,霸权国所主导的国际秩序与崛起国的利益诉求之间的矛盾会逐渐突显,毕竟,崛起国在现有国际秩序下只能缩小与霸权国的实力差距,而难以成为第一领导国并建立新的国际秩序。面对霸权国的阻挠,追求地位提升的动机会驱使崛起国采取相应的策略,甚至会采取冒险和侵略性行动以抵抗地位固化的阻力。总之,受地位动机影响,崛起国和霸权国的冲突并不是什么“困境”或 “悖论”,而只是双方利益冲突的直接表现,并且这种利益冲突在很大程度上是零和的。正如有评论所指出的,如今中美博弈 “一方的获胜在很大程度上就意味着另一方的失败:要么中国臣服于美国主导的秩序,要么美国撤出西太平洋”。
其次,大国在战略竞争中对彼此的意图很难完全保持善意。崛起国与霸权国的竞争通常由实力对比变化而引发,随着权力转移的进行,霸权国会越来越难以相信崛起国的克制承诺,日益明显的相对衰落前景会逐渐强化前者对后者发动预防性进攻的意图。近期的研究甚至显示,即使放松 “国家知道并能预见权力转移”这个假定,权力转移背景下的承诺问题依然存在并且依然可能引发战争。而对崛起国而言,发动冲突和战争能够起到迫使其他国家承认其地位的效果,甚至无关其结果是胜是败。
综上可见,大国战略互动通常都不构成安全困境。正因如此,美苏冷战从整体上看并不属于安全困境,而更适合被视为一种大国间的持久性竞争。同时,这也能解释为什么文献回顾中提及的多数实证研究都不支持螺旋模型的假设:因为该模型的理论前提在真实世界中很难完全满足。厘清大国竞争的动因问题,为我们准确揭示大国互动中崛起国一方对抗—让步策略的取舍逻辑扫清了障碍。
(二)消耗战博弈下崛起国的决策逻辑
相较于由安全动机驱动的安全困境模型,由地位动机驱动的大国竞争更适宜用 “消耗战”博弈加以刻画。在消耗战博弈下,博弈双方为争夺某个利益而展开竞争,当其中一方选择退出时另一方赢得该利益;在双方都未选择退出时,双方每坚持一轮都须支付相应的成本。在这个限定下,对每个参与者来说,对方退出的时间越早,己方收益越大;对方下一轮退出时己方的收益大于己方在这一轮退出时己方的收益。当两个大国投入资源争夺地位、荣誉和权力,且双方均难以在单次战争中取得对对方的决定性胜利时,双方的竞争与消耗战博弈的上述两个特征相吻合———双方都希望对方先退出竞争,并且为了迫使对方先退出,双方都愿意比对方坚持更长的时间。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因素左右着这场消耗战的胜负,进而影响着博弈参与者的决策?
1.物质资源 (实力)对比
竞争双方可支配物质资源总量的对比从根本上决定了消耗战博弈的最终结局———谁的资源总量更大,谁就能坚持更长的时间。这意味着,在完全信息情况下,物质资源总量较多的一方在第一轮选择争夺,较少的一方在第一轮选择退出是该博弈的纯策略纳什均衡。不过,大国物质资源的对比不是静止不变的,大国一方面会因竞争而消耗资源,另一方面又会因经济生产而创造资源。如果经济发展创造资源的速度超过了自身因竞争而消耗资源的速度,那么国家的可支配资源总量仍然会随时间增加。显然,那些物质资源“净增速”(经济发展创造资源的速度减资源消耗的速度)较低的大国,将最终因相对物质资源较少而败下阵来。因此,处于权力转移过程中的大国一方面会关注各自实力随时间的相对变化趋势,另一方面,相比较于军事实力,大国特别是霸权国会更加关注经济发展的潜力。
崛起国的定义决定了其物质实力增速快于霸权国。这种相对有利的实力变化趋势决定了崛起国在对抗 (鹰/强硬)—让步 (鸽/合作)的策略光谱中存在偏好后者的固有倾向。这是因为,首先,时间在崛起国一边,相比较于现在,崛起国
在未来与霸权国交战或谈判的处境将更为有利,因此,崛起国有动机推迟冲突。其次,避免冲突有助于保持和促进崛起国的实力增长趋势,如果过早选择强硬和对抗策略,则不仅会丧失原有的积累实力的机会,而且会招致其他国家的制衡,从而额外消耗自己的发展潜力。最后,根据前景理论,实力崛起的过程处于收益区间,在该区间下行为体会更倾向于规避风险。因此,相较于地位下降所引发的地位焦虑,地位上升速度低于实力增长速度所引发的地位不一致导致崛起国采取冒险举动的可能性更低。
也正因如此,越来越多的批评者质疑经典权力转移理论关于崛起国有修正主义倾向的理论预设,毕竟,崛起国冒险用一种未经检验的新秩序取代一种正在促使其崛起的现有秩序,且不惜为推翻现有秩序、建立和维持新秩序支付巨大的成本,这样的设定是令人费解的。正如戴尔·科普兰所说,“对于一个正在崛起的国家而言,几乎没有理由去发动一场大战或者一轮显然会引起大战的危机”,“只要冷静对峙下去有利于本国的发展,就没有理由打破现有的格局”。从这个意义上讲,崛起国的 “修正主义”主要体现在改变现有物质实力对比而不是现有秩序的规则和制度上。具体到中国这个崛起国,有研究显示,随着实力的增长,中国在处理领土争端时使用武力的意愿在下降而不是上升。
总之,相对物质资源是消耗战博弈的根本约束,崛起国的实力增长预期使其有意愿在较长时间内选择较为克制的合作性政策。2018 年美国为打压中国的经济和科技发展发动贸易战,但中国政府认为 “中国经济长期向好大势没有变”。
基于这一判断,中国在贸易战中的应对总体上保持了克制和合作的姿态。20 世纪 30 年代,面对德国的不断挑衅和扩张,英国政府认为通过大规模重整军备,自己与德国的实力均衡能够在 30 年代末得到恢复,因此决定在此之前对德绥靖以争取更多的发展时间。
反过来,如果霸权国的打压和遏制政策使崛起国的实力增长预期逆转,则崛起国出于夺回自身物质实力发展主动权的理性考虑,以及身处损失区间愿意承受风险的心理倾向,会转而选择强硬和抗争性策略。一战后,日本工业发展所需的原材料和石油几乎完全依赖进口,而美国和英国自 1930年之后开始增加贸易限制,到 1941 年8 月,美英等国切断了对日所有石油贸易,对此日本决策者一致认为,除非恢复石油进口,否则经济衰退将危及自身长期安全。为恢复石油贸易,日本天皇最终批准了全面战争计划。
2.决心对比
相对物质实力并非决定消耗战博弈结果的唯一因素,因为在现实世界中,博弈双方的资源总量以及各自愿意投入的资源总量等信息往往是不对称的。在不完全信息情况下,谁能让对方相信自己有能力和意愿消耗更多的资源 (坚持更多的轮次),亦即展示更大的决心,谁就能够迫使对方首先退出竞争。这一点在核对抗中体现得最为明显。而即使是在常规军事冲突中,决心与冲突结果之间也存在着明显的正相关关系。从博弈模型来看,在不对称信息条件下的消耗战中,表现更加强硬、更有决心的一方预期收益更高。
消耗战博弈的这一特点决定了参与者有动机证明和捍卫自己的决心。国家不仅仅关注自己行为的短期结果,还关心其长期影响。其他国家会观察一国的行为并根据其既有行为所建立的声誉做出相应的决策。在这种情况下,当一国决心遭到对手的质疑和挑战时,其必须要考虑如果自己在当下做出让步会对自己决心的声誉 造成何种影响,进而对自己在未来博弈中的处境产生何种影响。实证研究显示,发出威胁的一方如果在过去的强制性外交中做出过让步,则当前其威胁的目标方做出让步的可能性更低;过去退缩过的国家更有可能在未来遭到挑战。
由于一国过往行为所建立起的决心的声誉能够增加自己在未来博弈中讨价还价的筹码,声誉越高越有可能迫使对手在未来轮次中首先退出博弈,因此,捍卫决心的声誉必然成为大国竞争中影响大国决策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个体预期未来博弈的轮次越多,声誉对个体的重要性越大。对自身决心的声誉的关切会直接影响大国在对抗 (鹰/强硬)—让步 (鸽/合作)政策光谱中的选择。实证研究显示,决策者越重视他国对本国决心的看法,就越愿意将争端升级而不是让步。向对手证明自己的决心,是国家发动军事冲突的重要动机。
1995 年5月,美国宣布允许中国台湾地区领导人李登辉访美。中国决策层对美国此举意图的判断是 “测试一下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底线”,看中国是否会 “吞下李登辉访美的苦果”。为打消美方幻想、展示捍卫国家主权的决心,长期坚持韬光养晦战略的中国政府迅速做出决定,采取了包括开展连续9个月的大规模台海军事演习、召回驻美大使、暂停两国副部长级以上高层访问在内的一系列强硬反击措施。根据最近的一项研究,建立和捍卫自己决心的声誉同样是近期中国在南海地区采取强制性策略的重要考量。
3. 理论假设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将崛起国应对霸权国挑战时的决策逻辑总结为如下三个假设:
假设 1 :如果霸权国挑战的主要目标是抑制崛起国物质实力 (主要是经济实力)的发展潜力,但这种挑战和遏制并未从方向上逆转崛起国对自身未来实力发展前景的原有预期,则崛起国的政策偏好是规避风险,倾向于选择让步和合作性政策。
假设 2 :如果霸权国抑制崛起国物质实力增长的行为逆转了崛起国对自身发展前景的预期,由预期收益转变为预期损失,则崛起国的偏好是接受风险,倾向于采取强硬和对抗性政策。
假设3 :如果霸权国试图试探和挑战崛起国捍卫自身利益 (尤其是重大利益)的决心,使崛起国感到如果在当前做出让步,则不仅自己须付出重大代价,而且未来对方很可能会提出更过分的要求,那么崛起国会倾向于接受风险,选择强硬和对抗性政策。
四、案例研究
本部 分 通 过 考 察 德 国 (1890~1914)、苏 联 (1945~1948)和 北 宋(1004~1120)三个案例,分别检验上文提出的三个假设。
(一)德国 (1890~1914)
俾斯麦时期的德国采取了克制的对外政策。俾斯麦认为,德国经济正在发展,没有必要过早地露出锋芒。而在俾斯麦下台之后,德国事实上在一段时期内依然延续了其外交路线。俾斯麦的继任者列奥 · 冯 · 卡普里维认为,维持德国安全体系的前提是永远不要挑战英国的海上霸权。1890年7月,德英签订了划分两国在东非和西南非势力范围的《赫尔果兰—桑给巴尔条约》,双方都将该条约的签订视为德国对英国的重大让步。威廉二世做出这一让步的唯一目的是换取英德关系的良性发展。1897年新任德国外交大臣的伯恩哈特·冯·比洛也认为,不激起英国的愤怒和怀疑至关重要,德国外交的主要任务就是确保与英国保持良好关系。
德国对外克制的外交战略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本国经济的顺利发展为前提的。到 19世纪90年代,德国已经成为以重工业为主导的工业强国。工业生产能力越大,德国自身的原料供给能力和市场规模就越显现出不足。在这种情况下,德国资产阶级迫切需要走出国门,寻求海外原料市场和商品销售市场。进口方面,1910年,德国原料进口已达到16130 万马克,与 1872 年相比增长约 28 倍,1890至 1913年,德国粮食进口年均增长 4.8% ,远高于3.9%的总体经济增速;出口方面,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德国全部工业品的1/5到1/4依赖国外市场。德国的资本输出需求同样增长很快,从19世纪 80年代到 19世纪末,仅20 年左右就从资本输入发展为资本输出。德国各阶层因此逐渐形成一种共识,即德国迫切需要获得 “必不可少的”殖民地,以便吸收过剩的产品、资本和人口。当时的泛德意志协会主席亨利希·克拉斯说:“如果说某一个国家有理由关心如何扩大它的势力范围,这个国家就是德意志帝国……我们需要工业品销售地区和工业原料。”
经济发展形势的变化在促使德国当局重新审视自己外交战略的同时,也开始引发英国的焦虑。事实上,对德国经济超越英国的关注是一战以前的20年里英国政治的主要议题。1897 年,加拿大突然对非英国商品征收歧视性关税,此举直接违背了德国和英国于1865年签订的最惠国条约的相关规定。德国对此提出抗议,但英国非但没有做出补偿,反而发表声明单方面废除了1865年条约。随后英国又与其各殖民地谈判,允许殖民地或英联邦国家自行采取单边歧视性政策。英国的这种收紧自由贸易的政策很自然地被威廉二世视为在针对德国,他对此表示, “除非我们建立一支强大的舰队,迅速而有力地阻止这种邪恶行为”,否则英国人就会得逞。
当时德国的各阶层人士都认为,现存的殖民帝国将进一步转变为封闭的保护主义实体,美国的门罗主义将得到更严格的执行,并将西半球与世界的其他部分隔离开;英国、法国和俄国的政策也将沿着类似的方向变化,加强其特惠关税制度,并消除外国首先是德国的竞争。美国极端保护主义的关税政策以及英国建立海关联盟的计划,成了当时德国决策者的主要关切。而事实上,英、美、法三国的确在1897年签订过一个秘密条约,得知条约内容后,威廉二世很确定地认为其目的就是 “试图消灭德意志帝国和奥地利,减少它们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对手”。
德国的决策者非常清楚强硬会招致英国的打压并可能诱发两国冲突。比洛曾指出,“我们的舰队在建造时必须考虑英国的政策。……我们不能以针对英国的政策来指导我们的决定和行动,也不能为了英国的友谊而依附于它。……在发展成为一个海上强国的进程中,我们既不可能作为英国的附属国,也不可能作为英国的对手而实现我们的目标”。由此可见德国在对抗和让步之间的两难处境。
然而,德国同时还面临另一个严峻的现实,那就是海外殖民地已基本被其他欧洲强国瓜分完毕,如果不能通过有效的手段实现海外市场的扩张,则德国崛起的方向和路径将受到严重阻碍。更为严峻的是,随着英德关系的逐渐紧张,对海外贸易极端依赖的德国人越来越担心其海上交通线被英国切断,这促使德国下定决心大力发展海军。事实上,在一战前的十年中,英国已经制定了完整的对德封锁计划。在这种形势下, 1899年9月,德国海军大臣阿尔弗雷德·冯·提尔皮茨指出,德国在海外的大规模商业扩张几乎注定会导致与其他国家的接触和冲突,因此,如果德国不想迅速衰落,增强权力 (海权)就显得至关重要。1900年的一份德方备忘录更明确地指出:“如果我们希望推行强有力的海外政策并确保那些有价值的殖民地,我们必须首先准备好与英国或美国发生冲突。”
进入20世纪后,为抑制德国的崛起,英国开始采取对欧洲大陆的 “再平衡”战略,于1904年和1907年分别签订 《英法协约》和 《英俄协约》,明确划分了英、法、俄在海外争议地区的势力范围,从而使三国得以在一定程度上摆脱欧洲以外的纠葛而将更多的精力和资源投向欧洲大陆。英国以这种方式将英德对抗转化为德国与整个欧洲均势体系的对抗。在1904年以前,德国一直认为英国与法俄同盟之间存在不可克服的矛盾,德国可以在英国与法俄之间走 “中间路线”,因此,德国对 《英法协约》的签订深感震惊,外交系统官员普遍认为,英法缔约是法俄同盟建立以来德国外交遭受的最大挫败之一,并认为德国必须采取措施进行反击。1905年3月,威廉二世在访问丹吉尔时强调,德国决定将保护它 “在摩洛哥的巨大的和不断增长的利益”。这个宣示被认为是对英法发动外交攻势的前奏。
1907年8月 《英俄协约》的签署无疑是对德国的又一次沉重打击,德国
由此感觉到其他大国开始认真地联合起来遏制德国。在当年举行的第二次海牙会议上,英国提出限制军备,对此德国当然无法接受,两国的不信任进一步加深。此后从1909年起一直到1912年,英德断断续续地就海军军备问题进行谈判,德方一度提出推迟其海军计划进程但不进行削减,希望以此换取英国在德国一旦受到攻击时保持中立,英方对此表示拒绝。1914年第二次摩洛哥危机后,德国政府和各党派均意识到,必须建立自给自足的经济区,以确保德国的原料和粮食进口以及工业出口不受封堵,为此,德国将不得不以战争的方式夺取殖民地,包括 “在最直接的欧洲势力范围中的大片土地”。
总之,随着本国经济发展潜力的日益受阻,德国的外交战略由温和逐步转变为强硬,这种强硬政策发展到极致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德国决策层对这次战争的目标非常明确: “建立大中欧经济区,使我们能够在各国的经济斗争中保持自己的地位,在面对那些日益封闭和强势的世界经济帝国时,不至于陷入经济衰退的窘境。”
(二)苏联 (1945~1948 )
二战后的美苏关系通常不被视为典型意义上的霸权国与崛起国的关系,但苏联作为相对弱势的一方,其承受的来自美国的压力总体上大于它对美国的压力,分析二战后苏联对美政策的转变有助于深化我们对两极互动下实力较弱方对较强方政策转变轨迹的理解。
二战结束初期,苏联的经济和军事实力都远落后于美国,因此选择了战略克制,避免挑战美国的直接利益。在自身势力范围得到保证的前提下与美英等西方国家和平共处,是这一时期苏联外交的一项基本原则。1946年12月 21 日,斯大林在会见来访的埃利奥特·罗斯福时表示,苏联这样的共产主义国家与美国这样的民主制国家和平相处 “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合理的,完全可以实现”。1947年4 月9 日,斯大林在会见美国共和党人士哈罗德·史塔生时再次重申了两种制度和平共处和相互合作的愿望。此外,当时的苏联高层非常不愿意苏联再次陷入大规模战争中。苏联红军从1945年5月的1140万人裁减到1947年下半年的290万人。对此,美国军方的一份报告认为, “除非出于纯粹防御的目的”,苏联在五至十年内必然会尽量 “避免发生大规模的武装冲突”。
1946年9月17日,斯大林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我不相信 ‘新战争’的实际危险。”二战结束初期,斯大林对战后国际秩序的安排也持较正面的态度。1946年3月22日,斯大林在回答美联社记者关于联合国意义的提问时表示:“联合国具有重大的意义,因为它是维持和平和国际安全的重要工具……它是建立在各个国家平等的原则上,而不是建立在某些国家统治另一些国家的原则上。”1946年9月在回答记者问时,斯大林明确表示:“我不认为英国和美国的统治集团能够 ‘对苏联’造成 ‘资本主义包围’,即使他们想这样做的话。”同年10月在回答记者问时表示,他不同意美国国务卿詹姆斯·伯恩斯所说的苏美关系已日益紧张的意见。上述外交原则以及对战后国际关系的基本判断直接影响了苏联在德国问题上的政策。二战结束初期,斯大林在德国问题上一度对美国的政策提议持开放和合作的态度。1945年12月,斯大林在莫斯科与伯恩斯会谈时表示,他对美国决定保留雅尔塔—波茨坦合作模式感到满意,并原则上同意就德国非军事化问题进行讨论。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苏联对美国战略意图的不信任开始加深。1946年5月,苏联决策层对美国提出的德国非军事化提议进行评估后一致认为,美国的主张包含了终止苏联获得德国赔款、废除雅尔塔—波茨坦模式、削弱苏联对德国的控制以及促使德国反对苏联等目的。此外,苏联高层官员及斯大林本人都担心,过早地从德国撤军会使苏联失去继续在中欧和巴尔干半岛驻军的权利。与此同时,美国杜鲁门政府对苏战略开始转向 “遏制”模式,这进一步暗淡了苏联与美国在德国问题上达成合作的前景。1946年9月6日,伯恩斯在演讲中强调,美国而不是苏联应当成为德国主权和民主化未来的主要支持者。这个演讲进一步强化了苏联决策层关于美国意欲消除苏联在德国的存在并否认苏联在中欧势力范围的共识。
尽管如此,直到1947年,苏联在德国问题上依然保持了克制,主动限制东德共产主义者和苏联驻德军事管理委员会中的激进分子的行动,延缓了对德国苏占区的苏维埃化。1947年4月,在莫斯科召开的苏、美、英、法四国外长会议上,参会的西方代表否决了在德国成立中央政府机构的提议。为挽回提议,苏联外长莫洛托夫甚至表示愿意在赔款问题上做出更多的让步。苏联之所以会选择保持克制,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斯大林及其他苏联高层相信,战后资本主义国家将不可避免地出现经济危机,一旦发生,美国将不得不从西欧撤军。
但是,当苏联在德国的既有权益不断受到挑战时,为表明捍卫自己利益的决心,苏联在德国问题上的对美政策开始逐渐强硬。1947年,美、英、法提出对德国西部三个占领区实施一体化并共同参与马歇尔计划,这明显违背了波茨坦会议所确立的统一德国的原则。1947 年11月至 12月在伦敦再次召开的苏、美、英、法四国外长会议上,苏联与西方在西德一体化问题上产生了严重分歧。面对莫洛托夫的抗议,英国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公然警告称:“你们把自己的脖子伸得太长了,总有一天会被砍掉的……我们知道你们不能忍受战争,而你们的行为正在把双方引向最后的摊牌。”
此次会议后,美、英、法三国继续无视苏联的强烈反对,于1948年2月在伦敦重新召开会议,在未邀请苏联代表与会的情况下,不仅批准了德国西部地区的经济统一决议,而且坚持在整个德国推行苏联明确反对的联邦政府制度。这次会议直接违反了波茨坦会议确定的四大国共同决定德国事务的基本原则,这种挑衅苏联大国地位的举动显然是苏联无法接受的。苏联外交部欧洲三局主任安德烈·斯米尔诺夫在3月12日写给莫洛托夫的一份备忘录中提出,根据目前的情况, “我们不能再局限于向西方列强提出抗议……,我们不仅需要采取措施限制美、英、法在德国采取的分裂行动,还应积极行动打乱他们将德国纳入西方集团的企图”。
1948年3月30日,苏联宣布从4月1日起检查所有经苏占区进入西柏林的货运和人员证件,由此引发第一次柏林危机。 6月7日,英、法、美三国在伦敦发布共同声明,宣布将在德国西部占领区建立一个联邦政府。 6 月18日,三国进而宣布在西占区开始发行新货币。面对西方的紧逼,苏联不得不再次提高对抗强度,于6月24日切断了西柏林与其他西占区之间的一切陆路和水路联系。在实行封锁的前一天,苏联在华沙再次召集东欧各国外交部部长,宣布西方在德国建立联邦政府的决定是无效的。莫洛托夫表示:“如果我们输掉了德国,我们将输掉最后一场战争。”
由此可见,苏联在德国问题上政策逐渐转向强硬的核心决策逻辑是为了向美国及西方展示自己捍卫利益的决心。莫洛托夫在事后回顾柏林危机乃至美苏冷战的起源时说:“这一切都不过是因为我们在前进。他们 (西方国家)当然会对我们态度强硬,而我们则不得不捍卫我们所征服的东西。”事实上, 1948年4月苏联方面获得的舆情就已经显示,当时的美国外交决策层已经将柏林视为考验美苏双方外交政策决心的地方。在这种情形下,斯大林不得不选择以封锁柏林这样一种强硬方式让美国意识到苏联完全可能因德国问题而与美国发生战争。
(三)北宋 (1004~1120)
与美苏案例类似,北宋与辽之间也不是典型意义上的崛起国与霸权国的关系。之所以选择该案例,一是因为宋辽之间存在对体系主导权的竞争,符合本文的理论前提;二是因为该案例是一个大国长期面临另一个大国的挑战而两国关系却保持了长时期和平的典型案例,分析该案例有助于展示当经济前景不构成约束条件时,大国面对另一个大国挑战时的决策逻辑。
在宋辽关系中,宋 (在两次北伐之后)总体上更为克制,这被很多人归因为其军事实力的羸弱。但实际上,宋辽军事实力在很长时间里是大致相当的,辽并没有压倒性优势。979年,宋太宗第一次征辽失败后,辽于当年秋发动满城战役,最终宋军 “斩首万余级,获马千余匹”。980年三月,辽发动雁门关战役,最终宋以少胜多,杀退辽军。980年十月,辽景宗率军亲征,双方互有胜负,最终继续保持原有疆界。986年宋太宗第二次北伐失败后,辽乘胜南侵,宋辽两军先后发生君子馆和土磴寨战役,988年、989年和995年,辽又发动侵扰性战事,双方仍是互有胜负,宋军无力深入追击和围歼来犯的辽军,辽军也无法顺利攻占入侵地区。
999年、1001 年和1002 年,辽又三次侵宋,双方依然互有胜负,虽然宋军损失更重,但仍成功阻止和击退了辽军。屡次伐宋均徒劳无功,辽高
级将领多有厌战思想。萧太后也 “有厌兵意”。在此情况下,辽制定了以战促和的对宋方略。1004年秋,辽再次大举攻宋,两军在边境交战,仍是互有胜负。而在交战之初,辽就向宋传递议和信息,主动表示 “北朝钦闻圣德,愿修旧好”。在辽军进攻遭到有效抵抗、辽多次遣使 “乞许通和”的情况下,双方最终签订澶渊之盟。1042年,辽再次向宋索要关南土地,宋臣富弼出使辽国问辽兴宗:“今中国提封万里,所在精兵以万计,法令修明,上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胜乎?”辽兴宗回答 “不能”。
除了军事实力对比之外,也有人认为宋对辽忍让是因为有西夏的牵制,但事实上,辽同样受到西夏的牵制。1013至1020年,辽与元昊部因党项部落叛逃、吐蕃进贡等问题矛盾日益激化,1020年,辽夏在凉州北境发生军事对峙。与此同时,西夏对宋用兵不断取得胜利,又引起辽的嫉视和不安。辽夏矛盾在客观上为北宋创造了左右逢源的有利战略环境。1044年,辽兴宗起兵征伐西夏,还特意提前遣使至宋以争取后者的中立——— “或元昊乞称臣,幸无亟许”。
此次战役西夏虽然获胜,但对辽依然心存戒备,元昊临终时曾叮嘱其子谅祚: “异日力弱势衰,宜附中国,不可专从契丹。……顺中国则子孙安宁,又得岁赐官爵。若为契丹所胁,则吾国危矣。”
由上可见,宋对辽的政策选择存在其他更为主要的影响因素。宋辽对峙固然存在地位和权力的争夺,但辽直接针对宋的双边性挑战,其目标很多时候集中于经济利益。这一点在1042 年辽向宋索要关南地区土地时体现得最为明显。辽挑起这次争端的主要目的就是从宋攫取更多的经济利益。这一点宋方也看得很清楚,富弼出使辽国时,曾向辽帝转述宋仁宗的判断: “北朝所欲,不过利其租赋耳。”
一旦矛盾集中或者转化到经济维度,宋显然是更自信的一方,毕竟单以经济实力而论,北宋犹胜于汉唐盛世。农业时代经济繁荣的一个重要指标是人口数量。宋太祖开宝九年 (976年),全国户籍只有309万户。而到仁宗天圣年间 (1023~1032 年),户数已超过 1000 万。到北宋末期的宋徽宗大观四年 (1110 年),全国总户数超过2088万,几乎是汉唐盛世时的两倍,而北宋疆域远小于汉唐。按每户平均五口计算,北宋末期人口已超过一亿。人口和人口密度的增加,反映出北宋农业生产力的巨大优势。
北宋物产也比前代富足得多。北宋一般年产银二三十万两,最高达八十八万两;铜一般年产四百多万到六百多万斤,最高达一千四百六十余万斤;铅一般年产数十万斤,最高达九百多万斤;锡一般年产三十万斤,最高达二百三十万斤;铁一般年产六百万斤,最高达八百二十四万斤。单就铁产量而言,其峰值相当于唐宪宗元和初年的四倍,唐宣宗大中年间的十七倍。受铜、铅、锡等金属产量激增的影响,宋太宗至道年间铜钱岁铸额已达八十万贯,比唐代多出几倍。到宋神宗元丰年间,岁铸额增加至五百零六万贯,是宋初的六倍多,是唐代的几十倍。
与经济发展相应的是,北宋的财政收入一直比较充裕。宋太宗至道年间(995~997年),岁入税钱达三千五百五十九万贯。真宗天禧 (1017~1021年)年末达到五千七百三十二万贯。整个真宗、仁宗时期岁入约在四千万贯
至六千万贯之间。宋神宗熙宁、元丰年间 (1068~1085年),岁入税钱最高达六千万贯。政府资产如此充裕,以至于即使在用兵最为频繁的宋太宗时期,甚至出现了大批军用物资在库房霉烂的情况。神宗时期内殿库房所积绢匹三十二个库房都装不下,不得不另行扩充了二十个库房。
由于对手看重经济利益,而自身在经济和财政方面的条件又相对宽裕,因此北宋在面临辽的挑战时逐渐倾向于规避风险和做出让步。1004 年,宋辽在澶州形成对峙,边打边谈。宋真宗提出的和谈原则是:“若屈己安民,特遣使命,遗之货财,斯可也。所虑者,关南之地曾属彼方,以是为辞,则必须绝议,朕当治兵誓众,躬行讨击耳。”一方面明确己方的底线是守住关南土地,并强调不惜为此与辽战斗到底,另一方面也提出了己方可以为了维持和平而在经济利益方面做出妥协。宋方谈判使臣曹利用向宋真宗请示可接受的岁币数额,宋真宗明确表示:“必不得已,虽百万亦可。”最终,北宋以远低于该底线的岁币数额与辽签署澶渊之盟,并由此维持了两国长达一百多年的和平。澶渊之盟规定,宋每年须向辽提供二十万匹绢和十万两银。对这一让利,真宗朝宰相王旦认为: “国家纳契丹和好已来,河硕生灵,方获安堵,虽每岁赠遗,较于用兵之费,不及百分之一。”仁宗朝大臣富弼也认为:“自此河湟百姓,凡四十年不识干戈。岁遗差扰,然不足以当用兵之费百一二焉。则知澶渊之盟,未为失策。”二人均认为,与战争的消耗相比,输辽岁币只是一个不足百分之一二的很小数目。
1042年,辽兴宗遣使向宋索要关南十县,北宋坚持不许割地,表示可以和亲或者增加岁币并倾向于后者。富弼就此事出使辽国并极力劝说辽放弃和亲接受增币。最终双方议定,宋增加赠辽岁币银、绢各十万,辽帮助宋令西夏向宋臣服,双方保持原有疆界。范仲淹对此次增币交涉的评价是: “自古兵马精劲,西戎之所长也;金帛丰富,中国之所有也。礼义不可化,干戈不可取,则当任其所有,胜其所长,此霸王之术也。臣前知越州,每岁纳税捐十二万,和买绢二十万,一郡之入,余三十万,傥以啖戎,是费一郡之入而息天下之弊也。”有宋臣质疑这次协议:“富弼亦何功之有?但能捐金帛之数,厚夷狄而弊中国耳。”对此仁宗驳斥说:“不然……国家经费取之非一日之积,岁出以赐夷狄,亦未至困民。若兵兴调发,岁出不赀,非若今之缓取也。”
五、结 论
解决对抗—让步两难问题的关键是明确互动双方的动机和首要目标。如果双方的动机均为确保自身安全,首要目标都是避免冲突和维持合作本身,那么让步 (鸽/合作)性策略显然更有助于实现这类目标,也更易被国家所采用。但在崛起国和霸权国的战略互动中,两个大国都难将自己的目标仅仅限定在维持本国 (生存)安全上,而往往均将相对地位和影响力的提升作为自己的主要战略目标。在这一目标函数下,面对霸权国的打压和遏制,崛起国在对抗—让步策略光谱中的偏好将受到可支配物质实力对比、决心对比以及实力变化趋势三个因素的影响。
自2018年开始的中美贸易战尚未改变中国政府关于 “中国经济长期向好大势没有变”的判断,因此截至目前,中国对美外交总体仍保持克制与合作。根据本文理论,如果未来美国联合其他国家加速与中国经济脱钩,强化对中国的科技封锁,并由此影响到中国在21世纪中叶实现民族复兴的自我预期,或者美国在台湾、南海等事关中国崛起的重大问题上严重挑战中国的决心,中国外交的战略取向将被迫向对抗 (强硬)端倾斜,如此,则中美两国在短期内的对抗乃至敌对局面将很难避免,世界被重新割裂为两大对立阵营的冷战风险亦将显著上升。在当前对华强硬已成美国两党最大共识的情况下,上述暗淡前景出现的可能性正在迅速上升。中国在选择对抗性战略之后如何尽可能减少对抗对自身国力增长的负面影响,将是中国能否赢得这场“消耗战”的下一个关键性课题。
[1] 罗伯特·杰维斯:《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秦亚青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章;Charles L. Glaser,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Military Strategy: Expanding and Refining the Spiral and Deterrence Models,” World Politics, Vol. 44, No. 4, 1992, pp. 497-538. 心理学对威慑和螺旋模型的讨论参见Edward J. Lawler, “Bilateral Deterrence and Conflict Spiral: A Theoretical Analysis,” in Edward J. Lawler ed., Advances in Group Processes (Vol. 3) (Greenwich, CT: JAI Press, 1986), pp. 107–130.
[2] Frank C. Zagare and D. Marc Kilgour, “Deterrence Theory and the Spiral Model Revisited,” Journal of Theoretical Politics, Vol. 10, No. 1, 1998, pp. 59-87.
[3] 罗伯特·杰维斯:《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第97—98页;Jack S. Levy, “Misperception and the Causes of War: Theoretical Linkages and Analytical Problems,” World Politics, Vol. 36, No. 1, 1983, pp.76-99; Jennifer Mitzen and Randall L. Schweller, “Knowing the Unknown Unknowns: Misplaced Certainty and the Onset of War,” Security Studies, Vol. 20, No. 1, 2011, pp. 2–35.
[4] Andrew Kydd, “Game Theory and the Spiral Model,” World Politics, Vol. 49, No. 3, 1997, pp. 371-400; Charles Glaser, Ration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 55–92.
[5] 这两种理论的分歧和争论参见Stephen G. Brooks, “Dueling Realism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1, No. 3, 1997, pp. 445–477; Robert Jervis, “Realism, Neoliberalism, and Cooperation: Understanding the Debat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4, No. 1, 1999, pp. 42–63; 宋伟:《国际结构与国家行为:“内斗的现实主义”》,《外交评论》2007年第1期,第46—55页。
[6] Karl P. Mueller, “Conventional Deterrence Redux: Avoiding Great Power Conflict in the 21st Century,” Strategic Studies Quarterly, Vol. 12, No. 4, 2018, pp. 76-93.
[7] Thomas J. Christensen, “Fostering Stability or Creating a Monster? The Rise of China and U.S. Policy toward East Asi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1, No. 1, 2006, pp. 84-95.
[8] Scott L. Kastner and Phillip C. Saunders, “Is China a Status Quo or Revisionist State? Leadership Travel as an Empirical Indicator of Foreign Policy Prioriti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56, No. 1, 2012, pp. 163–177; Steve Chan, Weixing Hu, and Kai He, “Discerning States’ Revisionist and Status-quo Orientations: Comparing China and the U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25, No.2, 2019, pp. 613-640; Ghazala Yasmin Jalil, “China’s Rise: Offensive or Defensive Realism,” Strategic Studies, Vol. 39, No. 1, 2019, pp. 41-58.
[9] 相关争论和讨论参见Xuetong Yan, “From Keeping a Low Profile to Striving for Achievement,”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7, No. 2, 2014, pp. 153–184; Jinghan Zeng, “Constructing a ‘New Type of Great Power Relations’: The State of Debate in China (1998-2014),” The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8, No. 2, 2016, pp. 422-442; Jinghan Zeng, “Is China Committed to Peaceful Rise? Debating How to Secure Core Interests in China,”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54, No. 5, 2017, pp. 618-636; 高程:《中美竞争视角下对“稳定发展中美关系”的再审视》,《战略决策研究》2018年第2期,第14—25页。
[10] 相关争论和讨论参见Li Wei, “Towards Economic Decoupling? Mapping Chinese Discourse on the China–US Trade War,”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12, No. 4, 2019, pp. 519–556; Alexander Lukin, “The US–China Trade War and China’s Strategic Future,” Survival, Vol. 61, No. 1, 2019, pp. 23-50.
[11] 关于中美新冷战风险的讨论参见Lyle J. Goldstein, Meeting China Halfway: How to Defuse the Emerging US-China Rivalry (Washington, DC: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2015); Edward Luce, “Getting Acclimatized to the U.S.-China Cold War,” Financial Times, July 19, 2019, https://www.ft.com/content/a3062586-a9ac-11e9-984c-fac8325aaa04; Yuen Foong Khong, “The US, China, and the Cold War Analogy,” China International Strategy Review, Vol. 1, 2019, pp. 223-237; Melvyn P. Lefer, “Avoiding another Cold War,” China International Strategy Review, Vol. 1, 2019, pp. 205–212; Minghao Zhao, “Is a New Cold War Inevitable? Chinese Perspectives on US–China Strategic Competition,”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12, No. 3, 2019, pp. 371–394.
[12] 王浩:《中国崛起与东亚安全困境:界定、解析及应对》,《太平洋学报》2015年第6期,第40—50页;吴日强:《中美如何避免核军备竞赛》,《当代美国评论》2017年第2期,第39—60页;李燕燕:《战略互疑、安全困境与中美关系解析》,《太平洋学报》2017年第3期,第48—59页;吴志远、马相伯:《竞争中的战略:中国、美国和印太安全困境》,《中国国际战略评论》2019年第2期,第45—55页;鲁传颖:《中美关系中的网络安全困境及其影响》,《现代国际关系》2019年第12期,第16—22页;Thomas J. Christensen, “The Contemporary Security Dilemma: Deterring a Taiwan Conflict,”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25, No. 4, 2002, pp. 7-21; Aaron L. Friedberg, “The Future of US–China Relations: Is Conflict Inevitabl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0, No. 2, 2005, pp. 22–24, 27–29; Avery Goldstein, Rising to the Challenge: China’s Grand Strategy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14–17; Yong Deng, “Reputation and the Security Dilemma: China Reacts to the China Threat Theory,” in Alastair Iain Johnston and Robert S. Ross, eds., 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China’s Foreign Policy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186–214; Alastair Iain Johnston, “Stability and Instability in Sino–US Relations: A Response to Yan Xuetong’s Superficial Friendship Theory,”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4, No. 1, 2011, pp. 5–29; Andrew J. Nathan and Andrew Scobell, China’s Search for Securit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2); Jonathan F. Solomon, “Demystifying Conventional Deterrence: Great-Power Conflict and East Asian Peace,” Strategic Studies Quarterly, Vol. 7, No. 4, 2013, pp. 136-139; Adam P. Liff and G. John Ikenberry, “Racing toward Tragedy? China’s Rise, Military Competition in the Asia Pacific, and the Security Dilemm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9, No. 2, 2014, pp. 52–91; James Samuel Johnson, “Chinese Evolving Approaches to Nuclear ‘War-Fighting’: An Emerging Intense US–China Security Dilemma and Threats to Crisis Stability in the Asia Pacific,” Asian Security, Vol. 15, No. 3, 2019, pp. 215-232; Adam Breuer and Alastair Iain Johnston, “Memes, Narratives and the Emergent US–China Security Dilemma,” 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DOI: 10.1080/09557571.2019.1622083, 2019. 当然也有少数声音质疑安全困境在中美关系中的适用性,参见Andrew Scobell, “Learning to Rise Peacefully? China and the Security Dilemm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21, No. 76, 2012, pp. 713–721.
[13] Andrew Kydd, Trust and Mistrust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Charles L. Glaser, Ration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hapter 3; Shiping Tang, A Theory of Security Strategy for Our Time: Defensive Realism, chapter 5.
[14] Jennifer Mitzen and Randall L. Schweller, “Knowing the Unknown Unknowns: Misplaced Certainty and the Onset of War,” pp. 15-17. 另参见Robert Jervis, “Cooperation Un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World Politics, Vol. 30, No. 2, 1978, pp. 170-186.
[15] Jennifer Mitzen and Randall L. Schweller, “Knowing the Unknown Unknowns: Misplaced Certainty and the Onset of War,” p. 16.
[16] 曹德军:《关系性契约与中美信任维持》,《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9期,第94—95页;黄海涛:《不确定性、风险管理与信任决策——基于中美战略互动的考察》,《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12期,第138页;Michael P. Marks, “The Prison as Metaphor: Recasting the ‘Dilemma’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lternatives: Global, Local, Political, Vol. 26, No. 3, 2001, pp. 351-354; James Steinberg and Michael E. O’Hanlon, Strategic Reassurance and Resolve: U.S.-China Relation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4).
[17] Warner Wilson, “Reciprocation and Other Techniques for Inducing Cooperation in the Prisoner’s Dilemma Gam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15, No. 2, 1971, pp. 167-195; Jean-Pierre P. Langlois, “Perfect Equilibria and Stable Cooperation in the Iterated Prisoner’s Dilemma and Related Games,” Conflict Management and Peace Science, Vol. 11, No. 2, 1991, pp. 69-98; Duncan Snidal,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mong Relative Gains Maximizer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35, No. 4, 1991, pp. 387–402; Joshua S. Goldstein, “Great-Power Cooperation under Conditions of Limited Reciprocity: From Empirical to Formal Analysi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39, No. 4, 1995, pp. 453–477.
[18] Adam P. Liff and G. John Ikenberry, “Racing toward Tragedy? China’s Rise, Military Competition in the Asia Pacific, and the Security Dilemma,” pp.63-65.
[19] Charles L. Glaser, “The Security Dilemma Revisited,” pp. 171-201; Robert Jervis, “Was the Cold War a Security Dilemma?” 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 Vol. 3, No. 1, 2001, p. 38.
[20] Shiping Tang, “The Security Dilemma: A Conceptual Analysis,” Security Studies, Vol. 18, No. 3, 2009, p. 595. 另参见Ken Booth and Nicholas J. Wheeler, The Security Dilemma: Fear, Cooperation and Trust in World Politics, pp. 4-5.
[21] David M. Buss,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the New Science in Mind (Boston: Pearson Education, Inc., 2008), pp. 355-360. 另参见Roger D. Masters, “The Biological Nature of the State,” World Politics, Vol. 35, No. 2, 1983, pp. 161–193; Bradley A. Thayer, “Bringing in Darwin: Evolutionary Theory, Realism,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5, No. 2, 2000, pp. 124-151; Arthur J. Robson, “Evolution and Human Natur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 16, No. 2, 2002, pp. 89-106.
[22] Daniel Markey, “Prestige and the Origins of War: Returning to Realism’s Roots,” Security Studies, Vol. 8, No. 4, 1999, pp. 126-172; Randall L. Schweller, “Realism and the Present Great Power System: Growth and Positional Conflict Over Scarce Resource,” in Ethan B. Kapstein and Michael Mastanduno eds., Unipolar Politics: Realism and State Strategies After the Cold Wa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28-68; Jonathan Kirshner, “The Tragedy of Offensive Realism: Classical Realism and the Rise of China,”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8, No. 1, 2010, pp. 53–75.
[23] Richard Ned Lebow, A Cultur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Thomas J. Volgy et al., “Major Power Statu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 Thomas J. Volgy et al., eds., Major Powers and the Quest for Statu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1), pp. 1-26; T. V. Paul, Deborah Welch Larson, and William C. Wohlforth, eds., Status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24] Michael P. Colaresi, Karen Rasler, William R. Thompson, Strategic Rivalries in World Politics: Position, Space and Conflict Escal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155-156.
[25] Tudor A. Onea, “Between Dominance and Decline: Status Anxiety and Great Power Rivalr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40, No. 1, 2014, pp. 125-152.
[26] 刘博文:《崛起国的战略收缩缘何逆转——以日本(1920—1927)和苏联(1953—1960)为例》,《外交评论》2020年第1期,第99—107页。
[27] 刘丰:《国际利益格局调整与国际秩序转型》,《外交评论》2015年第5期,第46—62页。
[28] 徐进:《理念竞争、秩序构建与权力转移》,《当代亚太》2019年第4期,第4—25页。
[29] Deborah Larson and Alexei Shevchenko, “Status Seekers: Chinese and Russian Responses to US Primac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4, No. 4, 2010, pp. 63-95. 另参见Michelle Murray, The Struggle for Recognit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tatus, Revisionism, and Rising Power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30] Steven Ward, Status and the Challenge of Rising Powers: Obstructed Ambi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31] “China v.s. America: A New Kind of Cold War,” Economist, May 19, 2019, p. 9.
[32] Robert Powell, “War as a Commitment Proble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60, No. 1, 2006, pp. 169-203; Jack S. Legy, “Preventive War and the Bush Doctrine: Theoretical Logic and Historical Roots,” in Stanley Renshon and Peter Suedfeld eds., The Bush Doctrine: Psychology and Strategy in an Age of Terrorism (London: Routledge, 2007), pp. 175-200; Sam R. Bell and Jesse C. Johnson, “Shifting Power, Commitment Problems, and Preventive War,”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59, No. 1, 2015, pp. 124-132.
[33] Muhammet A Bas and Robert Schub, “Peaceful Uncertainty: When Power Shocks Do Not Create Commitment Problem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61, No. 4, 2017, pp. 850–866.
[34] Jonathan Renshon, “Status Deficits and Wa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70, No. 3, 2016, pp. 513-550; Jonathan Renshon, Fighting for Status: Hierarchy and Conflict in World Politic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7).
[35] Robert Jervis, “Was the Cold War a Security Dilemma?” pp. 36-60; Shiping Tang, A Theory of Security Strategy for Our Time: Defensive Realism, pp. 185-187.
[36] Deborah Welch Larson, “The U.S.-Soviet Rivalry,” in William R. Thompson ed., Great Power Rivalries (Columbia: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1999), pp. 371-390.
[37] J. Maynard Smith, “The Theory of Games and the Evolution of Animal Conflicts,” Journal of Theoretical Biology, Vol. 47, No. 1, 1974, pp. 209-221. 朱·弗登博格、让·梯若尔:《博弈论》(黄涛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01—102页。
[38] 周方银:《消耗战博弈与媾和时机的选择》,《国际政治科学》2007年第3期,第61—63页;Catherine C. Langlois and Jean-Pierre Langlois, “Should Rational States Really Bargain While They Fight?” Unpublished manuscript, Georgetown University, Georgetown, Washington, DC/San Francisco State University, San Francisco, CA., 2012. 另参见毛泽东:《论持久战》,载《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47—450页。
[39] Prajit K. Dutta, Strategies and Games: Theory and Practice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9), pp. 125-126.
[40] 戴尔·科普兰:《大战的起源》(黄福武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41] 肖河、蒙克:《“修昔底德陷阱”中的不对称竞争战略》,《国际政治科学》2019年第1期,第19—52页。
[42] Robert Powell, In the Shadow of Power: States and Strategie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34.
[43] David M. Edelstein, Over the Horizon: Time, Uncertainty, and the Rise of Great Powers, p. 23.
[44] Daniel Kahneman and Amos Tversky, “Prospect Theory: An Analysis of Decision under Risk,” Econometrica, Vol. 47, No. 2, 1979, pp. 263-292; Jack S. Levy, “Prospect Theory, Rational Choic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41, No. 1, 1997, pp. 87-112.
[45] Tudor Onea, “Between Dominance and Decline: Status Anxiety and Great Power Rivalry,” pp. 125–152.
[46] Jonathan M. DiCicco and Jack S. Levy, “Power Shifts and Problem Shifts: The Evolution of the Power Transition Research Program,”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43, No. 6, 1999, pp. 694-699; Randall Schweller, “Managing the Rise of Great Powers: History and Theory,” in Alastair Iain Johnston and Robert S. Ross eds., Engaging China: The Management of an Emerging Power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pp. 2-7; Zhou Jianren, “Power Transition and Paradigm Shift in Diplomacy: Why China and the US March towards Strategic Competition?”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12, No. 1, 2019, p. 10.
[47] 戴尔·科普兰:《大战的起源》,第50、70页。
[48] 亚历山大·库利等将修正主义划分为改变现有秩序和现有实力分布两个维度,只改变实力分布不改变现有秩序的国家称为位置主义国家(positionalist state)。Alexander Cooley, Daniel Nexon and Steven Ward, “Revising Order or Challenging the Balance of Military Power? An Alternative Typology of Revisionist and Status-quo State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45, No. 4, 2019, pp. 698-699.
[49] M. Taylor Fravel, “Power Shifts and Escalation: Explaining China’s Use of Force in Territorial Dispute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2, No. 3, 2007/2008, p. 47.
[50] 韩洁等:《展望中国经济长期向好大势》,新华网,2019年8月15日,http://www.xinhuanet.com/fortune/2019-08/15/c_1124879273.htm。
[51] 相关政策争论和梳理参见Li Wei, “Towards Economic Decoupling? Mapping Chinese Discourse on the China–US Trade War,” pp. 537-540.
[52] Norrin M. Ripsman and Jack S. Levy, “Wishful Thinking or Buying Time? The Logic of British Appeasement in the 1930s,” pp. 148–181. 从物质实力看,20世纪30年代中期德国已是欧洲无可争议的霸权国,相关数据参见Randall L. Schweller, Deadly Imbalances: Tripolarity and Hitler’s Strategy of World Conques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26-31.
[53] Dale Copeland, “Modeling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War: A Theory of Trade Expectation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Chicago, September 1995, quoted from Dale C. Copeland,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War: A Theory of Trade Expecta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0, No. 4, 1996, p. 26.
[54] Thomas C. Schelling, Arms and Influenc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6), pp. 92-125; Robert Jervis, “Why Nuclear Superiority Doesn’t Matter,”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94, No. 4, 1979/1980, p. 631; Robert Powell,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of Strategic Nuclear Deterrence,”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100, No. 1, 1985, p. 78; Robert Jervis, The Meaning of the Nuclear Revolution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 38-41, 105; Robert Powell, Nuclear Deterrence Theory: The Search for Credibil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33-45. 核对抗是典型的胆小鬼博弈,而胆小鬼博弈是消耗战的静态形式,参见Prajit K. Dutta, Strategies and Games: Theory and Practice, pp. 125-126.
[55] Zeev Maoz, “Resolve, Capabilities, and the Outcomes of Interstate Disputes, 1816-1976,”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27, No. 2, 1983, pp. 195-229.
[56] Clara Ponsati and József Sákovics, “The War of Attrition with Incomplete Information,” Mathematical Social Sciences, Vol. 29, No. 3, 1995, p. 240.
[57] John J. Mearsheimer, “Reckless States and Realism,”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23, No. 2, 2009, p. 244.
[58] Mark J. C. Crescenzi, “Reputation and Interstate Conflict,”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51, No. 2, 2007, pp. 382-396; Joe Clare and Vesna Danilovic, “Reputation for Resolve, Interests, and Conflict,” Conflict Management and Peace Science, Vol. 29, No. 1, 2012, pp. 3-27.
[59] Timothy M. Peterson, “Sending a Message: The Reputation Effect of US Sanction Threat Behavi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57, No. 4, 2013, pp. 672–682.
[60] Dustin H. Tingley and Barbara F. Walter, “The Effect of Repeated Play on Reputation Building: An Experimental Approach,” pp. 343-365; Alex Weisiger and Keren Yarhi-Milo, “Revisiting Reputation: How Past Actions Matter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 473–495; Chong Chen, “Territorial Dispute Initiation by Weaker States,”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11, No. 3, 2018, pp. 339–372.
[61] Thomas C. Schelling, Arms and Influence, p. 124; Barry O’Neill, Honor, Symbols and War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9); Keren Yarhi-Milo, Who Fights for Reputa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Leaders, Resolve, and the Use of Forc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8).
[62] Özyurt Selçuk, “Building Reputation in a War of Attrition Game: Hawkish or Dovish Stance?” The B.E. Journal of Theoretical Economics, Vol. 16, No. 2, 2016, pp. 797-816.
[63] Dustin H. Tingley and Barbara F. Walter, “The Effect of Repeated Play on Reputation Building: An Experimental Approach,” p. 344.
[64] Allan Dafoe and Devin Caughey, “Honor and War: Southern US Presidents and the Effects of Concern for Reputation,” World Politics, Vol. 68, No. 2, 2016, pp. 341-381.
[65] Joe Clare and Vesna Danilovic, “Multiple Audiences and Reputation Building in International Conflicts,”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54, No. 6, 2010, pp. 860-882; Krista E Wiegand, “Militarized Territorial Disputes: States’ Attempts to Transfer Reputation for Resolve,”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48, No. 1, 2011, pp. 101–113.
[66] 钱其琛:《外交十记》,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07—308页;牛军:《三次台湾海峡军事斗争决策研究》,载张沱生、史文主编:《对抗·博弈·合作——中美安全危机管理案例分析》,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版,第198—199页。
[67] Ketian Zhang, “Cautious Bully: Reputation, Resolve, and Beijing’s Use of Coercion in the South China Se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44, No. 1, 2019, pp. 117–159.
来源时间:2020/12/6 发布时间:
旧文章ID:23658